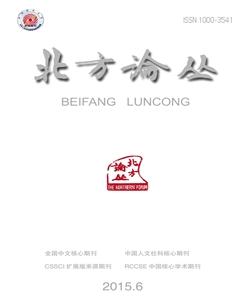被異化的“自我意識”與被照亮的思想未來
孫琳
[摘 要]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以兩種原子論比較為切入點,對抽象的“自我意識”的異化物,即宗教、各種宿命論哲學、神話進行了“三重去昧”與揚棄,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邏輯演進下復歸至“自我意識”的本質“自由”之中。在“三重去昧”過程中,馬克思的“自我意識”觀完成了三層超越:第一,僅僅作為“實體”存在的德謨克利特的必然性原子論;第二,僅僅作為“主體”存在的青年黑格爾派的抽象“自我意識”;第三,僅僅作為“抽象性”的個體存在的伊壁鳩魯的“自我意識”。“自我意識”的對象化活動具有兩個層面:第一,作為其對象化活動的感性實踐;第二,作為其對象化物的感性自然界。通過這兩個層面的對象化使“實體即主體”的“自我意識”的本質在辯證邏輯中獲得完成。“自我意識”的本質即自由。《博士論文》開啟了新的世界觀,即新的現實理論視域和新的實踐視域,啟迪和照亮了思想的未來。
[關鍵詞]馬克思;《博士論文》;自我意識;啟蒙理性;辯證法;感性實踐
[中圖分類號]B01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5)06-0112-06
[收稿日期]2015-09-1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學術史研究”(12&ZD108)、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理解史視閾中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14CKS001)、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唯物史觀范式創新與當代形態研究”(15ZXC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經費專項基金項目“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研究”(XKXM2012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經費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范式創新研究”(SK2014019)
它在它的異在(Anderssein)本身里就是在它自己本身里。——這就是意識的[辯證]運動。[1](p.264)
——黑格爾
青年馬克思帶著啟蒙理性的自由主義激情創作了博士論文。在理性主義基礎、個人主義彰顯,以及人本主義精神的驅使下,馬克思完成了這篇“解決了一個在希臘哲學史上至今尚未解決的問題”[2](p.10)的博士論文。那么,馬克思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我們所需要厘清的馬克思的創新思路是什么?這些創新思路又有哪些意義?這些將首先成為解讀《博士論文》的關鍵線索。
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和解答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啟蒙理性倡導的自由精神正是《博士論文》一以貫之的精神紅線,馬克思解決的問題正是揭示了希臘哲學中深刻的卻被忽視的自由精神。馬克思最重要的創新之處在于以古希臘原子論創造性地隱喻這種自由精神,以此來呼應和繼承啟蒙運動的思想。文中體現的現實性和實踐性視域,雖然尚未形成科學體系,但是,已經開創了歷史的本質性維度的思路,因而意義深遠。
然而,在解答上述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又不得不面對一系列新的問題:第一,“自由”在全文中幾乎難覓蹤跡,馬克思是通過隱喻的方式呼喚自由。那么,馬克思是如何通過辯證法來隱喻自由的?第二,馬克思在文中主要通過對伊壁鳩魯與德謨克利特古代原子論的區別,充分運用其辯證法的批判手法,可以說是對“自我意識”的異化物——宗教、哲學和神話進行了三重“去昧”,在內容上體現了初步使用萌芽中的新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批判基督教教義、古代社會唯物主義、帶有隱形宗教性質的思辨唯心主義,以及神話的創新品質。然而,既然批判建基于“自我意識”的總命題框架范圍內,那么這種主觀性極強的“自我意識”是如何與客觀性極強的唯物主義獲得暫時的一致性的?第三,對抽象的“自我意識”異化物的三重“去昧”是否意味著新的世界觀的降臨?馬克思的“自我意識”與以往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哲學的區別是什么?這三個問題是真正解讀馬克思青年時代思想創新的線索和鑰匙。歸根究底,馬克思的創新正是使用辯證法反對各種抽象的被異化的“自我意識”,最終揚棄異化,回歸自由本質的深刻寫照,同時也是初步探索新世界觀新方法論的哲學實踐(理性實踐)和實踐哲學(實踐理性)的深層結合。對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進行解讀,我們可以發現古希臘的自由戰士伊壁鳩魯、啟蒙運動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青年黑格爾派(鮑威爾)、詩人海涅、社會學家盧梭、伏爾泰等人的思想中閃耀的自由精神的光輝,在《博士論文》中化為完整的整體。可以說,這篇博士論文的主旨不僅隱喻人類的自由精神,而且啟迪并照亮了整個西方思想的未來。
一、 抽象的被異化的“自我意識”——宗教批判
(一)以自由主義批判非理性神學
宗教神學贊同自然的無序與非理性世界的存在,因為只有在此前提下,神才存在。馬克思通過為希臘哲學精神正名進而駁斥舊理性主義神學。馬克思認為,普魯塔克對伊壁鳩魯神學的論戰,不是代表其他個別的東西,而是代表“一種方向”,也就是以神學化的理智對待哲學的態度的方向。馬克思認為,希臘哲學本不應有平淡的結局。思想“助產師”蘇格拉底全面開啟了面向人本身提問的思考模式,從而超越以往伊奧尼亞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和德謨克利特學派的自然哲學,使哲學發生了根本變革。哲學的任務不只是獲得外界事物的規律性、必然性,更在于追問人本身的意義。哲學的研究對象在古希臘已然完成倫理學、實踐哲學轉向。伊壁鳩魯的人學原子論其實是聯系蘇格拉底與啟蒙運動的橋梁。在啟蒙運動的昭示下,哲學的任務是使世界和人變為理性的世界和人,喚醒受到神學的牽連與控制的“自我意識”。只有具有能動性的“自我意識”是哲學的真正的自我直白與格言。在普羅米修斯“我痛恨所有的神”的口號下,只有辯證地喻示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識”,才是具有“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2](p.12)。宗教不過是一切“自我意識”的異化物,因而作為“自我意識”對立面的宗教無法與人的“自我意識”相提并論:“不應該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識相并列”[2](p.12)。馬克思深刻分析以具有能動性的“自我意識”為主體的作為一種意志力量的哲學與外部必然發生的關系——人與現實、哲學與世界的辯證關系,正是為了表明只有從人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關系中才能解決真正的自由問題,這也是馬克思思考新世界觀的萌芽。
(二)以唯物主義批判宗教目的論
伊壁鳩魯對德謨克利特的超越是在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內部的一次超越,伊壁鳩魯超越的是機械論和決定論的必然性的唯物主義。馬克思則追隨了伊壁鳩魯的這種唯物主義立場,用具有能動性的“原子的偏斜”來打破必然性的命運的束縛,借此表明宗教目的論破產。馬克思捍衛了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立場,并對其亦有所超越。因而我們有必要分析馬克思在此的唯物主義的本質,才能進一步分析其如何與“自我意識”相結合。馬克思在這篇論文中體現的唯物主義并不同于伊壁鳩魯,也不同于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崇尚思想與現實、哲學與世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具有能動性辯證法的唯物主義。實則馬克思通篇都以這種唯物主義來揭示神秘的唯心論的宗教目的論性質[3](p.21)。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里跳動著”[2](p.12),它就將永遠與宗教相對立。可見,宗教的本質與德謨克利特原子論是本質上相同的,都受制于必然性的束縛及命運的定然法則。因而德謨克利特與普盧塔克一樣,不過是把“哲學帶上了宗教法庭的立場”[2](p.11)。馬克思在論文中通過對原子的偏斜理論的論證,證明只有具有偶然性、現實性、能動性的“自我意識”的人才能從宗教必然性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成為非限制性的定在。
(三)以理性主義批判神在論
馬克思主要通過對兩位啟蒙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的高峰——康德和黑格爾的批判達成神在論批判的目的。
1馬克思批判了康德對神在論批判的無效。馬克思贊同康德主張的“人為自然立法”的哲學觀點,但在馬克思看來,康德的神在論批判并不實在奏效。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曾批判證明神在論的各種方法,馬克思以其中一段關于判斷成分的邏輯意義的推論為例,指出康德的批判的問題所在:其一,康德通過對認識論的劃界,指出當物體所包含的東西應當與物體的概念相等時,概念才成立。但是,這種相等只能在特定的范圍內實現,“要么可靠地擴展我們的純粹理性,要么設置它的確定的和可靠的限制”[4](p.39),否則,“憑借空洞的玄想對純粹知性純然形式的原則作一種質料上的應用”[4](p.76),只會讓知性本身陷入一種危險。康德的本意是通過知性概念與對象是否具有一致性來證明神不可知,但在馬克思看來,讓知性本身陷入危險并不能證明神不存在,而只能讓人們對自己的認識能力進行懷疑,進而懷疑神到底存在不存在,反而為神留下庇護所。其二,馬克思認為康德的不可知論給神的存在從根本上保留了一些適用性的空間。馬克思以塔勒一種德國舊銀幣。舉例道,當涉及財產的時候,一百個真正的塔勒就比它們的概念,即想象的塔勒、可能的塔勒要來得多。這樣一來,知識便與其所包含的現實對象不一致,“即使它包含著某種可能適用于其他對象的東西,也是錯誤的”[4](p.74)。據此推論,神在也許是與現實對象不一致的,是錯誤的,但依然還是可能適用于某種純粹理性的對象。認為康德此舉恰好反過來加強了神在論的本體論證明。其三,康德對想象界的不妥當處理,也同樣反過來加強了神在論證明。馬克思認為,康德的前提是預先確立了想象事物的存在(正如剛才分析的第一個錯誤的前提一樣),才能讓判斷確立現實與想象之間是否相符合,最終為信仰保留了地位,于是“這個想象就會起這樣的作用,正像整個人類曾經欠他們的神的債一樣”[2](p.101)。此外,康德將這種想象的事物進行普遍化后會引起相關的后果:“你把你所信仰的神帶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國家去,人們就會向你證明,你是受到幻想和抽象概念的支配”[2](p.101)。馬克思以一種特定的場域變化的邏輯證明神在論的謬誤:特定的國家對于特定的神正如理性的國家對于一般的神一樣,都是神不得不停止其存在的地方。因此,只要是在理性的范圍內,神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存在。因而康德的不可知論的理性主義對神在論的批判無效,最終將自由劃分為彼岸的神秘之物。
2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神秘唯心論體系的本質無外乎是顛倒的證明神存在的另外一種方式。黑格爾表面上推翻了神,實際上,“他推翻了這一證明,以便替他作辯護”[2](p.100)。黑格爾用比神學家更為聰明和隱蔽的方式,即在啟蒙理性的光輝外衣下為神在論作掩護。“神”在此外衣下獲得新生,以“絕對精神”的面貌重新公之于世。與德謨克利特不同,黑格爾不是通過證明絕對必然性的存在證明神存在,而是在“否定之否定”的抽象辯證啟示下,通過證明必然性的對立面由于辯證法的作用消失于必然性,從而使“絕對精神”出場。必然世界是神存在的前提,神卻成為偶然世界的保證。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只有把“因為偶然的東西不存在,所以神或絕對者存在”[2](p.100)的命題轉變為“因為神或絕對者不存在,所以偶然的東西存在”,才是正確的。因而馬克思才會對此予以反諷,黑格爾這位宗教法庭的“辯護律師”只有親手殺死“訴訟委托人”(神在論),才能“使他們免于被判刑”[2](p.100)。作為黑格爾體系頂峰的“絕對精神”外化物的宗教與哲學,在馬克思看來,無外都是想象的東西,無外都是對現實表象化后的另一種神。
因此,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隱藏著深刻的辯證法:宗教是自由的異化物和對立面,宗教必須通過自我揚棄才能讓具體的“自我意識”直面和回歸自由精神。這也為馬克思后來通過法哲學批判宗教、國家、市民社會關系埋下伏筆。馬克思批判繼承了啟蒙運動的人學思潮,在“自我意識”的指引下,證明了各種神在論對神存在的證明不外是對神不存在的證明,證明了德國古典哲學各種對神在論的批判不外是為神在論提供理性主義保護傘。正因為宗教是“自我意識”的異化物,因此,對神在論的正反論證都“不外是對人的本質的自我意識存在的證明,對自我意識存在的邏輯說明”[2](p.101)。 二、 抽象的被異化的“自我意識”——宿命論哲學批判
(一) 批判德謨克利特原子論,揭示其必然性的唯心本質
在馬克思的立場上,真實的原子的靈魂就是“自我意識”,其本質是真正的實體與主體的統一。他使辯證法作為在場邏輯來說明兩種原子論在內容上的具體差別。總體說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是完成的原子,或者只具有“實體性”而不具有“主體性”的原子。簡而言之,他的原子世界是孤傲的冷峻的與人無關的世界。為了證明原子概念所包含的“實體即主體”的思想,馬克思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論證:其一,馬克思區分原子的直線運動與偏斜運動,指明沒有具有能動性特征的個別性的“自我意識”。其二,通過闡明原子的質,闡述原子概念所包含的矛盾辯證法。“重力”是原子異化為現象世界和進入到表象領域所不可或缺的質,否則就無法完成辯證法的所有環節。其三,馬克思說明了伊壁鳩魯指認的不可分的“本原”與不可分的“元素”的區別,指出作為“本原”的原子與作為“元素”的原子是原子概念辯證法所包含的本質異化為現象的兩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是同一個辯證的原子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而決非兩種不同的原子。其四,馬克思對時間概念的論述也指明了原子的本質是主體與實體的統一。德謨克利特的原子只能在“空間”中以“排斥”運動中的必然性的直線運動解釋“定在”,而伊壁鳩魯通過“排斥”運動中的偶然性的“偏斜”運動否定“定在”,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兩者對本質世界之外的時間概念的規定。德謨克利特的“空間”只能使對象化環節局限于屬于“實體”自然現象世界,而伊壁鳩魯通過對現象世界的形式即“時間”的辯證本質把對象化環節擴展至“主體”領域,即偶性、感性知覺和感性現象界,使原子概念所包含的“形式”與“質料”兩個相互對立的環節獲得了對象化,進而在主體的“自我意識”領域回復至“原子”的本質,即自由之中。
四、 對伊壁鳩魯和青年黑格爾派“自我意識”哲學的超越
(一)對伊壁鳩魯“自我意識”哲學的超越
伊壁鳩魯將“自我意識”的主觀性的獨立性通過理性的“抽象的可能性”,即想象的方法來獲得時,他的原則得到實現的地方,也就不具有“現實性”了,因而他的“自我意識”只能是“抽象的個別性”,而非“具體的個別性”。在這個觀點上,馬克思對伊壁鳩魯是持有批判態度的。
1伊壁鳩魯的自由也即“自我意識”本質的實現僅僅發生在內主觀意識之中,而非現實生活中。伊壁鳩魯用想象來消滅自然界的現實性,用抽象的個體意識自由來代替真正的自由實現,從而脫離了現實,使得人類的真正現實的普遍的自由成為“抽象的可能性”幻影。“如果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被設定為絕對的原則,那么,由于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統治地位的不是個別性,一切真正的和現實的科學當然就被取消了”[2](p.63)。在科學中,西方傳統理念論認為“形式”高于“質料”,“統治”事物的是普遍共性,而非個別特性,因而伊壁鳩魯“抽象的”“個別性的”“自我意識”取消了現實的科學,同時也取消了超驗的迷信的包括想象的理智的東西。這說明,馬克思在此對伊壁鳩魯抽象性的“自我意識”哲學持有正反兩方面的態度,因為他在取消實證的自然科學和抽象的普遍性的東西時,“可是”[2](p.63)一詞表明,也同時取消了所有屬于想象的理智的東西,這與他的感性原則的認識論是自相矛盾的。
2馬克思此時的辯證法邏輯和世界觀思想深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本身有所局限,但已開創了歷史的本質性維度的那一度的初始視域。伊壁鳩魯的不足之處是把“自我意識”停留在內心,不付諸實踐,導致了伊壁鳩魯“自我意識”觀念的內在矛盾。馬克思說道:“在自身中變得自由的理論精神成為實踐力量,作為意志走出阿門塞斯冥國,面向那存在于理論精神之外的塵世的現實。”[2](p.75)自由的理論精神只有化為實踐的力量,才能走出阿門塞斯冥國而走向精神之外的塵世現實。
3馬克思依然予以伊壁鳩魯的創造性的原子論高度贊揚。如果“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識”不能在自身中否定自己,即獲得“個別的”“能動的”“自我意識”,那么也就無法通過否定性的辯證法在“否定之否定”過程中,而獲得原子與自我意識的本質來祛除內心的恐懼與宿命的迷亂,而達致“內心的平靜”實現真正幸福。因而伊壁鳩魯所有的偉大正是體現在這古老的辯證精神中,也是實證哲學與倫理學意志哲學的最初分野后,對人本身的意義的追問所帶來自由精神所在。
(二)、對青年黑格爾派“自我意識”哲學的超越
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與馬克思的“自我意識”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只具有“主體性”,而不具有“實體性”,因為“現實的塵世”是在他們的視野之外的。所以,馬克思對“自我意識”的理解不僅超越了僅僅具備“實體性”的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哲學,超越了抽象的“實體即主體”的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哲學,也超越了青年黑格爾派的僅僅具備“主體性”的原子論哲學。馬克思不僅具有現實視域,更難能可貴的是具有了實踐視域。在馬克思看來,“實踐”麥克萊倫認為,馬克思這里的“實踐”依然是鮑威爾似的理性實踐,而不包括任何馬克思自己的新想法在內,即并非作為實踐理性來理解。而當時的馬克思只是作為對鮑威爾的某些思想深有同感的普通的青年黑格爾派分子。參見:麥克萊倫:《青年黑格爾派與馬克思》,夏威儀等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74—75頁。是感性的人的活動,也即“自我意識”的外化活動與對象化活動,反過來決定人的“自我意識”,它“可以反過來推論一種哲學的內在規定性和世界歷史性”[2](p.75),它是哲學的生活道路的集中表現,實現了黑格爾“自我意識”的“主奴意識”辯證法。盡管馬克思此時的“實踐”最終還是回復到“自我意識”的辯證邏輯演進之中,一切都還是以“自我意識”作為邏輯的出發點與前提,但能夠明確將“實踐”從“自我意識”中提煉出來,正是其新世界觀萌芽和超越青年黑格爾派領袖人物鮑威爾的體現,為其后將“實踐”與“自我意識”在歷史觀中進行出發點逆轉做了鋪墊。
五、馬克思的“自我意識”的對象化——感性的實踐與感性的自然界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以原子隱喻個人,偏斜隱喻能動、排斥隱喻否定、自我意識隱喻自由,意在以啟蒙精神為世界觀主導的辯證法體系下打破黑格爾“絕對精神”體系的牢籠,使抽象的辯證法邏輯上升到歷史的辯證法邏輯(盡管并尚未完成)。自由、偏斜、偶然、辯證法與“自我意識”是相互糅合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相互畫上等號。那么我們開篇所提的疑問,唯物主義與“自我意識”如何在青年馬克思思想中相結合的問題此時也可得到解答。
唯物主義與“自我意識”在啟蒙運動的自由精神的呼喚下實現了一種共識與統一:首先,作為方法論的辯證法,在承認必然性的基礎上超越必然性。辯證法是正在生成的運動,唯物主義的現實的感性實踐、感性自然界與“自我意識”的自由精神都是以辯證法的邏輯演進過程獲得自身。其次,作為兩者最終目的的向往——自由。唯物主義與“自我意識”最終都在“自由”中實現了“是”與“應當”的統一。最后,作為兩者共同的實現途徑,即現實的感性自然界的具有生成性的感性實踐,感性實踐是“自我意識”的對象化活動,也是“自我意識”統攝感性自然界的橋梁。
因此,馬克思通過“自我意識”這一核心概念聯系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是從抽象的“自我意識”上升至具體的現實的“自我意識”。感性實踐是“自我意識”的對象化活動,感性自然界則是“自我意識”的對象化物。兩者都是“自我意識”的對象化環節,而不再帶具有異化物的迷信與蒙昧。第一,感性的實踐是“自我意識”的對象化活動,并通過這種對象化活動而揚棄其異化物宗教、哲學、神話,在“否定之否定”的邏輯演進中復歸至“自我意識”的本質。第二,感性的自然界是經驗的、個別的自我意識的對象化物。馬克思指出,世界哲學化同時也是哲學世界化,即哲學與世界的關系體現在“自我意識”的對象化環節中。感性自然界與感性的實踐活動標志著馬克思新的世界觀開始形成。馬克思此時唯物主義中已有感性實踐、現實人的能動性視域,以及理性實踐與實踐理性的分野視域,但尚停留在以“自我意識”為起點與終點的辯證邏輯與圓圈之內,并最終以“自由”為形式,也就是用《精神現象學》的宏大敘事系統與邏輯演進理路,因此,盡管馬克思發現了其中體系與方法論的矛盾,并對“自我意識”進行了“否定之否定”的揚棄以突破體系牢籠,但是,馬克思此時的“自我意識”與“自由”是把黑格爾“絕對精神”的客觀唯心論的體系轉化為主觀唯心的本體論,其辯證體系也依然是到達的終點,也依然是絕對的自我的無差別的同一,最終帶有濃烈的唯心主義目的論色彩。正如馬克思自己在發現方法沖破體系所遇到的問題時說的,當“自我意識”感覺到與體系的有伸縮性的自我等同的矛盾時,即便轉而通過能動的辯證法來反對這個體系,卻也“只是實現了這個體系的個別環節”[2](p.76)。所以,馬克思此時尚未完成唯物主義歷史觀對在場形而上學的逆轉,只是已經發現了這個矛盾,具備了初始視域。
此外,感性自然界、感性的實踐活動,還只是“自我意識”的對象化環節,它們與“現實的定在”,即感性人雖然已然共同出場,但目的都是為了完成“自我意識”的辯證法的環節,通過“否定之否定”揚棄異化而回歸其“自由”本質。這種唯心史觀也奠基了馬克思隨后在“巴黎筆記”中的主要論點,即以費爾巴哈“類本質”為起點與終點來討論自由的異化、揚棄異化、回歸本質,進而以這種邏輯理路來批判資產階級社會關系。所以,馬克思此時還沒有形成真正的唯物史觀。我們要將“哲學中的問題”與“問題中的哲學”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后來所開創的唯物史觀視域。總體說來,馬克思的《博士論文》追尋著自由精神,并在以后的理性實踐與實踐理性中,繼續以隱藏的價值觀念追尋著這種不朽的精神,傳承了古希臘哲學的思想光輝,啟迪與照亮了思想的未來。
[參 考 文 獻]
[1][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M]賀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陳學明應當重視馬克思對宗教目的論的批判——評J·B·福斯特對馬克思“博士論文”的研究[J]科學與無神論,2010(6)
[4][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作者系南京農業大學講師,哲學博士)
[責任編輯 張桂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