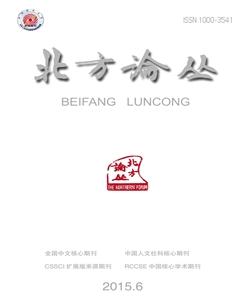盧卡奇辯證法的存在論闡釋
劉建卓
[摘 要]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借助黑格爾的總體性范疇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彰顯為關(guān)于歷史的總體性辯證法。盧卡奇的這一總體性辯證法集中展現(xiàn)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物化結(jié)構(gòu)的批判,以此不僅真實地揭示了人的物化存在,而且通過訴諸無產(chǎn)階級意識把總體性辯證法最終綻露為摧毀物化和實現(xiàn)人類解放的革命武器。這深刻表明盧卡奇的辯證法已經(jīng)觸及到了存在論的根基,《歷史與階級意識》切實開顯了隱藏在方法形式下的辯證法實乃作為存在論的真實內(nèi)涵。
[關(guān)鍵詞]盧卡奇;辯證法;總體性;階級意識;存在論
[中圖分類號]B5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5)06-0122-05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ukacs Dialectics
LIU Jian-zhuo
(Center of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and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Lukacs turns totality dialectics into critique of capitalism materialization structure. The totality dialectics not only reveals the human materialization existence, but also becomes the weapon of destroying the material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liberation by resorting to the proletarian consciousness. It shows lukacs dialectics has touched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show dialectics hidden in the form of method as the real connotation of ontology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Key words:Lukass;dialectic; totality; proletarian consciousness; ontology
馬克思的辯證法問題向來是一個重大而艱難的哲學(xué)課題。在對馬克思辯證法的研究中,盧卡奇具有濃墨重彩的一筆。為恢復(fù)馬克思主義的正統(tǒng),盧卡奇十分重視馬克思的辯證法,其早期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核心主題乃是關(guān)于馬克思辯證法本質(zhì)的問題,從該書的副標題“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研究”即可見一斑。然而,以往的研究中我們總是將盧卡奇的辯證法視為純粹方法論上的事情而忽視了其存在論的實際內(nèi)涵。
導(dǎo)致這一問題的原因,首先在于我們對馬克思辯證法的教條式理解。馬克思“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特別集中地展現(xiàn)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并由此實現(xiàn)了對“現(xiàn)實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把握。因此,馬克思的辯證法正是作為理論內(nèi)容和方法相統(tǒng)一的存在論的辯證法。但長期以來,哲學(xué)界總是想跳開他的理論內(nèi)容去研究他所謂辯證的方法。這種對馬克思辯證法教科書式的理解結(jié)果是,一方面使我們對盧卡奇辯證法的詮釋也陷入了抽象的教條;另一方面,由于盧卡奇本人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序言(包括新版序言)以及正文中,對“辯證法作為一種方法”的多次強調(diào)。隱藏在文本形式的這一皮相之下,他的辯證法的存在論實質(zhì)變得更為復(fù)雜和晦暗。對于這一問題的自覺意識,勢必要求我們重新開啟對盧卡奇辯證法的思考:穿透文本的表層皮相,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的辯證法是否確實只是一種單純的外在方法,又或者說我們只是誤將盧卡奇關(guān)于馬克思的辯證法解讀為了單純的外在方法?這就要求我們以馬克思辯證法作為原則和燭照,沉入《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對文本進行深度耕犁,洞悉并開顯盧卡奇辯證法的本質(zhì)內(nèi)涵。
一
海德格爾認為,一個哲學(xué)家一生只能研究一個哲學(xué)問題,而這個哲學(xué)問題一定是他所處時代的重大的時代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西歐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陸續(xù)失敗。這一殘酷現(xiàn)實促使盧卡奇逐漸擺脫憎惡現(xiàn)實的空想之路,力圖尋求一種改變世界的哲學(xué)。找回逝去的革命,就成為作為革命的理論家的盧卡奇所自覺承擔(dān)的歷史使命。《歷史與階級意識》開篇以“哲學(xué)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p.502)作為題記,這就非常明確地表明了盧卡奇借助馬克思來改變世界和重啟革命的立意。正是這一目的本身構(gòu)成了盧卡奇轉(zhuǎn)向馬克思辯證法的根本原因。
在盧卡奇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tǒng)不是教條的辭令而僅僅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此一“方法”就是辯證法。辯證法之所以對馬克思主義具有本質(zhì)而重要的意義,其原因就在于革命性是辯證法最突出的特性。對此,盧卡奇曾經(jīng)明確提出:“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一種革命的辯證法。”[2](p.49)然而,盧卡奇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作為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國際卻在根本上閹割了辯證法的革命性本質(zhì)。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將辯證法庸俗化為脫離社會歷史的、只是對純粹自然世界的規(guī)律的理論。以這一理解為導(dǎo)向,辯證法由此變?yōu)閱渭兊耐庠谥庇^,變成不觸動對象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的純粹“科學(xué)”,以致在理論上禁錮了革命的實踐。
盧卡奇認為,拯救被宰制的辯證法的革命本質(zhì),最好的武器就是復(fù)活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辯證法的根基。黑格爾的辯證法表現(xiàn)為概念的自我認識和自我生產(chǎn)的過程。概念作為思想的對象“不僅是我們的思想,同時又是事物自身,或?qū)ο笮缘臇|西的本質(zhì)”[3](p.120),是作為思維和存在具有內(nèi)在差別的同一的基礎(chǔ)。概念作為實體同時也是主體,是自在自為的運動和生產(chǎn)著的。概念通過自己“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的思維方式,能夠逐漸揚棄和克服事物的片面性和外在性,并最終達至它的最完滿的形式絕對理念。正是在概念的自我否定中構(gòu)成了概念之間的毫無例外的生成性的歷史-總體。以這種歷史—總體為場域和載體,思維與存在、理論與實踐獲得了具體的統(tǒng)一。盧卡奇指出,這就是黑格爾哲學(xué)的認識現(xiàn)實的總體性的辯證法。“馬克思要發(fā)現(xiàn)黑格爾辯證法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nèi)核。這一合理內(nèi)核就是辯證法的否定性。”[4](p.27)在盧卡奇看來,總體范疇作為革命性的原則,在本質(zhì)上構(gòu)筑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否定性,盡管黑格爾辯證法的保守體系常常使總體范疇的這種革命性隱而不顯,因為他不能理解實際活動著的人及其歷史,終究只是以“概念神話”的形式構(gòu)造了現(xiàn)實,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的變化。因此,他的辯證法歸根到底也只是歷史的思辨表達。盧卡奇認為,馬克思正是以實際活動著的人及其歷史作為基礎(chǔ),成功吸收了黑格爾辯證法的革命性的總體范疇,從而創(chuàng)造性地將其變革成為了一門全新的科學(xué)。對此,盧卡奇一再強調(diào),馬克思之所以能使黑格爾的辯證法變成“真正的革命代數(shù)學(xué)”,“是因為馬克思維護了這種方法的本質(zhì),總體的觀點,把所有局部現(xiàn)象都看作是整體——被理解為思想和歷史的統(tǒng)一的辯證過程——的因素。”[2](p.80)
針對總體性的辯證法的真實內(nèi)涵,盧卡奇進行了具體分析。盧卡奇指出,歷史既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客觀歷史過程,又是人類追求著自己目的的能動性的活動,因而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歷時展開的統(tǒng)一,是作為人類自身的生成性的存在。所以,辯證法正是主體改造客體的歷史發(fā)展過程本身的思想和理論表現(xiàn)。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辯證法只能是歷史范圍之內(nèi)的辯證法,“辯證法來自歷史本身,是在歷史的這個特定發(fā)展階段的必然的表現(xiàn)形式。”[2](p.264)因此,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作為第二國際窒息辯證法革命性的理論根源,正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非法誤用,因為自然界不存在改造活動的自覺主體,也就失去了辯證法革命性的可能。這一點同時也就決定了,作為人之生成性的現(xiàn)實歷史也不是第二國際理論家所繼承的實證主義那樣,只憑借一種自然科學(xué)的方法論就可以獲取的。這種方法究其實質(zhì)只是試圖去追求人之外的規(guī)律,其結(jié)果只能是將人類生活抽象成一堆孤立的數(shù)字,其根源則在于模糊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從而必然導(dǎo)致對現(xiàn)實本質(zhì)的遮蔽。
那么,如何才能獲得對現(xiàn)實本質(zhì)的認識?在盧卡奇看來,這必須通過歷史的總體性辯證法才能獲得。總體性辯證法要求將社會視為一個總體,既強調(diào)歷史整體對各個部分而言具有決定性的統(tǒng)治地位,又堅持把一定的社會放在整個的人類歷史發(fā)展進程當(dāng)中去考察,從而使具體的社會直接面對其本有的歷史性制約。只有通過這種源于人類歷史自身的歷史辯證法,即把各種駁雜的現(xiàn)象都歸并為歷史發(fā)展總體中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的時候,才能穿透表象揭露全部歷史的實質(zhì),從而真實地展現(xiàn)人類生活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這一現(xiàn)實的歷史活動。這就是使我們戳穿表象真切地把握到歷史現(xiàn)實的總體性的辯證法。因此,盧卡奇著重指出,在歷史辯證法中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總體性范疇之所以是作為“科學(xué)中的革命原則的支柱”[2](p.80),它首要的方面不是對外在對象的消極的直觀反映,而是對社會的批判,以此才能切中社會現(xiàn)實,進而才能對現(xiàn)實實施革命性的改造。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科學(xué)的批判”,因而是作為真正的“歷史科學(xué)”的辯證法。
盧卡奇將黑格爾的關(guān)于思想的否定性的辯證法變革,為馬克思的關(guān)于現(xiàn)實的人類活動及其歷史的辯證法,通過這一改造將產(chǎn)生雙重意義上的有效性:其一,借助于黑格爾辯證法的總體性范疇,實現(xiàn)了復(fù)活馬克思辯證法的革命本質(zhì)的目的;其二,這深刻表明盧卡奇的辯證法已經(jīng)彰顯出了存在論的維度。辯證法正是關(guān)于實際活動著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的理論表現(xiàn),因此,盧卡奇所謂的辯證的方法不是別的,正是黑格爾意義上“全體的結(jié)構(gòu)之展示在它自己的純粹本質(zhì)性里”[5](p35)的方法,是作為沉入于歷史內(nèi)容本身的自行道說。只有這種由存在論深處生發(fā)出的辯證法才能切實地對抗被第二國際庸俗化了的辯證方法。
二
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對革命的總體性辯證法的存在論言說,并沒有止步于這種宏觀性的概括,而是將其集中地展現(xiàn)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批判。盧卡奇將他所處的時代明確地稱作“現(xiàn)代資本主義”,而這個時代特有的一個問題就是拜物教問題。總體性辯證法的本質(zhì)任務(wù)就在于戳破這種拜物教假象,揭露資本主義社會之下人的真實生活樣態(tài)。
資本主義批判何以可能?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總體性辯證法,首先要求把資本主義社會放在整個人類歷史發(fā)展過程當(dāng)中,資本主義社會的現(xiàn)實只有根據(jù)它在歷史總體中的作用和地位才能得以把握。因此,必須從局限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直接的、自發(fā)的規(guī)定出發(fā),從它們前進到對具體的總體的認識,也就是前進到在觀念中再現(xiàn)現(xiàn)實”[2](p.58)。盧卡奇將這一觀念追溯為經(jīng)濟范疇。人類社會具有社會的和經(jīng)濟的雙重運動邏輯,經(jīng)濟范疇從作為人與人之間相互關(guān)系的社會總體中產(chǎn)生,同時也就具有了改造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作用,因此,通過經(jīng)濟范疇與人的辯證的相互作用,我們就能夠發(fā)現(xiàn)作為社會總體的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所以,在本來的意義上,任何一個經(jīng)濟范疇都彰顯著人和人之間的一定關(guān)系。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拜物教假象卻成功地掩蓋了人的存在向度,這種掩蓋之所以可能,恰恰在于經(jīng)濟范疇“以對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地呈現(xiàn)在他的面前,對象性形式掩蓋了它們是人和人之間的關(guān)系的范疇這一事實。它們表現(xiàn)為物以及物和物之間的關(guān)系”[2](p.65)。盧卡奇將經(jīng)濟范疇的“對象性形式”稱為“物化”。
追隨馬克思的批判軌跡,盧卡奇選擇從分析商品這一經(jīng)濟范疇入手。之所以從商品出發(fā),是因為較于商品交換只是作為偶發(fā)的和短暫出現(xiàn)的之前社會階段來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形式逐漸成為社會存在的一個普遍因素并日益表現(xiàn)為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核心和結(jié)構(gòu)問題,商品作為普遍和核心地位的確立深刻地體現(xiàn)為勞動力成為商品,“對工人本身來說,勞動力是歸他所有的一種商品的形式……正是從這時起,勞動產(chǎn)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起來。”[6](p.198)因此,盧卡奇指出,只有通過商品形式才能洞穿資本主義社會中,被商品結(jié)構(gòu)物化掩蓋下的“主體性形式的原形”,即人的存在方式。在商品形式的結(jié)構(gòu)中,現(xiàn)實活動著的人僅僅作為一種“物”而存在著。“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獲得物的性質(zhì),并從而獲得一種‘幽靈般的對象性,這種對象性以其嚴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蓋著它的基本本質(zhì),即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所有痕跡。”[2](p.149)商品形式造成的人的物化存在集中地體現(xiàn)在對人類勞動的物化。人類勞動的被物化表現(xiàn)為雙重層面。在客觀方面,質(zhì)上不同的勞動產(chǎn)品被理解為量即變?yōu)樵谛问缴鲜窍嗤模@是不同質(zhì)的產(chǎn)品能夠?qū)崿F(xiàn)交換的一個前提。在主觀方面,這種量化或者形式化逐漸超出了商品本身,進而影響并滲透到了生產(chǎn)商品的工人勞動,這樣一來,工人的具體勞動也隨之變成只具有抽象的人類勞動的量的意義。盧卡奇指出,對象化在商品中的人類勞動的抽象和物化正是根源于“根據(jù)計算、即可計算性來加以調(diào)節(jié)的合理化的原則”[2](p.155)。這一原則構(gòu)成了盧卡奇揭露勞動物化的立足點。
盧卡奇指出,源于這一“合理化的原則”,勞動過程逐漸被劃分為各個孤立的、抽象的局部操作,從而要求破壞產(chǎn)品本身由其質(zhì)所決定的統(tǒng)一性。這樣,傳統(tǒng)意義上對整個產(chǎn)品進行有機生產(chǎn)的方式由于理性計算而徹底決裂,作為商品的產(chǎn)品的統(tǒng)一體被“合理化”為局部系統(tǒng)的客觀組合,從而與作為使用價值的產(chǎn)品分離開來。與此同時,與勞動過程被分割的情況一樣,作為勞動主體的工人也相應(yīng)地被分割為各個局部勞動的因素。原先有機生產(chǎn)時由勞動主體結(jié)合而成的共同體的聯(lián)系被生產(chǎn)的這一機械化切斷為各個孤立的原子。工人自身逐漸淪為附屬于機械的單純工具,越來越喪失作為勞動之主人的本質(zhì),以至于人格也只是作為機器的旁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