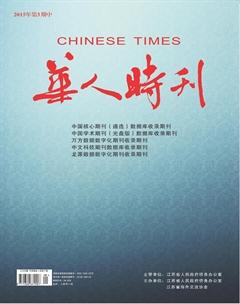從女神神話看女性地位
翁勇君
【摘要】神話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幽靈,在人類的文明演進中始終伴隨著人類前行。神話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產生于社會生活當中。而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代代相傳的神話也發生了改動。從不同的神話記載當中,我們能一窺人類文明的變化軌跡以及人類思維觀念的轉變。
【關鍵詞】女神:不獨立:父權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3-172-02
一、神話里的女神
文學的產生源于生活的變形。通過變形,生活現實轉化為藝術現象。作為最早的文學形式之一,神話產生于人類的“童年時代”,它反映了原始先民對周圍世界的把握、認知程度。然而,原始先民的認識是一種前邏輯的、具體聯想豐富而邏輯推理能力低下的非理性認識,斯特勞斯稱之為“野性的認識”,布留爾稱之為“原始思維”。因此,原始神話的色彩大多是非理性的、幼稚的。而在歷史的發展中,在人類的代代相傳中,人們不斷進行潤色,對神話賦予了更多的個人主觀色彩。在這一過程中,隨著意識形態的滲透,人物故事往往會發生變化,各種褒貶色彩也會發生變化。在現存的中國古代神話里,若相對于男神,女神的數量是十分稀少的。而在不同時代的古書里,對女神的記載也存在諸多異殊。下文以女媧為例解釋這種現象。
在盤古開天辟地的神話出現之前,古代神話中的造物主是女媧。《列子湯問》有這樣的記載:“昔者女娟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闊;斷鰲之足以立四極。其后共工氏與頗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①
漢初的《淮南子覽冥訓》記載:“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熄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瀕民,鴛鳥攫老弱。于是女娟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頗民生。”
在這樣的記載里,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女媧是最早的造物主:補天、理水、創造人類。而在此時還沒有出現關于盤古的記載。屈原的《天問》里出現了“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曹簡,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圖簡,惟時何為?陰陽二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②,但這并未涉及盤古等男性神,說明了那時女媧是作為一個獨立神而存在的。女媧并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神祗,甚至本身就具有造生世界的強大功能。
然而,在漢代以后,有關女媧的神話漸漸和伏羲密切聯系起來。最先的傳說記載伏羲與女蝸是兄妹。《路史后紀》注引《風俗通》佚文日:“女蝸,伏希之妹”。馬編《中華古今注》:“女蝸,伏羲妹,蛇身人首”。到了唐代以后,女媧和伏羲是為夫婦的故事才廣為流傳。依據《唐書樂志》記載:“玄宗開元七年享太廟樂章十六首”引高宗“鈞天舞”日:“合位媧后,稱伏羲”。③
二、地位日低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中提出:“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則白造眾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神話。”④中國的神話存在著歷史化的傾向:神話里的人物在儒家的解釋中,被賦予了上古歷史人物的身份。袁珂先生說過,“神話轉化為歷史,大多出白‘有心人的所為,儒家之流要算是這種工作的主力軍,他們為了要適應他們的主張學說,很費了一點苦心地把神來加以人化,把神話傳說來加以理解性的詮釋。這樣,神話就變作了歷史。”⑤
中國的史官擅長于造神,他們依據社會倫理,創造出各種符合時代統治精神的神。中國的神是倫理化的產物,上文所述的女神的身份變化中也體現了這一點。
事實上,神話里的女神或者是女英雄的數量是極少。“女神在中國神話中的地位是十分悲慘的,他們往往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而需要依賴某一位男性神抵或帝王”。⑥
例如,在漢代以后,關于女媧的神話里,女媧與伏羲的聯系愈發密切。而西王母的原始形象在《山海經西山經》中有記載:“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歷及五殘”。西王母本是一個穴居玉山,執掌瘟疫刑罰的猙獰怪神,后來在《穆天子傳》中蛻去了猙獰丑陋的而目,而變為一個能吟詩作賦的雍穆女神。到了六朝時期,《漢武帝內傳》中更進一步把西王母描繪為一個絕世美人:“可年姍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溶巖絕世”的真靈人。西王母從一個山野怪物演化為一位容顏絕世、母儀神仙天國的真靈人,并成為東王公的妻子,退居于從屬地位。
除了西王母之外,嫦娥的例子更能說明這一點。從最初的月神,到后來的女人,以至于最后被記載為偷竊仙藥的女賊,在一代代的流傳中,嫦娥不斷下降的地位正對應了父權意識的強化以及倫理化道德的強化。作為中國神話的美神,嫦娥的遭遇正反映了倫理意識中的現實精神對企圖超越現實規范的嫦娥的一種懲罰,“對現實規范的強化和皈依”。⑦
在神話中記載的女魃,也是依附于另一個男性神而存在的神。女魃吞云息雨,幫助黃帝戰勝了強大的敵人,最終因為白己的過失而被黃帝殺死。這在一個側而上也反映出倫理社會對女人的挑剔和苛責。
“男尊女卑”的觀念在神話里也有明顯的痕跡,這在顓頊制禮法的神話中就有赤裸裸的體現。而這樣的表現,來源于神話倫理化的結果。
除了失卻本身作為獨立神的自主地位而居于附庸地位之外,“男尊女卑”還體現在諸多方而。譬如神界里的一夫多妻制度:帝告有四妃——姜螈、簡狄、慶都、常儀;帝俊有二妻:羲和、常羲,帝舜有娥皇、女英二妻等等,不勝枚舉。相反地,我們在神話里卻難以發現一妻多夫的記載。“男尊女卑的觀念和二妻四妾的神會現實造成了中國封建道德的二律背反或悖論。一方而,理論上的圣人應該是‘坐懷不亂,不近女色的;另一方而,現實生活中的帝王將相名流顯貴又都是殯妃如云,妻妾成群。而據中國的那種‘現實即為合理的倫理認同,凡是處于社會上層的人,在理論上也應該是最具有道德修養的人。這一種理論和現實的矛盾就造就了中國封建道德的虛偽性”。⑨
而且,若將中國神話與西方神話作對比,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神話里極少涉及女神的愛情生活,女神的情欲是被抑制的。在所有的故事中,女神最多只擁有妻子這個角色,而難以擁有為愛而活的權利。并且在婚姻制度上的權利,多少還有依靠美貌取得的意味。譬如西王母最初處于山野之形時,記載者并未配給她一位如意郎君,唯有到了后期成為統領眾仙的道教尊神之后才有婚配的對象。如果西王母沒有“天姿掩靄”的絕世容顏,也難以母儀天國。
三、溯緣由
在母系氏族社會里,女性占據社會的主要地位。神話里女英雄的形象大多數都留有母系社會的殘余的色彩:人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根據神話的最初記載,附寶感雷電而生黃帝,簡狄吞玄鳥卵而生王契,姜嫄踐巨人跡而生后稷。在這些記載中,神人的誕生之時都是有其母而未知其父,只是到了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以后,記載的人都為其增加了父親這個角色。這是父權意識的興起導致神話倫理化的必然結果。
事實上,當男性承擔了社會的大部分生產勞動之后,男性群體所要求的地位需求就會不斷膨脹,父權意識的發展必然會擠壓女性發展的空間,兩性平等是不存在于歷史當中的。男性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決定了其在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地位。家國同構、君父同一的宗法關系壓抑了女性的權利和成長,同時又反過來促進父權在經濟、社會等方而的發展。而從女神在不同時代的發展特征,我們便能從中窺視一二。
注釋:
①李貞穎.神話:遠古記憶的重述與解讀[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3.
②宋洪興祖白化丈,許德楠,李如鶯,方進點校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85-86
③后晉劉峋,等撰.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1138.
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⑤袁珂中國神話傳說(上)[M].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4:84
⑥⑦⑧趙林協調與超越一中國思維方式探討[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40
參考文獻:
[1]趙林.協調與超越一中國思維方式探討[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2]程靜《淮南子》-女神研究[D]安徽大學,2010.
[3]龔柏巖從中國古代神話看中國傳統思維方式[D]山東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