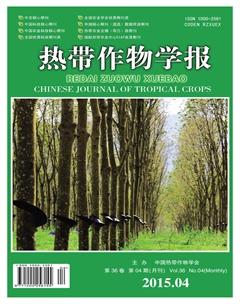基于景觀格局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森林生態安全研究
周亞東



摘 要 基于壓力-狀態-響應概念模型,從生態結構完整性出發,運用GIS和RS技術,結合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與森林景觀格局分析,建立包含28個指標的森林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以海南島為例,運用AHP法對權重賦值,并對研究區域森林生態安全狀況進行評價分析。結果表明:海南島的中部山區市縣的森林生態安全度較高,該方法進行生態安全評價科學、可行。
關鍵詞 生態安全;壓力-狀態-響應;景觀格局;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海南
中圖分類號 F307.2 文獻標識碼 A
生態安全是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新領域。生態安全有廣義和狹義2種理解,廣義的生態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樂、基本權利、生活保障來源、必要資源、社會秩序和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到威脅的狀態,由自然生態安全、經濟生態安全和社會生態安全組成的復合人工生態安全系統;狹義的生態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態系統的安全,即生態系統完整性和健康的整體水平反映[1-2]。
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是生態安全研究的基礎內容[3]。國際機構組織及相關學者針對生態安全評價設計了一系列的評價模型,其中具有代表的模型有:OECD的“壓力-狀態-響應”(PSR)框架模型;UNCSD的“驅動力-狀態-響應”(DSR)框架模型;歐洲環境署的“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指標體系[4-5];Corvailan等[6]提出驅動力-壓力-狀態-暴露-影響-響應(DPSEEA)概念模型。這些評價模型大都是在PSR模型的基礎上進行延伸和完善的。國內生態安全研究以PSR框架擴展和改良的模型應用比較廣泛。郭斌等[7]提出了由生態環境系統狀態、人文社會壓力、環境污染壓力、人文社會響應4個部分組成的模糊多層次評價模型,并應用于銅川市的生態安全評價。程硯秋等[8]建立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生態評價模型對中國10個城市的生態安全狀況利用“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框架進行了分析。本研究以PSR概念模型,結合景觀格局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構建森林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對海南島森林生態安全進行評價。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地概況
海南島地處108°37′~111°03′E,18°10′~20°10′N之間,海南全省土地面積為3.535 4萬km2,屬熱帶季風氣候和熱帶海洋氣候。全年溫暖,雨水充沛,具有較明顯的干濕季節,全年長夏無冬,年平均氣溫為23~26 ℃,年降水量達1 600 mm,降雨量因季節而表現出分配不均勻,春冬兩季干旱。動植物資源豐富,已被發現和記錄的維管植物多達4 680多種,約占全國維管植物種類總數的1/6,其中海南特有植物就有630多種。
1.2 研究方法
1.2.1 指標體系的構建 基于PSR模型,從生態系統的“功能”和“結構”2個方面評價森林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以8項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作為評價森林生態系統“功能”的指標,以森林景觀格局指數作為評價森林生態系統“結構”的指標,并與壓力-狀態-響應(PSR)框架及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相結合,建立指標體系。按照指標選取的科學性、可獲取性、動態性、實用性、代表性等原則,結合海南省森林資源和林業管理的現狀與特點,構建海南省森林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表1)。其中“壓力”是指人類社會對森林資源造成的壓力,從人口壓力、社會經濟壓力、生態壓力等方面構建;“狀態”即森林在上述壓力下所處的狀態,本研究從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出發,以生態系統的“功能”和“結構”來對狀態進行評價,以森林生態系統的8項服務功能作為“功能”指標,同時,選取了8項景觀格局指數作為“結構”指標;“響應”即人類措施在逆轉森林所受的不利影響,提高森林資源可持續發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從經濟響應、政策響應、社會響應等方面構建,選取的指標有6項(圖1)。
1.2.2 指標權重的確定 采用層次分析法結合德爾菲法、李氏九點量表來進行。層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簡稱AHP)是Saaty[9-10]提出的一種多準則決策分析方法,將決策問題的有關元素分解成多個層次,在此基礎上進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該方法把決策的思維過程數學化,從而為求解多目標、多準則或無結構特性的復雜決策問題提供一種簡便的決策方法。本研究的權重確定過程即采用德爾菲法的專家咨詢,經過10位專家評判,最后取平均值來建立各層次的權重判斷矩陣。
1.2.3 數據無量綱化 不同指標間量綱的不同,無法直接進行綜合比較,需要無量綱化為相同區間內的值,消除不同量綱的影響。無量綱化的公式為:
Yi=(Xij-minXj)/(maxXj-minXj) (1)
Yi=(maxXj-Xij)/(maxXj-minXj) (2)
其中,Yi為無量綱化后的指標值,Xij為j指標的i市縣的值,minXj為j指標最小值,maxXj為j指標最大值。正向指標,即指標值越大越好的指標,選用公式(1)進行無量綱化。負向指標,即指標值越小越好的指標,選用公式(2)進行無量綱化。無量綱化后指標值yij在[0, 1]區間。
1.2.4 生態安全指數 本研究中,森林生態安全指數的數學模型為:
ESIFP=
ESIFS=
ESIFR=
ESIF=
ESIFP為森林生態安全壓力指數,ESIFS為森林生態安全狀態指數,ESIFR為森林生態安全響應指數,ESIF為森林生態安全指數,yp為壓力指標,ys為狀態指標,yr為響應指標。
1.3 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1.3.1 數據來源 統計數據來自于海南省統計年鑒及海南省林業廳統計資料。森林資源的空間和屬性數據來源于海南省2011年森林資源二類調查矢量數據。影像來源于法國SPOT6衛星(Systeme Probatoire dObservation dela Tarre)2011年拍攝的遙感影像,融合后影像的分辨率為2.5 m。所有數據均轉成西安80坐標系,3度分度帶,卡拉索夫斯基橢球體,高斯-克呂格投影。在ArcGIS10.2下以2011年二類調查小班矢量數據為基礎,對比SPOT6衛星影像以目視解譯方法對二調小班圖進行校正。
1.3.2 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計算 以森林資源空間和屬性數據為基礎,森林小班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海南森林資源的特點,分為原始林、次生林、橡膠林、經濟林、用材林、灌木林6種類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計算主要參考國家林業局《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規范CLY/T1721-2008》,各項參數均采用本地區值。
1.3.3 景觀格局指數的計算 矢量數據以地類、林種、優勢樹種、起源為依據,劃分為以下6個景觀類型:天然林、人工林、灌木林、農地、水域、無林地。二調矢量數據在ArcGIS下轉換為5 m×5 m的grid柵格格式,最后導出為GeoTiff格式。導出的數據在ArcGIS 10.2下運用Fragstats 4.1進行景觀格局指數的計算。PLAND、MPS、MPI、FD、LPI作為類型級別上的景觀格局指數,分別計算出各個景觀類型的指數,然后根據咨詢專家的意見,天然林、人工林、灌木林以0.625 ∶ 0.250 ∶ 0.125的權重進行綜合,作為相應的森林景觀格局指數。
2 結果與分析
根據上述指標體系及評價方法,計算出海南島各市縣生態安全評價的結果(表2)。
2.1 壓力安全評價
在PSR框架中,壓力(Pressure)是指由于人類活動對森林造成的壓力。由表1可以看出,在人口因素等壓力的作用下,各個市縣的壓力指數分布較為均勻,壓力最大的是三亞和海口,壓力指數大于0.4,這與這2個地級市較高的人口密度及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關,城市建設的擴張及城市人口的增加造成了海口和三亞兩市森林所受到的壓力較大。由于文昌、昌江、澄邁、陵水、儋州等市縣開發建設力度比較大,壓力指標也較高。處于中部山區的瓊中縣,由于近年來森林有害生物發生面積較大,森林生態系統也處于較大的壓力之下。白沙、保亭和五指山3個市縣的分值是海南省所有市縣中最低的,源于這3個市縣處于海南島的中部腹地,所受到的來自人口及森林破壞方面的壓力較小,但森林火災和森林健康狀況還有待重視。總體來講,海南島森林生態在外界壓力上以海南省中部山區各市縣的分值較低;而沿海市縣所受壓力較大。
2.2 狀態安全評價
狀態(State)指森林當前所處的狀態或趨勢。由于歷史以來海南島對土地的開發利用模式,中部山區仍一定程度上保持較為原始的狀態,白沙、五指山、瓊中、保亭的分值最高,表明這幾個市縣的森林生態系統狀態較為優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較好,森林景觀破碎化程度低。雖然由于近年來發展向中部地區擴張,造成森林一定程度上功能的減弱和結構上的退化,但森林生態功能和結構仍處于優良水平。而定安、臨高與海口的森林覆蓋率低,長期以來人類活動的干擾造成森林破碎化,多與農地和水域混雜有關,從而造成景觀格局指數分值不高;另一方面因森林林分質量不高,影響了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故整體狀態指標較低。
2.3 響應安全評價
響應(Response)是指人類對森林生態系統改善所做的主觀能動性反映。海南較早就認識到森林對維系生態平衡的重要性,1984年海南島部分地區開始封山育林,1994年起全省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采伐,1999年開始實施國家天然林保護工程,截至2012年,海南島森林覆蓋率達到了61.5%,其中天然林覆蓋率提高到了19.17%,熱帶天然林面積已經恢復到了65.9萬hm2。從響應分值可以看出,各個市縣在響應上分布不均勻。樂東、瓊中、三亞3個市縣的分值最高,一方面源于這些地區的公益林和保護區的比重較高,林業從業人員也較多;另一方面在于該地區森林面積較大,林業投入因此也較高。而定安、瓊海的分值較低,最主要原因在于該地區因城市建設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公益林和保護區面積所占的比值很低。林業人員結構不合理,高學歷、高職稱的林業從業少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林業的經營管理水平。
2.4 生態安全綜合指數分析
根據對生態安全綜合指數的分析,森林生態安全度最高的市縣為五指山、瓊中、白沙3個市縣,其綜合指數大于0.5,表明海南島中部山區腹地的森林是維系全島森林生態安全的核心,森林景觀格局與服務功能水平都較高,但也不能忽視森林承載力閥值與人為因素對其所造成的影響,應當適當地加以保護與利用,以維護海南島整體的森林生態安全。海口、文昌、定安主要的用地類型為農地、其他非林地及人工林。農地小斑塊化及其他非林地造成景觀破碎化程度高,是森林生態系統面臨的最大問題。
3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采用PSR概念模型,從生態完整性出發,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景觀格局分析分別作為“功能”與“結構”指標融合到PSR框架中,建立了包含28個指標的海南島森林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層次分析法結合專家評分,對指標進行權重賦值并綜合進行指數計算,在不同區域之間進行對比。通過實例證明,該方法邏輯嚴密、過程科學、結論清晰,將生態安全狀況以簡潔明了的形式呈現;該方法能很好地把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在強調森林生態系統功能和結構的同時,又能考慮社會與經濟因素,在森林生態安全評價中具有可行性與很高的實用價值。
通過分析結果表明,海南島的中部山區市縣的森林生態安全度較高,森林結構合理,原始植被豐富,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強,天然林景觀斑塊面積大,是維護海南省整體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而沿海地區由于歷史以來人類活動頻繁,森林面積小而破碎,破碎的景觀斑塊造成生態系統功能的嚴重下降,同時又受到人為與社會經濟水平的多重壓力,森林生態安全度偏低。
森林生態安全評價,數據的易獲性、時效性和準確性是評價的基礎。然而,在實際研究過程當中,一些更能反映森林生態安全狀況的指標數據不容易獲取,數據的欠缺直接影響評價的系統性和準確性,對評價的質量有影響。
森林的消長是一個動態過程,由于海南島只有一期的森林資源二類調查矢量數據,在本研究中無法在時間序列上進行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應收集不同時期的森林資源調查數據,對森林生態安全的動態進行評價,更好地揭示森林生態安全的變化趨勢。
參考文獻
[1] Kullenberg G.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02, 45(4): 761-776.
[2] 肖篤寧, 陳文波,郭福良. 論生態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內容[J]. 應用生態學報, 2002, 13(3): 355-358.
[3] Costanza R.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5, 15(2): 89-90.
[4] Berger U, Rivera-Monroy V H, Doyle T W, et al. Advances and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based models to analyze and predict dynamics of mangrove forests: A review[J]. Aquatic Botany, 2008, 89(2): 260-274.
[5] 劉艷艷, 吳大放, 王朝暉. 濕地生態安全評價研究進展[J]. 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 2011, 27(1): 69-75.
[6] Corvalan C, Briggs D, Kjellstrom T.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indicators[M]//Briggs D, ed. Linkage methods for environment and health analysis. Geneva: UNEP, USEPA and WHO, 1996: 19-53.
[7] 郭 斌, 任志遠,高孟緒. 3S支持的城市土地利用變化與生態安全評價研究[J]. 測繪科學, 2010, 35(2): 125-129.
[8] 程硯秋,遲國泰. 基于核主成分分析的生態評價模型及其應用研究[J]. 中國管理科學, 2011, 28(3): 182-192.
[9] Saaty T L. Modeling unstructured decision problems: a theory of analytical hierarchies[C]//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e Rolla, 1977: 76-79.
[10] Saaty T L.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M]. New York:McGraw- Hill, 1980: 2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