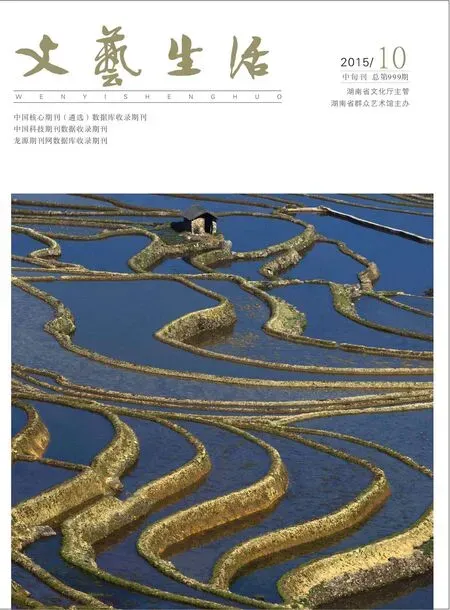淺談《楚辭與原始宗教》
謝曉冬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江蘇蘇州215006)
淺談《楚辭與原始宗教》
謝曉冬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江蘇蘇州215006)
楚辭是中國文化史上最為奇特的文化現象,它以其悲壯激越的情感和獨立不羈的人格力量大大沖擊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楚辭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形態,顯示了文化在過渡狀態之中文化因素的互相滲透和選擇的規律。
楚辭;禮俗;屈原;祭祀文化
兩千年來的楚辭研究其主導思想在于調和“發憤抒情”和“溫柔敦厚”兩種品格之間的矛盾,其最終用意是在維護傳統禮教。楚辭所表現出來的哲學思想﹑歷史觀念政治思想和人格情操等理性內容,基本上體現了屈原對時代精神的把握,楚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楚國特殊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影響。
楚文化,是以楚國的傳統文化為主,以中原周文化為次,兼有其他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個綜合體,它形成于春秋末期,并一直保留到戰國結束。戰國各地有宗教,而以楚地為盛。《漢書·地理志》記“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文物考古則印證了歷史記載。湖北江陵戰國中期的天星觀一號墓出土的竹簡中有2700字有關卜筮﹑祭祀的簡文,說明戰國時期中原各國儒家等學說的理性精神漸居上風,楚地卻巫風盛行,楚人沉浸在鬼神的世界之中。
屈原是楚王的宗族,曾任左徒,后又稱三閭大夫,知識廣博,有較強的外交能力和政治能力,他職掌王族宗族長官,具有懷疑精神和理性品質。《天問》是楚辭中最奇特的一部作品。就其詩體形式而言,它一問到底的表達形式,十分罕見。對形式的過分執著往往意味著一種職業性在詩文背后起著作用。《天問》包括一百七十多問,一部分神跡巫祭之事,一部分述傳說歷史。各民族的史詩無一例外都要回答宇宙和人類起源的問題,《天問》也不例外。《天問》還有問及鬼神者,如風神“伯強”﹑水神“康回”等等,這顯然是巫史知識的一個重要部分。《天問》亦有問及祭祀儀式者,如“化為黃熊,巫何活焉”等,以上幾個方面相當于《訓典》的“序百物”,是巫師所必備的知識。《天問》實有似于《訓典》,所以可以推斷《天問》正是以屈原自己所掌握的巫史文獻作為素材而創造出來的長篇詩歌。
屈原的職務與巫史傳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天問》是一部巫史文獻的作品,屈原雖知識淵博,充滿了時代精神和浪漫氣質,但遭陷害流亡的不幸經歷,使得他對社會歷史有著深刻的反思。司馬遷說:“余讀《離騷》﹑《天問》…,悲其志。”《天問》和《離騷》一樣,包含了屬于屈原個人的思想和感情,并且有著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使得二百年以后的司馬遷都為之悲哀。《天問》表達了屈原對天意的懷疑,這一思想來自兩方面:一是戰國時代的社會現實,一是他自己的切身體會。另一方面是屈原正直不屈,卻為楚王所疏遠直至流放,對于滿腹抱負的政治家來說,簡直是命運中的巨大打擊。“王聽不聰,讒言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由此表明屈原忠君的政治熱情。
《周禮》曰:“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在屈原看來,夏啟的“九歌”,不但是祭祀“帝”的,而且還充滿著人情的放縱。“九辯”﹑“九歌”﹑“九韶”得自上的說法自然是神話,但可以相信這三者是和祭祀儀式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分為巫樂﹑巫歌﹑巫舞。因其本身的神秘性質,故被后人神化為夏禹竊自天庭,成了“天帝樂名”。屈原顯然是明白原始“九歌”的真實含義,只是他對原始祭祀性質不能接受,故對夏禹頗多指責。
楚辭的“九歌”是如何產生的呢?王逸曰:“《九歌》者,屈原所為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由此筆者可以得出幾點信息。(1)《九歌》原流傳的地點;(2)《九歌》是當地土著祭祀樂歌;(3)現傳《九歌》是經屈原改寫記錄的。屈原所作的《九歌》與原始“九歌”重名,相同的書名之間一定會存在某種文化聯系,但是兩個“九歌”之間相隔千年,雖出于一地,但不能說明就是同一體,“九歌”的祭祀禮儀的交往和傳播在流傳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生變異。屈原所任命的三閭大夫之職,包含有宗教祭祀的內容,因此,屈原無疑對楚文化的祭祀一套十分熟悉。當他看見沅湘祭祀之禮時,為了滿足“褻慢淫荒”,他對《九歌》進行加工改造。另一個原因應該是出自屈原的情感需要和創作的沖動,是一種自我安慰的方式。屈原知識豐富,具有強烈的政治抱負,卻遭流亡,司馬遷指出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記錄改造的《九歌》也是他文學創作的一部分,創作肯定是包含了作者的個人感情色彩,不是對原始”九歌”進行還原;而且巫術祭祀在本質上也是想象的產物,它除了初民用以“控制”自然外,也是他們面對自然世界的莫測和恐懼所采取的自我安慰的形式。
楚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非常廣泛而深刻的意義,楚辭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形態,顯示了文化在過渡狀態之中文化因素的互相滲透和選擇的規律。楚辭對巫術宗教的自覺保護,為人們提供了精神家園。
I206.2
A
1005-5312(2015)29-0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