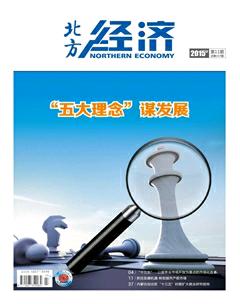從經濟學角度對我國PM2.5問題的分析及對策思考
一、解決PM2.5問題的經濟學價值
(一)PM2.5與我國對外貿易的關系
眾所周知,國際上通常會以一個國家的環境問題大做文章,進而限制該國的對外貿易。其中,西方國家對我國征收碳關稅就是典型案例,PM2.5問題就是一個典型代表。盡管政策限制和技術發展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但政策限制會降低企業生產積極性,技術發展則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總的來說,雖然短期看這些缺陷會造成商品國際競爭力有所削弱,進而影響出口貿易整體規模,但長期來看卻仍有利于環境改善,同時刺激出口企業采用更加清潔的節能減排技術,提高生產技術水平。而在出口貿易商品的構成中,則可以提升低碳產品的出口比重,從而使得出口貿易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二)PM2.5與區域產業結構轉型的關系

要解決PM2.5所引發的環境問題,產業結構首當其沖。PM2.5問題較嚴重的地區,重工業往往是其經濟支柱,也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因此,要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影響到的不僅僅是民眾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還將影響到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以往,對此類地區的綜合發展水平往往采用較為單一的經濟績效進行衡量。但實踐表明,在進行區域產業結構轉型中,加入環境成本核算有助于科學地評估產業結構的轉型效果。在對因產業結構不合理而造成嚴重PM2.5的地區,其進行產業結構轉型需要將注意力轉向逐步減少甚至淘汰資源浪費嚴重或是再利用率相對較低的產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高的產業和低污染、低耗能產業的比重。解決PM2.5問題,實際就是倒逼產業結構轉型,使得區域經濟的發展更為綠色、科學。
二、造成我國PM2.5問題的主要原因
(一)政府一味追求發展而扭曲市場
從經濟學角度看,政府通過一定的政策傾斜,鼓勵民營企業投資、吸收外資等來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拉動出口高速增長,這無可厚非。但部分地方政府在較長時間內,扭曲理解市場,盲目招商引資、甚至進行了過度的政策傾斜。如高污染的第二產業在稅收、土地政策等方面享受的過多照顧和遷就就對其他行業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不僅壓縮了其發展空間,更損害了其合理利益。具體分析如下:
一是工業用地審批尺度過寬。高污染行業的企業往往占地面積較大,而我國工業用地價格基本是居民住宅價格的1/8,這個比例只有其他國家和地區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4。這就使得高污染行業土地成本過低,降低了其行業門檻,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資金向高污染行業的流入。二是稅負征收存在扭曲。我國很多服務行業間接稅要高于制造行業,這在建國初期確實促進了工業企業的發展,但目前卻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瓶頸。三是很多服務行業進入門檻過高。我國政府在金融、通訊、教育、醫療、媒體、鐵路、民航等服務行業設置了較高的進入門檻,這雖然保證了行業的安全,卻也形成了這些行業的壟斷地位,不利于行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市場過于追求效益而忽視調控
一些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選擇了尊重市場而較少采用政策手段干預,這有助于提高市場活力和經濟效益。但由于市場存在自身的盲目性、滯后性,加之其本質是追求經濟效益,而非社會責任,這就導致了PM2.5問題的發生。具體可分析如下:
一是過度燃煤。我國石油天然氣相對較少,煤炭是第一大能源。站在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如果僅考慮煤炭生產者自身利益最大化及消費者消費費用效能最大化,而不考慮燃煤帶來的污染和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即“負外部性”)以及治理空氣污染需付出的沉重代價,那么煤炭的開采和使用將是不可控制的。二是清潔能源開發及投資不足。盡管政府、企業及公眾均能認識到清潔能源的“正外部性”——即清潔的空氣可減少民眾發生呼吸道疾病的概率,但由于清潔能源的價格要高于其他普通能源,消費者往往會選擇其他能源,清潔能源則被迫降低價格。盡管有一定的政府補貼,但由于這種“正外部性”無法內生化,就導致了生產者缺乏投資興趣。三是汽車消費增長過快。與分析燃煤過度問題的思路相似,要考慮到汽車增長的“負外部性”——即公眾以未算入空氣污染代價在內的“過低價格”買入汽車,并因過度消費造成汽車尾氣污染。盡管政府在發放車牌數量和限行上進行了嘗試,但效果并不明顯,且限行也引起了法律上的爭議。
(三)企業和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感有待提高
PM2.5問題的社會責任承擔者應當是整個社會,但此前不論是政府、企業還是消費者,其各自的目標函數中治理PM2.5責任的權重幾乎為零。與此同時,企業和消費者又將治理責任推向政府而忽視自身責任,具體可分析如下:
一是企業缺乏治理PM2.5問題的社會責任感。從微觀經濟學角度分析,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其主要是根據既定的投入成本和產品價格,通過對市場的預測,計算出最優的產量,由于污染成本過小及其承擔治理的回報較低,這導致了部分地區存在一些企業邊交罰款邊生產,而不進行排污整治的現象。即使有企業進行了排污治理,絕大部分也是受到了外部性刺激(政府正向補貼激勵或負向罰款激勵),而不是因為內部社會責任感的驅使。而從發達國家來看,企業所追求的目標除了利潤外,還包括社會責任,這在很多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的數據中就可體現。二是消費者缺乏治理PM2.5問題的社會責任感。微觀經濟學假設消費者追求消費效能最大化,而不考慮社會責任,這是一種理性假設。事實上,消費者的這種選擇必然會助長企業在治理PM2.5問題上的消極態度。反之,若在消費者的消費目標函數中加入社會責任感,其在選擇產品時則會傾向于更加清潔環保的產品(包括選擇更綠色的出行方式),綠色消費需求的增加則會引導企業調整生產方式及產品結構,形成類似于政府補貼的正向激勵,且這種效果更為良性和持久。
三、多方合力,共同推動低碳經濟發展
(一)政府引導,使發展綠色經濟成為新常態
一是合理確定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確定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合理性、加快產業結構轉型是解決PM2.5問題的根本。各地政府應當樹立合理的政績觀,由過去的“金色GDP”評價指標轉為“綠色GDP”評價指標,并注重地區間協同發展。二是加強對低碳經濟的扶持。在工業用地審批、稅負征收、服務業門檻準入方面,政府部門應改善相關政策措施,通過的相關政策調整來引導高污染行業現有模式的轉型。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大型企業,如鋼鐵企業的職工較多,的確不易實施改革,但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沒有最終協調不了的利益,這是政府部門應該確立的觀點。三是加大污染懲罰力度。新《環保法》給了環保部門更大的權力,但其實施需要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提高對污染企業生產的處罰力度,超過其違法利益所得,在這高壓態勢下企業必然會重新依據市場規律,尋求自身出路。
(二)市場引導,發展清潔能源
發展清潔能源,應當充分發揮市場的主體作用,加強政府宏觀調控,這樣既可以克服市場自身的缺點,又能夠引導企業和消費者投入清潔能源的開發和使用中。一是國有大型企業要克服自身利益藩籬,引領清潔能源發展。要加強鋼鐵、汽車、石油、煤炭等支柱性產業能源清潔技術的開發與使用,并加大新能源技術的研發投入。二是宣傳綠色能源的正外部性,通過補貼能高清潔能源市場競爭優勢。 PM2.5問題不是單純的市場問題,而是與環境和社會共同相關的綜合問題,而解決需要以市場為基礎。為此,一方面,需要加強宣傳清潔能源的正外部性,提高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政府要采用補貼、稅負等多種手段進行刺激,并通過多種渠道提高清潔能源產品的市場普及率和競爭力。
(三)提高企業和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感
提高企業和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感有助于增加市場對清潔能源的認識和需求。企業應提高社會責任感,拒絕破壞環境帶來的利益誘惑,同時,堅持創新清潔能源生產技術,降低生產成本,并豐富產品類型,提高清潔能源的正內部性,且以消費者能夠接受的價格進行銷售。消費者面對消費函數的調整應盡量減少購買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生產的低價產品,提高對清潔產品的需求,這有助于提高清潔產品的市場外部性。事實上,這雖然會在短期內造成個人消費成本上升,但長久堅持下去便能促使清潔能源的普及,既贏得了藍天白云,又贏得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