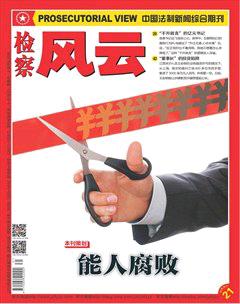對腐敗能人我們能否高抬貴手
楊旭垠
來自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檢察院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園區現有國企近30家,資產總額上千億,五年來共查辦國有建筑企業高管職務犯罪案件13件13人。其中,近90%是本科以上學歷,且多為技術骨干和專家型人才,有人負責的工程項目還獲得過建筑業最高榮譽“魯班獎”。實際上,蘇州園區作為一個縮影,映射出的是近年來各地“能人腐敗”案高發的現狀,也引發了普通大眾對“法治公正”與“工作效益”博弈的爭論。
安徽省黃山市政協原副主席吳洪明因涉嫌受賄、濫用職權罪站在被告席上時,曾大義凜然地自稱收錢是為了搞好上下級關系,在棚戶區改造拆遷補償中的權錢交易則是約定俗成,更是政府為民謀福的“天職”。他還大打感情牌,說自己年三十在車間與工人同吃年夜飯,著實讓人感到怎么那么“好”的官也會犯罪?
其實吳洪明的辯解并非另類,只是他表達得更加戲劇化。當一批曾在政界、商界、學界大有作為,甚至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官員、國有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紛紛落馬后,也冒出了一些吳洪明式的聲音,認為這些人曾經立下汗馬功勞,更讓老百姓得到了“實惠”,一些城市的面貌煥然一新。今日的沉淪,乃有其深刻的心理、環境原因,念其屢建功勛,是否可以“罪減一等”甚至是“戴罪立功”。然而這些真能成為減輕他們罪責的理由嗎?
“原罪”是否能被寬恕
據筆者所看,每一個欲望被異化的“能人”貪官,本質上都存在類似精神疾病的病態心理。其一是榮譽光環下的精神壓抑。一般而言,大部分紅極一時的貪官都有著卓爾不群的能力與魅力,而在榮譽的背后,卻是需要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投資”在為民謀福上的。不少“能人”領導出身貧寒,在其艱苦奮斗的創業史中曾把個人基本需要放在需要結構中最底層,而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到工作中。但是,這種個體的基本需要還是長期潛伏著,特別是將早年的貧寒經歷壓抑在潛意識的深處。江西原副省長胡長清就說自己是個山里娃,讀書時母親做的一雙草鞋穿破了也不舍得扔,但后來卻攫取公款500余萬元。所以一旦大權獨攬,這種本我的“原罪”便蘇醒過來,轉型為追求玩樂和放浪形骸。
其二是成功過后的恐懼。筆者感到,“能人”貪官的貪腐類似抑郁癥的自殺。一些領導者歷經磨難,修成正果,然而暮年的鐘聲也敲響了,頂峰之處必是回落的悲涼之感油然而生,脆弱的心靈已無法承受喪失權力所帶來的心靈振蕩。一些走進反貪局的“能人”不少便成為“59”現象的夕陽,潛意識中追求自我毀滅。
其三是人性中的安逸本能。從人的本性上來說,都是希望過上安逸的生活,“能人”也不例外,只是他們感到自己為事業付出實在太多,為求得平衡,便對權、財、色滋生出病態心理。有人曾統計,省部級以上腐敗分子幾乎人人包養情婦,中箭落馬的縣處級領導干部中則有80%以上陷入過色情陷阱。因此,貪婪心理、僥幸心理、矛盾心理、補償心理、虛榮心理等紛紛出籠,著實讓人們對“能人”腐敗的心理根源眼花繚亂。
然而,這些心理上的“原罪”真的能被寬恕嗎?且不說那些真正一心為民的好官清官——孔繁森、焦裕祿、任長霞等,他們也都是能人,但他們的超我已牢牢駕馭住了本我,讓個人欲望在利他中得到滿足,實現了馬克思所說“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人”。從法律上講,犯罪心理上的成因往往只能在犯罪心理學和預防學的層面上進行考量,充其量也只能進入到刑法學的“動機層面”,連犯罪構成中的“主觀要件”都算不上。因為刑法認為,主觀目的是與犯罪行為直接相關的,每一個個體,只要其心智正常,都要為其行為負責。當然,這種不正常,是不可能包括對欲望的病態心理的,否則那些殺人狂、色情狂都可以逍遙法外了,而刑法恰恰是給予這種心理病態以法律上的限制。對貪官的這種病態心理予以縱容,甚至歸因于他們早年的成長經歷和心路歷程,無異于告訴人們,只要是事出有因,就可以法外容情,而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政治生態問題及其刑法處置
2014年,中央第十二巡視小組向江蘇省反饋巡視情況,提出了“能人腐敗”,而在浙江,則直指有的領導干部存在“一家兩制”,除此之外,像“山頭主義”“蒼蠅式腐敗”“少數黨員參教信教”“個別黨員干部參與群體性事件”等新名詞,也出現在各地巡視組的表述中。可以想見,巡視組是把這些情況作為一類問題提出的,特別是對山西政治生態問題的表述,更是前所未有。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生態?刑法到底能不能管?說到政治生態,與其用枯燥的名詞解釋,不如列舉幾個不良政治生態的表現來得直觀。
第一種是“一把手”生態。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掌權后,幾乎成了一個上級管不到、下級不敢管、群眾無法管的“土皇帝”,進而直接形成與其個性相匹配的政治生態,在有些地方,大搞黨政大權“一把抓”、財政大權“一支筆”、干部大權“一言堂”。
第二種是“江湖式”生態。南通經濟開發區總公司原副總孫俊落馬后感嘆:“好朋友就像助力車,壞朋友就像催命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兄弟義氣,轉變為政治舞臺上沆瀣一氣的借口,辦事先講關系,論人脈,甚至借助職權培植黨羽。一些“能人”坦言,沒有“自己人”,工作就寸步難行,同流合污和職務犯罪集團化怎會不應運而生。
第三種是“交易型”生態。一些地方權錢交易“潛規則”盛行,“能人”干部推波助瀾。四川省甘孜一副縣長甲波扎西是位文藝青年,撰寫的旅游風光片《最后的香格里拉》榮獲全國一等獎,創作的歌曲《凈土亞丁》獲西部歌曲大賽金獎,然而“小清新”的背后卻是“重口味”,他大搞權錢交易,收受巨額賄賂,最終玷污了這片凈土,這片香格里拉。
第四種是“人情化”生態。安徽省鳳陽縣兩名稅務分局長犯了受賄罪。法院審理中竟收到縣國稅局開具的證明,稱兩人在工作中表現突出,建議從輕處罰。對此,縣國稅局長還振振有詞:“主要是不想讓家屬覺得單位沒有人情味,讓他們心寒。”這位有“人情味”的領導能做出此等荒唐事,怎能不讓人感到“人情”的“偉大”。
我們常說,壞的制度能讓好人干壞事,而好的制度則能讓壞人不敢干壞事。在筆者看來,如果說目前的政治生態還未完全凈化,那就要靠法治來形成良好的制度環境。早在蒙昧時代,北歐國家尚處于“歐洲外緣”,那里的先民更有“維京海盜”的行事傳統,這顯然比同時代刀耕火種的中國人彪悍許多。然而,中世紀法律的嚴苛,加之宗教法的影響和海盜交易規則的確立,使他們逐步走向現代文明,時至今日,北歐已成全球最清廉的地區,這就是法治的力量。
我們對那些墜入權力深淵的貪官,特別是“能人”貪官,不否認環境對他們造成的影響,然而這種外部影響一定不是根本性的,根本的還是內因。換句話說,不懲處他們,也是縱容他們進一步惡化政治生態。既然跨出了這一步,就必須受到刑法的制裁,這在刑法學上被稱為“罪責自負”原則,位于救濟最后一條防線的刑法首先要做到秉公執法,才能反推凈化整個政治生態環境。
從“刑不上大夫”到“揮淚斬馬謖”
李祥,吉林省煤炭工業局原副局長兼總工程師,上世紀90年代,遼源礦務局年平均絕對死亡人數37人,李上任后,年平均絕對死亡人數18人,李祥因此被授予國家采礦專家稱號。如果按照他一年少死19條人命的功績來看,那李祥后來受的那60多萬元賄賂根本就不算什么,因為“生命無價”,可事實真是那樣嗎?
但凡一個貪官倒了,總有人歷數其“豐功偉績”,說他如何平易近人、如何處事公道、如何力挽狂瀾,類似的輿論在沈陽市原市長慕綏新案和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案審判后同樣存在。但事實上,法律上壓根兒就沒有“好貪官”一說,因為法律講究功過分明、功不抵罪。需要強調的是,所謂“好貪官”一說不僅在法律上沒有市場,在政治倫理上也講不通。依據法律懲罰貪官,既是貪官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也是在政治倫理上對扭曲價值觀的一種矯正。
要說將功抵罪,中國古代倒是早已有之。曹魏時期,刑律中正式確立“八議”,即八種人犯罪,一般司法機關無權審判,必須奏請皇帝裁決,由皇帝根據其身份及具體情況減免刑罰的制度。他們是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筆者曾想,這范圍里要是個個都議,也夠皇帝忙一陣的了。“八議”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禮制原則在刑罰適用上的具體體現。從此時起至明清,“八議”成為后世歷代法典中的一項重要制度,歷經1600余年而相沿不改。
而這樣的做法,在現代社會是注定行不通的。但時至今日,竟還有人留戀于那個禮法不分、功過相抵的年代。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隋鳳富,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農村星火計劃帶頭人、全國新長征突擊手、中國當代杰出企業家,在他的帶領下,黑龍江墾區糧食產量突破400億斤,按13億中國人計算,足以確保全國1/10人口一年的口糧。若照鳳陽縣國稅局“因工作中表現突出,建議從輕處罰”的說法,那中紀委就該頭痛了,該用“怎樣的功”來抵“怎樣的罪”呢?這恐怕又得回到“說人情”“講關系”的死循環中,腐敗“零容忍”也只能是一句口號罷了。
功是功,過是過。貪官只要觸犯刑律,就應該受到法律制裁。最后想起商鞅說過的一句話:“所以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商鞅最后是死在自己制定的刑罰下,也算“以身試法”了,但蕓蕓大眾直至2000多年后的今天,有不少人還搞不清短期利益和長遠公正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