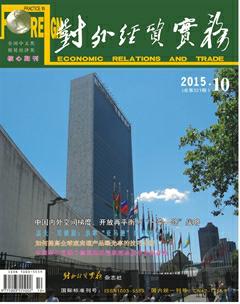中國內外空間梯度、開放再平衡與“一帶一路”戰略
徐德友

中國內部和外部都存在明顯的空間梯度發展差異,并由此在亞洲形成了包括中國東、中、西部在內的拓展版“雁陣模型”,這客觀上要求中國應該實施更均衡、更全面的國內開發政策和對外開放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因此應運而生,它是促進中國內外部開放再平衡的重要載體。加快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既能對外拓展中國自己的規則圈,又能與國內正在實施的中西部區域開發戰略相結合,形成內外聯動式發展。并在中國內部與外部空間梯度下,從大戰略上實現對外開放的內外部空間再平衡。
一、中國內外空間梯度下的拓展版“雁陣模型”
中國是世界上典型的發展中大國,廣袤的國土空間中存在著明顯的發展梯度,具體包括:一是要素價格梯度,即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在東中西部存在顯著差異;二是市場需求梯度,即不同地區間的人均收入、消費水平和需求層次明顯不同;三是產業結構梯度,即中國東中西部甚至區域內產業表現出多元化、階段化的特征,如中西部很多地區以資源型產業為主導,缺乏帶動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東部沿海地區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較快,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生存空間不斷萎縮。空間梯度是大國綜合特征的重要表現,它一方面令中國存在著巨大的區域發展差距,不平衡的增長使得中國在高速增長了三十多年后依然是中等收入經濟體;但另一方面,它又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更長久的增長過程,以及更廣闊的空間縱深。正是這種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梯度緩沖,中國經濟轉型、產業結構轉換“軟著陸”的可能性會更大,過程可能也更長,回旋余地也更大。
若在更廣闊的空間維度看,就會發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同樣存在著明顯的空間發展梯度。如果把中國的省與周邊國家并列比較,把中國的東部、中部、西部同亞洲的不同區域(中亞、東南亞、南亞)相比較,可以明顯發現,兩個維度上的比較都呈現出明顯的空間梯度:中國內部的東部、中部、西部與外部的中亞、東南亞、南亞形成了層層遞減的梯度,具體到國內典型省份或國外經濟體層面,中國內部的江蘇、廣東、湖南、河南、四川、云南,由東到西形成遞減梯度線;這條遞減梯度線延伸到中國以外,到印度尼西亞、越南、烏茲別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梯度差”的存在是形成中國資本、技術、裝備、產品、服務“走進去”(到中國中西部地區)和“走出去”(到亞洲周邊其他地區)的重要基礎性動力,同時也是中國內外部區域發展和開放失衡的重要表現。
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之前已經利用“雁陣模型”對這種梯度發展模式進行過形象而深刻的分析,但隨著二戰后亞洲經濟地理的多次變遷,本文認為,如今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囊括范圍更廣的拓展版“雁陣模型”(如圖1):日本為雁頭,上世紀60年代一些通用型產業和技術成熟后,通過產業轉移將其成熟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地區(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70-80年代亞洲四小龍發展起來后,再將產品的生產線轉移到四小虎(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和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然后90年代到21世紀初,發展起來的四小虎和中國沿海地區再將已經標準化的技術和產業轉移到其他亞洲欠發達地區(如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度等)和中國內陸地區。此拓展版的“雁陣模型”體現了亞洲經濟發展巨大的多樣性、異質性和復雜性,集中表現為以空間廣闊性引致的空間梯度特征。在此拓展版的“雁陣模型”中,基于廣袤的國土面積、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巨大的區域差異等大國特征,中國既做了雁身,也當了雁尾,換言之,中國處在此“雁陣模型”的中間地帶,其內部和外部均存在著顯著地空間發展梯度。中國內外部的空間梯度致使中國在亞洲經濟地理上面臨著雙重區域發展失衡:內部形成了東、中、西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外部也形成了東北亞、東亞、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幾乎完全迥異的經貿合作格局。在此梯度差的動力下,新一輪的亞洲經濟地理變遷已經開啟,突出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國內空間梯度引致產業由東部沿海向中西部轉移之趨勢已形成。作為一個存在巨大空間發展梯度的大國,中國區域間的要素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差異并不亞于國家間的差異,這種空間梯度正是中國區域間發生產業轉移的基礎性動力。當前大量東部沿海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正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發生在中國的區際產業轉移可以看作是國際產業轉移在中國的延伸,即拓展版“雁陣模型”的國內部分。因為更多層階的區域發展梯度,中國其實是參與了至少兩次國際產業轉移(見圖1):第一次是東南沿海地區承接了來自東亞地區的產業轉移,第二次是中西部地區承接了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國內由沿海到內陸、由東部及西部一直持續進行著產業的轉移和擴散,由此推動了中國空間漸次推進式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必然表現出的特征。
第二,外部空間梯度使得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等國家經貿合作潛力和動力不斷趨強。伴隨著中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的是,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中亞等地區的貿易、投資往來日漸便利化,中國處在高梯度的優勢明顯,無論是相互投資還是貿易,其增速都超過了平均增速,例如,中國與東盟建立自貿區后,雙邊相互的進出口貿易平均增速達到10%以上。由于東南亞、南亞等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較快,與中國的空間距離也相對更近,其產業結構與中國目前產業轉型升級的契合性、互補性更強,中國國內龐大的市場為這些地區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因而,中國在同這些地區進行經濟往來時的主導性相對更大。更關鍵的是,與這些地區的經濟合作內容更廣,范圍更大,不僅有傳統的進出口貿易,還有相互間雙向的直接投資,這些地區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更有基礎設施投資合作、裝備制造的全產業鏈出口以及技術、人才、文化的交流。
內外部空間梯度下的拓展版“雁陣模型”使得中國的區域發展和對外開放呈現出一些獨特的空間模式:產業發展東強西弱,對外開放海強路弱,貿易體系大國強小國弱。隨著當前世界經濟低迷的持續、國內區域開發格局的變遷和全球貿易體系的重構,內外空間梯度下的拓展版“雁陣模型”必須適應新的變化、謀劃新的戰略。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區梯度開發、對外開放力度,促進與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等陸上周邊國家的合作,便是當前國內政策和對外戰略的重要著力點。
二、中國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內外開放的再平衡
在中國內部外部空間梯度影響下形成的拓展版“雁陣模型”,決定了中國未來應該實施更為均衡的國內開發政策和對外開放戰略,以實現中國內外部發展的再平衡。這是“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和實施的重要現實基礎,在國務院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也明確了在此大戰略下中國各地方的開放態勢:“一帶”通過陸路將我國中西部地區與中亞、西亞、歐洲連接起來,擴大中西部地區的開放態勢;“一路”通過海路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與東南亞、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連接起來,優化東部地區的開放格局。
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的對外開放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2年,即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階段是從1992年到2001年,即從全面深化市場體制到加入世貿組織;這兩個階段相當于“以對內市場化改革迎接對外全球化開放”。第三階段是從2001年到2012年,即加入世貿組織的過渡期,在此階段中國實現了“入世”所帶來的開放紅利,也成功達到了“以對外貿易自由化、引資便利化促進國內改革”的目的。通過這三個“大約十年”,中國初步探索出了以改革開放謀發展的漸進式改革路徑。第四階段是從2012年到今后的一段時間,即國內深化改革與對外高度開放相互融合和協同發展階段,目前的國內外的形勢和條件已經體現出這種訴求。
從國內空間上看,前三個階段的對外開放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對外開放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沿海地區,面積廣袤的中西部地區、沿邊地區開放程度嚴重滯后,而這也正是中國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從外部空間上看,前三個階段的對外開放也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對外開放的目標對象主要集中于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以及WTO等多邊貿易協定,對發展中經濟體和區域、雙邊協定關注不足,特別是與中國空間距離臨近又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等亞洲地區,限于產業結構的滯后、單一,跟中國的經貿往來與其經濟規模并不匹配。基于此,當前新一輪的中國對外開放對內而言應該是全覆蓋的,對外而言應該是全方向的,以從大戰略上實現對外開放的內外部空間再平衡。
對國內區域開放而言,“一帶一路”涉及和覆蓋了全國所有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西北地區是“一帶”的交通樞紐和核心經濟區,中國與中亞、西亞經貿往來的必經之路,涉及地區包括新疆、甘肅、青海、陜西、寧夏,“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使其深處西北內陸、沿邊沿境的區位劣勢轉化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優勢。東北地區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一端,聯通著俄羅斯、蒙古,通過對俄、對蒙的公路、鐵路等通道,提升內蒙古、黑龍江、吉林和遼寧的開放水平。西南地區與東盟國家陸海相鄰,處在中國連接東南亞、南亞的核心位置,也是“一帶”和“一路”的交匯處,涉及廣西、云南、西藏和貴州,“一帶一路”進一步強化了廣西和云南作為西南、中南地區開放新戰略支點的地位。不沿邊的內陸地區是“一帶”的腹地依托,依托中歐鐵路通道,內陸地區的重慶、成都、武漢、合肥、長沙、南昌、鄭州、太原、西安都是“一帶”的東端出發點,涉及到的重慶、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山西等省份,也是當前東部沿海產業向西轉移的主要承接地。沿海和港澳臺地區都是“一路”的覆蓋范圍,涉及到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和香港、澳門和臺灣等地區,這些地區經濟發達、開放度高、輻射帶動能力強,引領著我國的對外開放的競爭新優勢。由此可見,“一帶一路”是一個全國聯動的戰略,沿海沿邊地區是通道、窗口;內陸地區是支撐和依托,而且形成內外聯動式發展,極大地拓展了區域開發的廣度、深度和層次性。
對國外空間開放而言,“一帶一路”具備明顯側重向西開放、向新興經濟體開放、向周邊發展中國家開放的戰略意圖。中國全域是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東部起點,終點大多位于西端的歐洲和地中海沿岸,途徑的沿帶沿線國家幾乎覆蓋了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歐、中歐、南歐、西歐、北非、東非的大部分地區,雖然這些地區與中國經貿往來密切,相互間的產業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但一直以來,中國與這些地區經濟合作的廣度、深度、層次并不高,彼此間的共同利益、貿易投資的需求應進一步強化和提升。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成功繞開了美國、日本這兩個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主導國,從而在亞太和歐洲間構建和打造起屬于自己的“圈子”:以“一帶一路”為載體,中國優先與沿線國家進行雙邊或區域自貿協議談判,通過成立多邊金融開發機構進行基礎設施投資,使中國與沿線國家合作更加緊密,逐步構筑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雙邊經貿網絡,以形成更加平衡和多元的全方位開放格局。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是要推動區域內各國以實現“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為目標,這樣就避開了美國長期以來對國際規則的壟斷和控制。一直以來中國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現行國際經貿規則的適應者、遵循者,從來都要順應美國為主導制定的游戲規則;現在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已經有能力去參與、影響甚至主導國際游戲規則,去推廣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此,在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體系中,中國“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從而“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這是中國從開放大國邁向開放強國的必經之路。
三、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著力點:內外空間梯度下的“移、通、融、接”
當前,“一帶一路”戰略已經從理念轉入到全面實施階段,研究實施這一戰略的著力點十分重要。筆者認為在內外部空間梯度的作用和影響下,“一帶一路”戰略的著力點應該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一) 鼓勵東部沿海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沿“一帶一路”進行內外雙向梯度轉移
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框架下,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特別是低端加工、生產、組裝等低附加值環節,向外轉移之趨勢已然形成,轉移的目標方向有兩個:一個是中國中西部的內陸地區,一個是海外地區,主要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觀上看,東部沿海制造業向中西部轉移和向海外轉移是存在沖突的:東莞的鞋企向越南轉移的多了,就意味著向湖南轉移的可能就少了;實則不然,兩種轉移模式更多是一種互補關系,而非競爭關系。例如,東南亞、南亞雖有勞動力和土地廉價的優勢,但產業配套欠缺、基礎設施落后、工人勞動技能不足,加之原料、配件還需從國內運輸過去,所以在海外生產的綜合成本并沒有明顯優勢;但在海外生產可以規避歐美等發達市場的貿易準入門檻,例如目前歐盟、美國對東南亞部分國家的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實施零關稅政策,而對從中國進口的同類產品則保持10%以上的進口稅,這使得海外采購商更偏向于從中國企業的海外工廠進貨,從而大幅拉低自己的銷售成本,還包括在海外生產也能部分降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

把生產基地從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勞動力、土地等生產成本,但更多的情形是,為了保持高端或工藝、技術復雜類產品的制造能力,多數制造業在向中西部轉移的同時伴隨著生產工藝的升級,這樣做也是為了贏得在日漸龐大的中西部市場的競爭份額。因此,中國東部沿海制造業依托內外發展梯度同時向國內中西部、海外欠發達國家進行雙向轉移,這是企業在更大范圍內優化生產和市場布局的體現,也是中國從產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重要路徑,兩者不是替代關系,而是為中國制造提供了新渠道、新優勢,更多是一種互補模式。
(二) 以與中國互聯互通為目標,重點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
基礎設施聯通是加快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基礎性條件。從目前來看,不論是印尼等東南亞國家,還是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亦或是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在交通、電力、通信等基礎設施領域都面臨著資金、技術、裝備、經驗缺乏等問題,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普遍的需求。而中國在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有很強的投資、建設、營運能力,加之當前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相關重化工產業,如鋼鐵、水泥、工程機械,國內多存在產能過剩、價格低廉的特征,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能夠帶動國內資本的輸出并稀釋部分行業過剩產能,從而有利于將國內的技術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同時,在硬件日漸完善時會加快推進建立統一的全程運輸協調機制,促進國際通關、換裝、多式聯運有機銜接,更有利于實現國際運輸便利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海外修建交通、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面廣、內容多,較之一般貿易行為,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更大,必須充分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進行更為周全和審慎的評估和決策。對于中國來說,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中,要充分發揮中國的主導和輻射作用,特別是要強化和完善中國西部廣大邊境地區與周邊國家的公路、橋梁、鐵路等交通基礎設施,從而提升多條“一帶一路”通道的運載內容、運載能力、運行效率和運行速度。通過加快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中國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互聯互通,也必將使中國西部地區從過去我國對外開放的邊緣地區變為未來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
(三)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構建高標準自貿區網絡,以實現相互間經濟發展的深度融合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的各地區(包括中國東西部和外部國家)經濟發展梯度明顯,產業結構互補性強,相互間自貿區的建立有助于貿易伙伴國之間的產業分工,使資源配置更合理,成員國能在更大市場范圍內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提高本地區產業競爭力和整體福利水平。2010年以來,中國先后與東盟、巴基斯坦、新西蘭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并實施了自貿區協定,目前正在談判的自貿協定有8個,涉及23個國家,分別是中國與韓國、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斯里蘭卡、挪威和澳大利亞,以及中日韓三國自貿協定、區域全面伙伴關系(RCEP)和“中國-東盟”升級版。但與歐盟、日韓等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在雙邊、區域自貿區的建設方面起步較晚,簽署的自貿協議相對較少,且涵蓋的國家、貿易領域和標準層次相對較低。從區域多邊合作的角度看,中國正在參與的RCEP和亞太自貿區(FTAAP,由中國在2014年APEC會議提出)是未來中國參與亞太區域內一體化的重要實現路徑;從雙邊合作的角度看,“一帶一路”為中國與其沿線國家建立高標準自貿區、促進區域經濟深度融合帶來了新機遇。
因此,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建立新的自由貿易協定應側重于高標準的開放性政策,以實現從貿易、投資的“相通”到經濟的“融合”,包括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制造業領域的全面開放,以及在金融、醫療、教育、文化等服務業領域的高度開放,降低相互間在證券投資、并購投資、綠地投資等方面的投資準入門檻。以高標準自貿協定的談判和簽署,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打造規范、公正、透明、相對可預期的市場經濟環境,降低雙方在跨境生產和貿易供應鏈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提升上下游、產供銷、內外貿互聯互通的一體化效率,使雙方的人員、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和產品、信息、服務等產出相互更自由而高效地流動,從而最終實現相互間經濟發展的深度融合。
(四)適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多樣性,充分利用已有機制化合作和非機制化合作并協調推進兩者的對接
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是一種戰略,而對沿線國家和周邊地區而言,更多的是一種新型區域合作機制,這種合作機制顯然不同于現有的任何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如自貿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一體化等。事實上,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多樣性和經濟梯度性,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也很難形成統一的、覆蓋整個地區的自由貿易區或其他更高級的區域一體化組織形式。作為國內發展同樣差異性、多樣性巨大的中國而言,也并不期望通過“一帶一路”來打造一個高標準的區域一體化組織,也不期望以此組建一個具有強制規范力的排他性國家組織。對所有參與國而言,“一帶一路”應是一個開放的、多元化的區域合作大框架和基礎性平臺,在這個框架和平臺上,允許機制化合作(如自貿區)和非機制化合作(如上海合作組織)并存,其關鍵是要做好機制化合作與非機制化合作的對接工作。
因此,“一帶一路”未來的運轉應該是機制化合作和非機制化合作兩條腿走路,而且要兩條腿要配合好、協調好、對接好。一方面繼續推進與沿線條件成熟國家的自貿協定談判,推進高質量、深層次、機制化的合作機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好現有的非機制化的多邊合作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SCO)、亞太經合組織(APEC)、亞信會議(CICA)、中國-東盟“10+1”、亞洲合作對話(ACD)、中國-海合會戰略對話、亞歐會議(ASEM)、中阿合作論壇、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也包括各種區域合作論壇、博覽會、洽談會等交流活動。不同類型的合作機制相互對接,不僅能較好地適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樣化的政治制度、歷史傳統、文化、宗教,而且還能將未來的合作區域延伸到歐洲和非洲,實現與“一帶一路”的開放性相匹配。▲
(本文發表時對原文進行了適當壓縮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