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與傳媒行業有“對撞”機會么?
——專訪新智元創始人楊 靜
本刊記者|曹素妨 實習記者|林暢
人工智能與傳媒行業有“對撞”機會么?
——專訪新智元創始人楊 靜
本刊記者|曹素妨 實習記者|林暢
深度學習的智能到底有多“深”?

楊 靜新智元創始人
由谷歌開啟的“機器學習計劃”吸引了全球數以千計的科學家參與,Facebook、亞馬遜、百度、阿里、訊飛等眾多科技公司正紛紛“入手”潛心研究這一領域,昭示著人工智能時代的盛世即將來臨。
《中國傳媒科技》:度秘、騰訊寫稿機器人、小冰、Siri等智能助手的野蠻生長背后,您有怎樣的冷靜思考?
楊靜: 應該說度秘、小冰和Siri是智能助手或對話機器人,而騰訊寫稿機器人是一種專家撰稿應用。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智能助手向智能人機交互模式的轉化還有個過程。例如語音識別、語音合成、情感分析、認知分析能力的提升,也就是需要進一步人格化。我認為從某個專業領域做起,將專用智能助手先做到智能程度滿足特定需求,可能是一種更好的漸進方案。例如百度倡導的3600行+。
《中國傳媒科技》:如何解讀深度學習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分量?能夠引爆人工智能的“讀心術”?
楊靜: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是人工智能甚至機器學習領域的一個分支,專注于讓計算機神經網絡學習如何像人類一樣感知與思考。從本質上說,深度學習是一項“大數據工程”,為機器賦予了充足、高效而相對低廉的計算能力,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海量數據的學習。由于該領域與移動互聯網時代緊密相連,它正迅速成為包括百度在內的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優先發展領域。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這項技術對人類生活的改變將是巨大的——智能圖片搜索、智能語音識別與輸入、人臉識別、無人機送貨、無人駕駛汽車乃至更宏大的工業4.0等等,都離不開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而這也是各個IT巨頭不遺余力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動因所在。
《中國傳媒科技》: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對于資本的投入要求很高,也直接關乎研發周期、成果轉換等。缺乏產業基金及社會機制的保障,是否會遲滯中國在此領域的競爭力?
楊靜: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投入成本很高,缺乏產業資金和智慧,在企業研發的時候,它會確實存在一種試錯的成本。有的企業對人工智能的研究缺乏連續性,特別是資本市場出現泡沫以后,也有部分人工智能或者是機器人的企業在融資方面不像以前那么順利,但是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中國在智能領域的研究還是比較先進的,我們僅次于美國。
綜合而言,無論是國家資金投入,還是企業或者是一些創投的資金對這方面的關注和投入力度還是比較大的。重要的一點是要有持續性,因為人工智能的研究可能很難短期實現巨大突破,并且相關研發成本較高,所以有一些企業可能會選擇撤資,或者是轉移方向。無論是國家戰略的層面還是企業戰略的層面,都需要保有一種持續性,把人工智能研究繼續推進下來,因為這畢竟是我們在世界科技最前沿的領域之一。
《中國傳媒科技》:目前創投界的熱捧是否可以緩解這樣的矛盾?
楊靜:實際上現在缺乏針對性,我很認同前期科學界和企業界的工作做的還是比較嚴謹,但是創投這方面跨界的情況嚴重,專業程度略有欠缺,而且相關配套也欠缺嚴謹性、科學性。創投界的熱捧有時不是特別符合科學規律。可能就是跟風和炒作,當然我認為這種熱捧對行業有一種積極的作用。但也希望今后的投資更加的理性,并且更加具有持續性。
《中國傳媒科技》:您認為當下最需要進行大資金長期性投入的是何領域?如何形成可持續動力?
楊靜:在高性能計算方面,奧巴馬提出為期五年的超級計算機計劃,咱們國家目前在這方面沒有一個長期的規劃。對于算法和高性能計算的研究,應該從企業和社會之間形成合力,共享基礎設施。超級計算機目前存在很多問題,部分超級計算機利用率停留在10%左右,是對國家資源的浪費。我們將來怎么產、學、研共用,還是需要多動用國家、社會和企業三方的資源,高性能計算和計算智能方面的研究還要持續推進。
人工智能與傳媒行業有“對撞”機會么?
中科院復雜系統管理與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王飛躍在一次演講中提到X5.0時代,指出在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網絡化之后,我們進入了第5個技術發展階段:平行化,就是以虛實平行互動為特征的智能技術時代。在這個“平行世界”里,人工智能會不會與傳媒的世界相交?
《中國傳媒科技》:人工智能可以從三個層面去理解:計算智能(會算和存儲)、感知智能(機器擁有和人一樣的五官技能會聽會寫)和認知智能(會思考會學習)——超智能。這些會與傳媒應用產生哪些交集?
楊靜:對于數據的存儲以及一些大數據的分析、運用方面,目前傳媒行業做的還是不夠的。但是應用的前景以及層面是非常廣泛的,包括可視化新聞、數據新聞等等,這些都屬于計算智能范疇。感知智能就是語音方面的,語音識圖、語音圖像等。比如,語音機器人可以與新華網融合“說新聞”。
另外,在傳媒與用戶的交互方面可以使用機器人來進行操作,使其作為一個智能助手或者智能伴侶,專門為用戶提供其想要的新聞信息。
《中國傳媒科技》:對于無人機新聞,在數據庫與LBS結合上產生動態時間軸的對比,會給新聞傳播帶來怎樣的差異化驚喜和紅利?
楊靜:舉個例子,像尼泊爾大地震以后,百度有一個全景式的掃描,這個全景式掃描就是一個對比數據,原來的這個地方是什么樣,后來這個地方是什么樣,它是對重建的持續跟蹤。拿地震來說,記者是進不去現場的。天津爆炸或者是汶川地震,通過無人機進入現場進行數據采集,可以看到重建的一個狀態,每天是什么樣的,形成對比,也可以成為歷史性的一個數據化史料。
以前沒有無人機的時候,像挪威有一個電視新聞欄目,叫慢新聞,直播一艘遠洋油輪一直在大西洋上漂流的情景,每天都在播,極度無聊。但大家更關注的是動態的對比,不可能一直看這個。比如說咱們的冬奧會場館是怎么建設的?從無到有的過程與記錄,更能凸顯出無人機的重要性。
《中國傳媒科技》:百度布局人工智能,推出智能機器人“度秘”,其新戰略是搜索和服務,搜索是連接方式,服務是變現方式。而有效的資訊連接和服務是媒體的本質,這將給媒體行業帶來又一大挑戰,對此,給媒體以怎樣的啟示,以及媒體行業該有怎么的動作?
楊靜:我覺得百度現在的方式其實是O2O,還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多一些,并沒有特別強調資訊服務,反而強調裂變而來的3600行。這最底層的連接3600行,在教育、醫療、金融、餐飲等各個領域都對接很多服務,對于百度來說生活服務可能是它們的重點,“度秘”人工智能機器助理就是其O2O服務的一個入口。
對我們媒體來講,內容資訊的增值服務做的不夠好,建議可以從這方面下一些功夫。另外,媒體和用戶的關系哲學,可以參考借鑒百度“度秘”智能伴侶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說,媒體與用戶是伴侶的關系,媒體轉變為用戶的資訊助手或者資訊伴侶,來滿足用戶的資訊需求。
因為機器人不能理解新聞事件背后的因果關系,無論是線上的資源還是線下的資源,我們媒體擅長對深度的宏觀把控,以及對資訊背后信息的理解。在人的認知能力方面,我們能做到的更多,也比互聯網公司更有優勢。實際上,各種智能助手離認知智能的實現還比較遙遠,所以這是媒體可以著力的關鍵所在。
《中國傳媒科技》:騰訊也開始布局智能產業,最近騰訊財經開發了自動化新聞寫作機器人Dreamwriter,根據算法在第一時間自動生成稿件,瞬時輸出分析和研判,一分鐘內將重要資訊和解讀送達用戶。騰訊自動化新聞寫作機器人的出現,坊間便有了關于“記者下崗”的各種猜測,對此,您怎么看?

楊靜:自然語言理解以及真正的認知智能,是連IBM這類國際領先公司也不完全具備的。騰訊的新聞寫作機器人,還不是通用領域的機器人,對新聞行業形成不了有規模的沖擊。微信和微博,形成的是兩個超級壟斷的平臺,這兩個平臺已經影響了傳統媒體新聞來源和新聞發布渠道的主體性。微信內有上千萬個公眾號,就有上千萬個信息來源和發布渠道,對傳統媒體確實存在沖擊。
這個寫作機器人對騰訊本身來說并不特別,真正看騰訊財經機器人寫的財報的受眾,我認為不會很多。而財報這類的稿件,在財經稿件中占比也比較低,我不認為會對整個的格局造成很大的沖擊。
目前這些研發與嘗試,都處于初級階段,但確實是給傳媒界的一個信號,但若要產生巨大的沖擊,至少要三到五年的過程。美聯社已經用機器人寫稿一段時間了,而且做的不錯。記者在美國地位低,收入也不高,無論是從大學教育還是從業或者是我們職業上升的渠道來看,已經是非常狹窄了。
在中國也是一樣,同樣大學畢業,一個程序員——計算機系畢業的碩士生年薪可能是五十萬,但現在記者和編輯月薪一萬就非常高了。這種擠壓不是機器人造成的,而是整個社會結構轉變造成的新聞行業逐漸下沉,導致記者這個職業本身下沉。
記者不會完全下崗,只是部分記者下崗,可以說最像機器人的記者先下崗。但是如果記者本身具有一些創意和創新,而市場又給了記者一些機會和空間,這些記者就不會下崗,反而會大有成就。所以,記者下崗不能一概而論。
從“看到”到“看中”如何行引爆趨勢?
從《靈魂機器的時代》到《奇點臨近》的一次閱讀之旅,也許就能點燃一個人對人工智能的濃烈興趣,以及由此而生的對人工智能的執著信仰,再到有所作為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效力。這也是人工智能帶動的一場蝴蝶效應。
《中國傳媒科技》:從《中國經營報》《精品購物指南》、中國經濟網等媒體的經營顧問,到中國人工智能學會社會計算與社會智能專委會秘書長,再到【新智元】創始人,如此熱情的轉變投入到人工智能事業,從中,你看到了什么?又看中了什么?
楊靜:從一家跨國廣告公司的媒體咨詢總監到中國經濟網經營顧問,過去若干年,我的夢想是辦媒體,以及組織一個跨界的中國頂級精英俱樂部。我曾經想組織一個財經方面的百人會,但由于各種條件的制約沒有實現。幾年前,我對庫茲韋爾的幾本書非常著迷,包括《靈魂機器的時代》《奇點臨近》等,所以對人工智能特別感興趣。我夢想把相關的技術領袖聚集在一起,組織一個AI俱樂部,整合社會資源,實現人工智能的夢想。過去幾年,在微博上與中國自動化學會副理事長王飛躍老師和中國計算機學會高性能計算專委會秘書長張云泉研究員有不少互動,此外也與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的幾任主席熟悉。
去年我開設微信公眾號以后,雖然曾定位于泛財經科技,但后來發現大部分訂戶都來自計算機界。通過參加YOCSEF的會議,以及組織《奇點臨近》主題沙龍,我發現自己對人工智能科技開始產生一種執著的信仰和超級濃厚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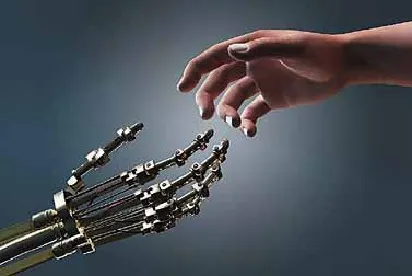
特別去年參加了百度大腦與訊飛超腦的發布會以后,我就將自己的公眾號與微信群明確定位在人工智能方向。王飛躍老師讓我擔任中國人工智能學會社會計算與社會智能專委會秘書長,我也非常樂意參與組織人工智能領域的活動。
之后開始參與主辦一系列的沙龍、論壇、特輯等活動,可以說,過去一年的時間里,我做過的事情和產生的影響力可能比以往十年或者二十年產生的影響力還要多,創建的自媒體在社會上產生的能量也不亞于一些專業媒體,我也逐漸成為了人工智能界的一個標簽和符號。
我認為是興趣驅使我走入計算機這個圈子,信仰使得我熱愛人工智能事業,堅信人工智能將是世界未來的發展趨勢。
《中國傳媒科技》:“新智元”自媒體剛剛創建,似乎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也吸引了投資界的很多目光,接下來,“新智元”作為一家自媒體會有怎樣的定位和發展目標?
楊靜:互聯網媒體和自媒體的快速更新迭代和創新創業的寬松環境,造就了我們這些在創新邊緣的一群人,以及我們所產生的一種社會效力。
我現在這個公司,LOGO還沒有弄好,但是每天都有合作伙伴,也有很多的投資者來找我們:你有什么計劃?你的商業計劃是什么?其中一些我也非常感興趣,還有一些甚至主動打來電話邀請我去他們公司,去講我的商業發展計劃等等。我覺得這種社會聚焦以及激勵創新創業的社會氛圍給了我很大的觸動。
接下來是一個新智能的時代,世界的未來就是智能對決的一個系統性競爭,那么我們中國能不能在未來的競爭當中取得優勢?我們中國的文明、我們中國的智慧能不能在未來人機融合的智能化時代,還保有我們的競爭力和生命力?其實無論在傳統媒體,還是在新媒體,產業界、學術界也好,我們共同守護的是我們中國的基因和智慧,如何把我們先輩傳承下來的文明在未來全球化的新智能當中傳承下去?這是我們共同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新智元”定位于“智能+中國的資訊社交平臺”,致力于推動中國從互聯網+邁向智能+的新紀元。重點關注人工智能、機器人、大數據、虛擬現實、量子計算、智能醫療等前沿領域發展,關注人機融合、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革命對人類社會與文明進化的影響。“新智元”的發展目標是成為智能+中國的主平臺,領航中國新智能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