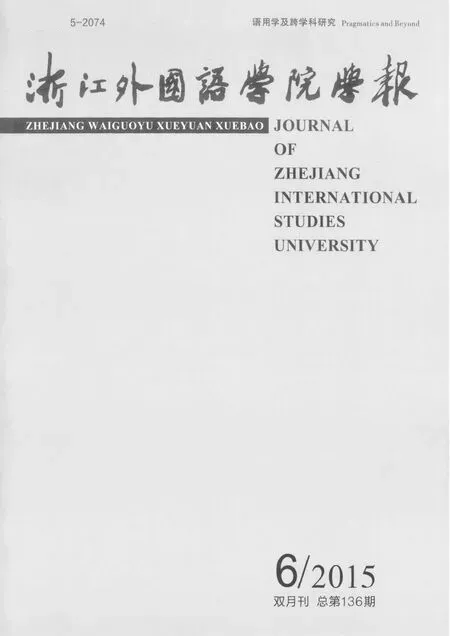城市居民休閑活動對幸福感的影響研究
——以杭州市為例
蔣 艷
(浙江外國語學院 國際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2)
城市居民休閑活動對幸福感的影響研究
——以杭州市為例
蔣 艷
(浙江外國語學院 國際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文章以休閑動機為導向,將休閑活動分為“休息放松”“享樂”“社交”“運動”和“自我提升”,研究了城市居民休閑活動對其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在杭州各主城區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城市居民休閑活動中只有享樂活動對幸福感沒有顯著影響,其他類型休閑活動都會對幸福感的一個或多個維度產生顯著影響。提升城市居民休閑活動的頻率和質量需要引導休閑活動向更豐富的方向發展,并有針對性地配套免費休閑場所和設施。
城市居民;休閑活動;幸福感;影響機制
一、引言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居民的休閑活動日益普遍和多元化,國家也出臺相應政策推動居民的休閑活動,如2013年初正式發布的《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①。與此同時,居民對幸福感的追求逐漸提上日程。中央和地方政府開始重視幸福感。許多機構對居民的幸福感進行了調研,2012年國慶期間央視新聞頻道連續9天播放《你幸福嗎》街訪紀實節目②,并成為當年下半年的熱門話題。通過休閑活動提升幸福感的觀念日益受到重視。作為“東方休閑之都,品質生活之城”,杭州有相對發達的社會經濟背景和較為深厚的休閑文化傳統,城市居民的休閑活動較為頻繁,而且自2007年開始評選“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以來,其一直名列前四,2007—2009年連續三年位居第一③,這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樣本。通過探索城市居民休閑活動對其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引導杭州城市居民休閑活動健康發展,對其他城市乃至整個國家都有借鑒意義。
二、研究綜述
目前,關于休閑活動的定義已有很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許義雄[1]、呂建政[2]和劉泳倫[3]6認為,休閑活動包括休息、自娛、非功利性的知識學習、技能提高以及主動參與社會活動以施展創造才能,自由支配、不受拘束、非工作性和非經濟性是其顯著特征。陳祥慈[4]12提出,在休閑時間內所從事的各項活動,都可被視為休閑活動。謝秀芳和鄭麗霞[5]將休閑活動的內涵總結為一種在個人自由時間內自主選擇的,以滿足個人需求為出發點,以快樂、放松的方式來達到修身養性、擺脫壓力目的的活動。歸納起來,本研究認為,休閑活動是指除去工作、學習、家務、睡眠之外的自愿從事的活動。休閑活動有兩大特征:一是自由選擇,二是不以生存為目的。
很多學者都試圖根據自己的研究目的對休閑活動進行分類,但是列出所有人們可能參與的休閑活動是相當困難的[6]6。休閑活動的分類方式極其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素分類法和主觀分類法,還有多元尺度評定法等。采用哪種分類方法,取決于具體的研究對象和目的。主觀分類法比較靈活,較適用于本研究。本研究以休閑動機為導向,借鑒文崇一[7]、王煥琛[8]、李志恭等[9]的分類方法,將休閑活動分為“休息放松”“享樂”“社交”“運動”和“自我提升”。本研究同時參考了Stebbins、Gilbert等[10-12],將休閑活動項目分為深度休閑(Serious Leisure)和隨興休閑(Casual Leisure),休息放松、享樂以及社交活動屬于隨興休閑范疇,而運動和自我提升活動屬于深度休閑范疇。
目前,休閑和旅游研究領域對幸福感的描述主要有快樂、生活品質和生活滿意等[13]。研究幸福感的文獻通常認為happiness和subjective well-being可以通用[14]6,但后者顯得更有學術性,也更為接近幸福感的本義。關于幸福感的概念界定有很多,目前最廣為接受的幸福感定義出自Diener及其研究伙伴[15-16],他們認為幸福感是個體主觀上對現在的生活狀態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狀態的一種肯定的態度和感受,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感體驗(包括正、負面情感)兩部分。這一觀點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理論和實證支持[17-18]。通過對大量文獻的整理可以發現,幸福感具有主觀性,都是基于事實而作出的主觀判斷,因而本研究對幸福感的測量采用自陳量表的形式。幸福感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有“幸福的設定點”[19]12。幸福感具有綜合性特點,本研究傾向于從兩個方面4個維度來衡量幸福感:一是幸福感知度,即對幸福感的自我主觀評價;二是幸福感的多維主觀評價,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感體驗等兩個層面的3個維度,即生活滿意度、正面情緒和負面情緒。
關于休閑活動和幸福感關系的研究,國內外學界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亞里士多德認為,休閑活動本身可以產生快樂和自足,這就是一種幸福④。休閑是自愿參與的活動且不需要考慮生存的問題,這使得休閑活動容易帶來幸福感。很多學者的研究表明,休閑活動是幸福感的最佳預測因子,是幸福感的最重要來源之一[20-28],深度休閑會促進幸福感的提升[29-47]。Becchetti等[48]認為,休閑活動有助于提升生活滿意度,比如社交性休閑活動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積極影響。Hills等[49]認為休閑活動可以改善短期情緒,比如運動可使情緒發生明顯的、短期的積極變化[50-51]。盡管如此,將城市居民作為一個單獨的群體,定量研究其休閑活動與幸福感關系的研究仍不多見,兩者之間的關系有待于進一步揭示。
三、研究過程
(一)研究假設
大量研究已證明,休閑活動對幸福感具有促進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休閑活動參與頻率越高,幸福感知度越強,生活滿意度越高,正面情緒越多,負面情緒越少。當然,羅伯特·斯特賓斯提出,并非所有的休閑活動都能帶來幸福狀態[31]。進而,本研究在對休閑活動分類的基礎上,分別分析不同類型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的關系。
(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城市居民的休閑活動對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問卷的具體設計經歷了多次征求意見和修改過程,并結合預調研情況進行了個別調整,最終完成了正式的調查問卷。量表共有4個,分別是個人基本信息表、幸福感知度量表[52]30、生活滿意度量表[53]和情緒測量量表[54]。為了保證問卷測量的統一,調查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休閑活動參與頻率設定為“從不”“極少”“有時”“經常”“幾乎每天”5個等級,按照1—5分計分。對于幸福感知度的測量,選擇項設定為:1=非常不幸福;2=比較不幸福;3=沒有強烈感覺;4=比較幸福;5=非常幸福。對于生活滿意度的測量,選擇項設定為:1=非常不同意;2=比較不同意;3=不確定;4=比較同意;5=非常同意。
(三)問卷調查
本研究采用簡單隨機抽樣方法對杭州城區的居民進行抽樣。在具體方法上,主要是通過現場隨機發放問卷的方式獲得數據。現場問卷發放主要是選擇廣場、商場、超市、小區公共游憩區等人流量較大且大部分人處于停留狀態的公共場合。為了實現抽樣樣本能夠覆蓋整個杭州城區,本研究在調研地點的選擇上盡量涵蓋杭州的城東、城西、城北和城南。2012年10—11月在杭州城區的廣場、超市、商場、居民小區或公園等公共場所,發放并回收了1025份問卷,回收率100%。經篩選后,得到952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率為92.88%。問卷分析使用SPSS18.0軟件。
一般認為,當偏度絕對值小于3.0,峰度絕對值小于10.0時,表明樣本基本上服從正態分布,可以展開進一步的分析。檢驗表明所有選項的偏度和峰度絕對值都小于3.0,可認定本研究的大樣本調查數據服從正態分布。幸福感量表樣本的KMO檢驗系數為0.864,巴特利特球度檢驗的顯著性是0.000,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對幸福感量表內部一致性進行分析,得到總量表克朗巴哈α系數為0.861,表明量表內部一致性較好;各層面量表克朗巴哈α系數均大于0.8,信度可以接受。研究樣本中被調查者的人口學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被調查者的人口學特征描述

統計內容頻率有效百分比(%)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職業月收入男44947.2女50352.815—2420621.625—3440542.535—4417918.845—6012713.361歲以上353.7初中及以下596.2高中/中專15015.8大學專/本科63166.3研究生及以上11211.8未婚39241.2已婚53556.2離婚、分居或喪偶252.6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12613.2事業單位員工13914.6公務員323.4商貿服務和銷售人員10210.7普通企業員工20521.5自謀職業者768.0工人282.9學生697.2教師636.6離退休人員515.4下崗待業人員404.2社團社區工作者212.21500元以下899.31501—3000元24625.83001—5000元32634.25001—10,000元21422.510,001元以上778.1
四、休閑活動對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分析
調研結果顯示,城市居民參與休閑活動的頻率普遍偏低,休閑活動較為單一而且以隨興休閑為主,其中休息放松的頻率較高(均值為3.65),社交和享樂活動的頻率較低(均值分別為2.81、2.80),運動和自我提升活動的頻率更低(均值分別為2.58、2.53)。除月收入以外,其他人口學變量對居民參與休閑活動的頻率都有顯著影響:女性偏好享樂活動,男性偏好社交和運動;未婚者參與享樂活動較多;高學歷者參與自我提升活動較多;離退休人員從事休息放松活動的頻率相對較高。休閑活動和幸福感關系的具體分析如下。
(一)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的相關分析
采用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方法,分析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的相關性。從表2可知,幸福感知度、生活滿意度和正面情緒與各種類型的休閑活動皆顯著正相關;負面情緒僅與“休息放松”顯著負相關。
表2 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的相關關系表

休息放松享樂社交運動自我提升幸福感知度生活滿意度正面情緒負面情緒休息放松1 享樂0.279**1 社交0.165**0.311**1 運動0.155**0.159**0.224**1 自我提升0.072*0.185**0.173**0.303**1 幸福感知度0.195**0.180**0.241**0.184**0.177**1 生活滿意度0.134**0.155**0.201**0.192**0.149**0.627**1 正面情緒0.200**0.196**0.291**0.276**0.230**0.417**0.489**1 負面情緒-0.187**-0.032-0.038-0.0100.059-0.210**-0.179**-0.111**1
注:**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在0.05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進一步的偏相關分析顯示,控制其他變量后,幸福感知度、正面情緒與休閑活動顯著相關。控制其他變量后,生活滿意度與“社交”“運動”顯著相關;控制幸福感知度后,生活滿意度與“休息放松”“享樂”“自我提升”無顯著相關關系。控制其他變量后,負面情緒與“休息放松”顯著相關,但與其他類型休閑活動無顯著相關關系。
(二)休閑活動對幸福感的預測
1.休閑活動對幸福感知度的預測
對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知度關系的預測采用逐步多元回歸分析方法,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知度的模型匯總表

模型RR2調整R2標準估計的誤差更改統計量R2更改F更改df1df2Sig.F更改容差(DW)10.241a0.0580.0570.7260.05858.59119500.00020.288b0.0830.0810.7170.02525.51019490.00030.316c0.1000.0970.7110.01717.93019480.00040.326d0.1070.1030.7080.0077.23519470.0071.850
注:a.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b.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休息放松。c.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休息放松,自我提升。d.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休息放松,自我提升,運動。
由表3可知,DW=1.850∈(1.5,2.5),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知度模型之間不存在自相關現象。最大的條件索引為13.583,小于15,自變量之間沒有共線性問題。休閑活動中,“社交”可以獨立解釋幸福感知度5.7%的變異量(F(1,950)=58.591,p=0.000);“休息放松”可以獨立解釋2.5%的變異量(F(1,949)=25.510,p=0.000);“自我提升”可以獨立解釋1.7%的變異量(F(1,948)=17.930,p=0.000);“運動”可以獨立解釋0.7%的變異量(F(1,947)=7.235,p=0.007)。模型4共有4個獨立變量,調整后總計可以解釋幸福感知度10.3%的變異量。經過模型的系數分析及其標準化,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知度的回歸模型為:Y(幸福感知度)=0.179X1(社交)+0.143X2(休息放松)+0.109X3(自我提升)+0.089X4(運動)。
2.休閑活動對生活滿意度的預測
對休閑活動與生活滿意度關系的預測采用逐步多元回歸分析方法,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休閑活動與生活滿意度的模型匯總表

模型RR2調整R2標準估計的誤差更改統計量R2更改F更改df1df2Sig.F更改容差(DW)10.201a0.0400.0390.816470.04040.08219500.00020.251b0.0630.0610.807190.02322.97019490.00030.265c0.0700.0670.804540.0077.27519480.00740.276d0.0760.0720.802440.0065.97219470.0151.727
注:a.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b.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運動。c.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運動,休息放松。d.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運動,休息放松,自我提升。
由表4可知,DW=1.727∈(1.5,2.5),休閑活動與生活滿意度模型之間不存在自相關現象。最大的條件索引為13.583,小于15,自變量之間沒有共線性問題。休閑活動中,“社交”可以獨立解釋生活滿意度3.9%的變異量(F(1,950)=40.082,p=0.000);“運動”可以獨立解釋2.3%的變異量(F(1,949)=22.970,p=0.000);“休息放松”可以獨立解釋0.7%的變異量(F(1,948)=7.275,p=0.007);“自我提升”可以獨立解釋0.6%的變異量(F(1,947)=5.972,p=0.015)。模型4共有4個獨立變量,調整后總計可以解釋生活滿意度7.2%的變異量。經過模型的系數分析及其標準化,休閑活動與生活滿意度的回歸模型為:Y(生活滿意度)=0.146X1(社交)+0.121X2(運動)+0.085X3(休息放松)+0.081X4(自我提升)。
3.休閑活動對正面情緒的預測
對休閑活動與正面情緒關系的預測采用逐步多元回歸分析方法,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休閑活動與正面情緒的模型匯總表

模型RR2調整R2標準估計的誤差更改統計量R2更改F更改df1df2Sig.F更改容差(DW)10.291a0.0850.0840.615010.08587.70119500.00020.362b0.1310.1290.599440.04750.98519490.00030.384c0.1480.1450.594030.01718.38019480.00040.404d0.1640.1600.588780.01617.97719470.0001.904
注:a.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b.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運動。c.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運動,休息放松。d. 預測變量:(常量),社交,運動,休息放松,自我提升。
由表5可知,DW=1.904∈(1.5,2.5),休閑活動與正面情緒模型之間不存在自相關現象。最大的條件索引為13.583,小于15,自變量之間沒有共線性問題。休閑活動中,“社交”可以獨立解釋正面情緒8.4%的變異量(F(1,950)=87.701,p=0.000);“運動”可以獨立解釋4.7%的變異量(F(1,949)=50.985,p=0.000);“休息放松”可以獨立解釋1.7%的變異量(F(1,948)=18.380,p=0.000);“自我提升”可以獨立解釋1.6%的變異量(F(1,947)=17.977,p=0.000)。模型4共有4個獨立變量,調整后總計可以解釋正面情緒16.0%的變異量。經過模型的系數分析及其標準化,休閑活動與正面情緒的回歸模型為:Y(正面情緒)=0.209X1(社交)+0.168X2(運動)+0.130X3(休息放松)+0.133X4(自我提升)。
4.休閑活動對負面情緒的預測
對休閑活動與負面情緒關系的預測采用逐步多元回歸分析方法,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休閑活動與負面情緒的模型匯總表
注:a.預測變量:(常量),休息放松。b.預測變量:(常量),休息放松,自我提升。
由表6可知,DW=1.864∈(1.5,2.5),休閑活動與負面情緒模型之間不存在自相關現象。最大的條件索引為9.952,小于15,自變量之間沒有共線性問題。休閑活動中,調整后“休息放松”可以獨立解釋負面情緒3.4%的變異量(F(1,950)=34.268,p=0.000);“自我提升”可以獨立解釋0.5%的變異量(F(1,949)=5.201,p=0.023)。模型2共有2個獨立變量,調整后總計可以解釋負面情緒3.8%的變異量。經過模型的系數分析及其標準化,休閑活動與負面情緒的回歸模型為:Y(負面情緒)=-0.192X1(休息放松)+0.073X2(自我提升)。
(三)休閑活動與幸福感關系的具體分析

圖1 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知度的關系圖
在逐步多元回歸分析基礎上,對休閑活動與幸福感作均值分析。由圖1至圖4可見,總體而言,休閑活動中除了享樂活動與幸福感沒有顯著相關關系之外,其他4項休閑活動與幸福感知度、生活滿意度和正面情緒大致存在正向關系,而與負面情緒的關系相對較弱。具體分析如下:
由圖1可見,總體上,社交和運動的參與頻率與幸福感知度有正向關系。休息放松的參與頻率總體上會影響幸福感知度,但從不參與休息放松活動的人群,其幸福感知度并非最低,甚至會中等略高。
在深度訪談中發現,有部分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空閑時間太少,無暇休閑,但是大量時間投入到事業中,事業帶來的成就感和滿足感也會帶來一定的幸福感知度,這或許可以解釋前述現象。自我提升的參與頻率在一定數值范圍內可以促進幸福感知度的提升,但是經常參與該活動的人并非是幸福感知度最高的人。社交活動的參與頻率對幸福感知度的影響最大。
由圖2可見,社交和運動的參與頻率大致上與生活滿意度呈正比關系,休息放松的參與頻率總體上與生活滿意度正相關。自我提升的參與頻率在一定數值范圍內能促進生活滿意度的提升,然而經常參與該活動的人并非是生活滿意度最高的人,而且自我提升的參與頻率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相對較小,社交活動的參與頻率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最大。

圖2 休閑活動與生活滿意度的關系圖

圖3 休閑活動與正面情緒的關系圖
由圖3可見,社交、運動和自我提升的參與頻率與正面情緒正相關。除部分數值區間,休息放松的參與頻率與正面情緒也是正相關,較少參與休息放松的受訪者的正面情緒明顯高于從不參與休息放松的受訪者。另外,自我提升活動的參與頻率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相對較小,社交活動的參與頻率對正面情緒的影響較大。
根據Pearson積差相關性分析,休閑活動的參與頻率對負面情緒基本上沒有顯著影響。由圖4可見,在一定數值范圍內,休息放松的參與頻率會對負面情緒產生積極影響,即參與休息放松活動越多,負面情緒越少。

圖4 休閑活動與負面情緒的關系圖
(四)休閑活動對幸福感的影響機制
結合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和逐步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得出休閑活動對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如圖5所示。可見,只有享樂活動對幸福感沒有影響,其他類型休閑活動都會對幸福感的一個或多個維度產生顯著影響。對幸福感知度、生活滿意度和正面情緒產生最大顯著影響的因素是社交活動的參與頻率。

圖5 休閑活動對幸福感的主要影響機制圖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綜上可知,不同類型休閑活動的參與頻率對幸福感的影響特征有差異,總體而言,提升休閑活動的參與頻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幸福感知度、生活滿意度和正面情緒,這與很多學者的研究結果比較吻合。享樂活動作為隨興休閑活動,并不能對幸福感產生顯著影響,這從側面驗證了羅伯特·斯特賓斯的深度休閑理論。
(二)政策建議
1.引導休閑活動向更豐富的方向發展
近年來,杭州市政府在增加休閑消費場所方面作出了較多努力。總體上,杭州的休閑消費場所較多,但是休閑種類很少、很集中,基本上都是餐飲,茶和自助餐結合的餐飲是杭州最受歡迎的休閑方式之一,其他休閑種類相對較少。根據研究結果,盡管享樂活動是唯一一項不會促進幸福感提升的休閑活動,但餐飲活動還兼有部分社交內容,尤其是飲茶,多為結伴而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增進幸福感。如何打破杭州市休閑活動較為單一的局面,推出更豐富、公益性更強的休閑活動,這是我們當前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調查中發現,休閑活動中運動和自我提升的參與頻率仍然較低,因此未來可以通過政府引導,以這兩類活動為抓手進一步豐富杭州的城市居民休閑活動,具體措施有:(1)除了鼓勵運動休閑行業的發展之外,通過多種方式鼓勵居民參與運動,為居民運動創造更便利的條件,包括完善健身器材的布局、提供更多的運動公共場所、完善城市步行道等。(2)支持各種公益性的文化活動。目前很多文化活動是通過圖書館來做的,其影響力有限,未來還需要在這方面加大力度,為更多有需要的城市居民提供免費的文化活動機會。(3)鼓勵成立各類休閑愛好的民間組織,對于符合條件的民間組織提供資金等支持,從而實現活動從自發向自覺發展的轉變。目前杭州有很多越劇、舞蹈等愛好者,有些活動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這些活動只要稍加引導,便可發展得更好,比如政府對龍舟競賽活動的支持。
2.有針對性地配套城市居民需要的免費休閑場所和設施
因地制宜擴大城市公共休閑空間、增加休閑場所設施是完善城市休閑體系的硬件工程。近年來,杭城在免費開放各大公園、博物館和紀念館,增辟城市小廣場,提供公共自行車,安裝社區簡易健身設施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部分旅游景點的免費開放在客觀上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更高質量的城市公共休閑空間,然而博物館、紀念館等人文景觀本身并不像自然景觀那樣受歡迎,所以,在未來經營中,需要更多地考慮城市居民的偏好,提供更加豐富的休閑形式,以吸引更多的參觀者。博物館類公共休閑空間可以朝兩個方向發展:一為享樂型,那些文物價值相對較小的博物館可與餐飲業等其他產業合作,根據主題,設計休閑內容,加強參觀者的體驗深度。杭幫菜博物館的做法值得借鑒,即展示杭幫仿真特色菜品的同時,配套餐飲服務,使參觀者可以獲得杭州餐飲文化的雙重體驗。二為提升型,對于浙江省博物館等有較大影響力的博物館,需要增加展示方式,實現靜態和動態結合、平面和立體結合、無聲和有聲結合等。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參觀者對博物館文物的理解。政府部門需要為公共免費休閑場所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
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城市地塊尤其是市中心的地塊大多寸土寸金,但是仍然需要留出一部分空間作為居民的休閑廣場,這也可以鼓勵居民更多地參與休閑活動。比如,馬塍路和文三路的交叉口、華星路和學院路的交叉口,近年來都開辟了城市小廣場,它們既成為了城市居民的公共休閑空間,又成為了形象展示該區域文化內涵的文化地標,一舉兩得。每到傍晚,這些公共休閑區域都聚集了很多人。目前,杭州城市區域中仍然有一些類似的具有文化亮點的閑置空間,可以通過一些細化措施進一步提升其利用價值。在這點上,澳門地區的做法值得借鑒。相較而言,澳門半島的土地更為稀缺,但是,其城市空間被利用到極致,任何一塊極小的角落都是一道風景,都能讓人駐足。它們甚至通過增設公共健身器材和開辟大片的涂鴉墻,把即將拆遷的樓房變成了公共休閑空間。此外,杭州應在進一步擴大公共自行車網絡、配套后續服務的過程中,更多地考慮居民的休閑需要,從而為提升城市居民休閑活動的頻率和質量打下堅實基礎。
注釋:
①參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年)的通知》. http://www. gov. cn/zwgk/2013-02/18/content_2333544.htm。
②參見陳勁松,彭遠文,豐鴻平,等:《央視也搞“無厘頭”〈新聞聯播〉找幸福》. http://news. qq. com/a/20121019/001101.htm。
③參見《2007—2011年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國城市發展網綜合整理,2012年11月1日. http://www. chinacity. org. cn/csph/csph/48252.html。
④參見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苗力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3頁。
[1]許義雄. 休閑的意義、內容及其方法[J]. 體育學報,1980(2):27-40.
[2]呂建政. 休閑教育的發展[J]. 臺灣教育,1994(523):18-20.
[3]劉泳倫. 基層消防人員休閑參與、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D]. 云林:“國立云林科技大學”,2003.
[4]陳祥慈. 老年人參與休閑活動對休閑活動參與效益、生活品質與幸福感之影響探討——以臺中縣長青學苑為例[D]. 臺中:朝陽科技大學,2012.
[5]謝秀芳,鄭麗霞. 技職院校學生休閑活動參與狀況之研究[J]. 體育學報,1995(20):123-134.
[6]Kraus R G. Recreation and Leisure in Modern Society[M]. 4th ed.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0.
[7]文崇一. 青年工人的休閑行為及其類型[J].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輯刊,1981(51):1-62.
[8]王煥琛. 休閑教育從理論與實踐之研討[J]. 臺灣教育,1994(235):9-14.
[9]李志恭,李立良.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休閑參與類型與休閑滿意之相關研究[J]. 嘉大體育健康休閑期刊,2011,10(1):35-47.
[10]Stebbins R. Amateurs,Professionals,and Serious Leisure[M]. Montreal,QC and Kingston,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2.
[11]Stebbins R. Casual leisure:A conceptual statement[J]. Leisure Studies,1997,16(1):17-26.
[12]Gilbert D,Abdullah J. Holiday taking and the sense of well-be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4,31(1):103-121.
[13]Graham C.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An Economy of Well-being[M]. Washington D. 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1.
[14]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95(3):542-575.
[15]Diener E,Suh E M,Lucas R E,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9,125(2):276-302.
[16]Diener E,Oishi S,Lucas R E. Personality,culture,and subjective well-being: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3,54(5):403-425.
[17]Veenhoven R. Happy life-expectancy: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 in nation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6,39(1):1-58.
[18]Panaccio A,Vandenberghe C.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A longitudinal study[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9,75(2):224-236.
[19]伊恩·K. 史密斯. 幸福感——簡單幾步讓你收獲內心真正所需[M]. 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11.
[20]Tinsley H E A,Tinsley D J. A theory of the attributes,benefits,and causes of leisure experience[J]. Leisure Science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1986,8(1):1-45.
[21]Kelly J R,Ross J E. Later-life leisure:Beginning a new agenda[J]. Leisure Science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1989,11(1):47-59.
[22]Balatsky G,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ssian student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3,28(3):225-243.
[23]陸洛. 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J]. “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匯刊:人文及社會科學,1998,8(1):115-137.
[24]Currie J. Motherhood,stress and the exercise experience:Freedom or constraint?[J]. Leisure Studies,2004,23(3):225-242.
[25]李維靈,施建彬,邱翔蘭. 退休老人休閑活動參與及其幸福感之相關研究[J]. 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2007,3(2):27-35.
[26]陳欣宏,李志恭. 臺南縣市松年大學學員休閑參與、休閑滿意及幸福感之研究[J]. 屏東教大運動科學學刊,2011(7):173-186.
[27]蔣獎,秦明,克燕南,等. 休閑活動與主觀幸福感[J]. 旅游學刊,2011,26(9):74-78.
[28]譚家倫,趙小芳,宋金平. 兩岸高學歷單身女性健康生活型態、休閑參與、休閑滿意度與幸福感關系之比較研究——以北京市與臺北市為例[C]//2011《旅游學刊》中國旅游研究年會會議論文集,2011:117-132.
[29]Haworth J T. Meaningful a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models of non-employment[J]. Leisure Studies,1986,5(3):281-297.
[30]Lu L,Argyle M.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as a function of leisure activity[J].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1994,10(2):89-96.
[31]羅伯特·斯特賓斯. 休閑與幸福:錯綜復雜的關系[J]. 劉慧梅,譯.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42(1):31-43.
[32]Ruuskanen J M,Ruoppila I. Physical a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people aged 65 to 84 years[J]. Age and Ageing,1995,24(4):292-296.
[33]Zimmer Z,Brayley R E,Searle M S. Whether to go and where to go:Identification of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seniors’ decisions to travel[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5,33(3):3-10.
[34]Bath P A,Morgan K. Customary physical activity and physical health outcomes in later life[J]. Age and Ageing,1998,27(s3):29-34.
[35]Hills P,Argyle M. Musical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happines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1998,25(1):91-102.
[36]Fox K R. Self-esteem,self-perceptions and exerci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2000,31(2):228-240.
[37]Brown W J,Mishra G,Lee C,et al. 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in Australian women:Relationship with well being and symptoms[J]. Research Quar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2000,71(3):206-216.
[38]蔡碧女. 老人休閑教育之研究——以元極舞為例[D]. 臺中:臺灣體育學院,2001.
[39]Lee C,Russell A. Effects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emotional well-being among older Australian women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nalyses[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2003,54(2):155-160.
[40]林宜蔓. 游泳者持續參與在休閑效益與幸福感之研究[D]. 云林:“國立云林科技大學”,2004.
[41]Scanlon-Mogel J,Roberto K. Older adults’ beliefs about physical activity and exercise:Life course influences and transitions[J]. Quality in Ageing,2004,5(3):33-44.
[42]Th?gersen-Ntoumani C,Fox K R,Ntoumanis N. Relationships between exercise and three components of mental well-being in corporate employees[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2005,6(6):609-627.
[43]Netz Y,Wu M J,Becker B J,et 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advanced age:A meta-analysis of intervention studies[J]. Psychology and Ageing,2005,20(2):272-284.
[44]Sayyadi A R,Nazer M,Ansary A,et al. The effect of the exercise training on depression in elderly women[J]. Annals of General Psychiatry,2006,5(s1):s199.
[45]曾芊,曾芃. 論休閑體育活動對幸福感知度的影響[J]. 軍事體育進修學院學報,2008,27(3):8-10.
[46]吳龍山,黃仲凌. 臺灣地區民眾運動休閑參與涉入程度、休閑滿意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J]. 嶺東體育暨休閑學刊,2009(7):141-155.
[47]林坤和,李建霖,黃淑玲. 南區大專校院運動代表隊學生在休閑參與、休閑阻礙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J]. 人文與社會,2009,2(4):195-218.
[48]Becchetti L,Ricca E G,Pelloni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leisure and life satisfaction:Causalit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2,108(3):453-490.
[49]Hills P,Argyle M. Positive moods derived from leisur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happiness and personality[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1998,25(3):523-535.
[50]Berger B G,Owen D R. Stress reduction and mood enhancement in four exercise modes:Swimming,body conditioning,hatha yoga,and fencing[J].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1988,59(2):148-159.
[51]Berger B G,Motl R W. Exercise and mood:A selective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employing the profile of mood states[J].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2000,12(1):69-92.
[52]婁伶俐. 主觀幸福感的經濟學理論與實證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3]Diener E,Emmons R A,Larsen R J,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49(1):71-75.
[54]Oishi S,Diener E,Suh E,et al. Value as a moderator in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1999,67(1):157-184.
AStudyofInfluencesofUrbanResidents’LeisureActivitiesonSubjectiveWell-being:TakeHangzhouasanExample
JIANGYan
(SchoolofInternationalBusiness,Zhejiang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Hangzhou310012,Chin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urban residents’ leisure activiti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leisure activities were divided into activities of relaxation,enjoyment,social contacts,sports and self-improvemen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leisure motiv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SPSS software analysis,the study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frequency of four leisure activities,except the activity of enjoyment ha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urban residents’ leisure activities,more leisure activities should be created,and more public leisure places and facilities should be provided.
urban residents;leisure activities;subjective well-being (SWB);influencing mechanism
F590
A
2095-2074(2015)06-0098-12
2015-08-2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2CSH057)
蔣艷(1978-),女,浙江奉化人,浙江外國語學院國際商學院旅游系副教授,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