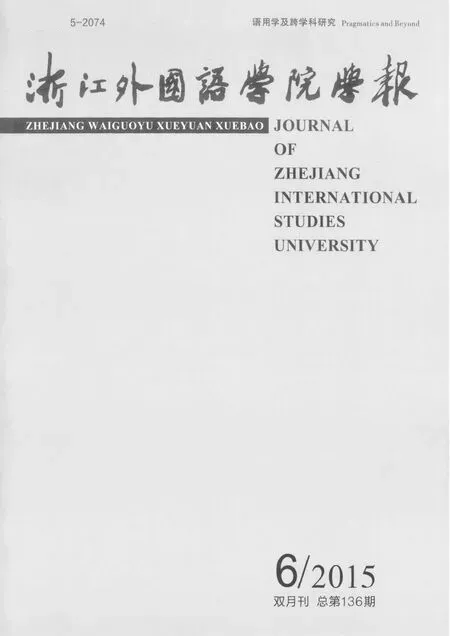論旅游文本翻譯中的語用充實
劉朝陽,莫愛屏
(1.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外語系,廣東 廣州 510620;2.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翻譯學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420)
論旅游文本翻譯中的語用充實
劉朝陽1,莫愛屏2
(1.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外語系,廣東 廣州 510620;2.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翻譯學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420)
基于言語交際中語用充實理論,對旅游文本中概念類、含義類、主題類、指示語類和語篇銜接類五種語類翻譯策略的探討發現:漢英兩種語言文化差異引起相關信息不對稱;旅游文本的翻譯過程比單語的理解和產出更為復雜。在充分掌握語言知識、邏輯知識、旅游文化知識及其他相關知識的前提下,譯者須力求將源語所表達的意義明晰化,找到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之間的最佳關聯,以獲取源語語言信息傳遞的最佳效果、保證譯語讀者接收信息的準確性。
語用充實;旅游文本英譯;關聯理論
一、引言
言語交際過程中,話語理解等信息處理不是簡單的信息編碼與解碼,而是言語交際者根據語境條件對目標話語進行相應的語用加工處理,這一過程就是“語用充實”的過程[1]345,也即言語交際者充分利用語境將語言使用中各種模糊、不確定的詞義加以確定的語用認知過程[2]158[3-4]。關于語用充實的研究,冉永平在《翻譯中的信息空缺、語境補缺及語用充實》[5]一文中詳細解讀了譯者如何對源語進行以語境為參照的信息補缺,以求最大程度地實現語際語用等效。陳吉榮[6]認為翻譯中的語用充實具有語言學范疇的五個特點(代償性、認知性、關聯性、動態性和推理性),并指出其具有明顯的語用擴大和語用強調的特點,突出反映了語境加工的動態特質。徐天樂[7]、張艷萍[8]等分別從詞匯、英語定語形容詞等方面探討了翻譯中的語用充實。也有學者從不同的文體范疇來研究翻譯中的語用充實:張新紅[9]、張法連和張魯平[10]、郭淑婉[11]等探討了法律翻譯中的語用充實;李成團[12]、王慧敏[13]探討了文學翻譯中的語用充實;張瓊[14]等則探討了典籍翻譯中的語用充實。綜上可知,盡管目前學界已有不少學者對翻譯中的語用充實進行了研究,但針對旅游文本翻譯的成果仍不多見。
旅游文本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跨語言的交際活動,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類似的語用充實現象。由于文化的差異,兩種語言文本相互轉換的過程中常出現信息缺失和/或信息不對稱等問題,譯者須在眾多語境假設中選取最可能的那一種對源語進行信息補缺,然后從譯語讀者的角度,對譯語進行語用充實與順應,即選擇最恰當的譯語形式來實現源語和譯語之間的最佳關聯。
本文基于相關的語際語用充實研究成果,擬從詞匯和篇章兩個層面,探討旅游文本翻譯中五種語類(概念類、含義類、主題類、指示語類和語篇銜接類)如何運用語用充實策略來實現最佳譯文效果,以期為旅游文本翻譯提供借鑒。
二、語用充實與旅游文本翻譯
相關研究對語用充實有多種探索維度,根據Carston[15]294[16]、Sequeiros[3]、Wilson[4]、冉永平[1]等的研究,語用充實主要包括兩個方面:語用收縮和語用擴充。語用收縮是指交際過程中某一詞語所編碼的意義在特定語境中的所指范圍或含義有所縮小。我們可能會發現某些詞語在詞典中所表達的意義是多義項的,而某些詞語所包含的信息有很強的概括性或含糊性。這就要求聽話人須依據語境來理解這些詞語的準確意義。語用擴充則是指原型意義或常規意義的語用弱化、延伸。交際中有些詞語所傳達的信息可能不是其詞典意義,而是其在特定語境中與其他詞語的搭配或組合意義。換言之,聽話人會在特定的語境條件下選擇對方話語所傳遞的意義,而這個意義有可能是對話語原義進行了延伸與擴展的結果。Sequeiros[3]特別對翻譯中的語用充實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稱其為語際語用充實,還將其分為五類:指示類、概念類、主題類、語篇銜接類和含義類。本文依據Sequeiros[3]關于翻譯中的語用充實的分類,來對旅游文本翻譯作一些探討。
旅游文本翻譯中,為準確傳遞相關的旅游文化信息,譯者往往需要參照語境,對源語進行語用充實與順應,選擇得體的譯語形式以實現源語和譯語之間的最佳關聯(見圖1)。這是一個譯者試圖實現語用等效的過程。

圖1 旅游翻譯中的語用充實
旅游文本翻譯作為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涉及語言─語境─交際者之間的互動[17]。圖1中各成分之間的關系表明,為了尋找源語和譯語之間的最佳關聯,最大限度地實現語用等效,譯者一方面須實施補足旅游源語文本信息的語用充實與順應行為,以獲取交際所需的信息;另一方面須充分考慮譯語讀者,適時地對特定詞匯的意義進行語義收縮或擴充以選擇得體的譯語形式。這個過程既是源語作者(交際者1)與譯者(接受者1)之間的交流,也是譯者(交際者2)與譯語讀者(接受者2)之間的交流。譯者借助雙重交際者的身份,實現了源語作者與譯語讀者之間的交流。
旅游文本的翻譯受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制約。翻譯過程中,譯者須通過語境尋找關聯信息,來實現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之間的語用等效;然后,再依據話語與語境之間的關聯進行推理,以求得最佳語境效果[18]115。一般來說,譯者會選擇可及性程度較高的語境假設來對客觀信息的傳達與輸入進行語用充實。根據源語語境準確把握源語作者的意圖是譯者實現成功翻譯的基礎。由于漢英文本之間的差異,譯者不僅要保留源語文本信息,還須選擇符合譯語讀者認知語境和語用習慣的譯語形式。這時,譯者就須對譯語讀者的語境作出假設,通過語用充實,以實現最佳關聯。如果譯者能對話語和語境進行有效推理,譯語文本所含信息足夠豐富,譯文讀者就可以付出較小的努力來理解源語文本。
下文將從詞匯和篇章兩個層面來探討旅游文本翻譯中的語用充實,所舉語料主要取自全國各大景點的漢英對照文本資料。
三、詞匯層面的語用充實
旅游文本翻譯中,概念類、含義類和主題類語用充實主要源于漢英兩種語言在詞匯方面的差異。在實施上述三種語用充實時,譯者首先要分析源語文本中存在的詞匯含義的信息缺失或不對稱現象;然后,根據譯語語境對其進行語用充實和順應,從而在準確傳達源語文本信息的前提下,確保譯語文本的可讀性。
(一)概念類語用充實
概念的理解離不開具體的語境。大多數情況下,如果脫離語境單從表面來判斷,概念的意義是含混和模糊的。言語交際活動往往發生在相對確定的語境之中,包含時空、社會和心理等多方面信息。正如陳新仁所說,只有在交際雙方共享各種語境信息,或者以特定場合下的交際意圖為前提,他們才能從不完整、不明晰、不確定的概念表述中得出完整、清晰的意義,而最終達到交際的目的[19]338。
社會、歷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差異會導致概念的不對等、空缺等問題。因此,在進行旅游文本翻譯時,譯者須分析漢英兩種語言在旅游專業概念表述方面的差異,對譯語讀者的認知語境加以評估,通過對不對等、空缺信息的補充,來幫助譯語讀者準確地理解源語文本。例如:
(1)峨眉山→Mount Emei 武當山→Wudang Mountain 象鼻山→the Elephant Hill
念青唐古拉山→the Nyainqentanglha Range 青山(香港)→Castle Peak
獅子山(香港)→Lion Rock 大嶼山(香港)→Lantau Island[20]211
在諸多的旅游文本翻譯中,都會涉及山名的翻譯。中國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具有概括性、模糊性和包容性,一個字往往可以包含多種義項,如“山”可以概指各種類型的山。因此,通名都是“山”的漢字,根據其不同的內在含義會有多種英譯表達,且不能互相替換。文化交流是旅游文本翻譯的一個重要任務。我們不僅僅要讓外國游客了解中國文化,還要讓他們理解、認可和接受中國文化。對于“山”字的翻譯,譯者須根據具體情況譯出其準確的含義[20]。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對“山”的定義和翻譯標準有著明確的規定:“海拔高度500米以上,相對起伏大于200米,坡度又較陡的高地”①。因此,海拔高度500米以上的高地才可以稱之為大山或者山岳,翻譯為mountain或mount。如有著較為濃厚文化色彩的佛教圣地——峨眉山,譯為Mount Emei;再如武當山,可根據“山”的基本義將其譯為Wudang Mountain[21]83-84。海拔高度500米以下的山地則為小山,也稱丘陵,與英語中的hill相對應。又如,可將桂林景區的象鼻山譯為the Elephant Hill。而念青唐古拉山實際上是山脈,有別于“山”的概念意義,因而將其譯為the Nyainqentanglha Range。同理,香港的青山之所以被翻譯為Castle Peak,是因為英國人覺得其形狀像一座歐洲城堡;獅子山其實是一塊很大的巖石,所以將其譯為Lion Rock;大嶼山是一座島嶼,故將其譯為Lantau Island。正如“山”的翻譯一樣,漢語中的“海”同樣也因其具體所指不同而選擇不同的翻譯。例如:
(2)東海→the East China Sea 大灘海→Long Harbor(香港) 邛海→Qionghai Lake
蜀南竹海→the Bamboo Forest in Southern Sichuan 牛尾海→Port Shelter(香港)[20]212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根據通名意義,不同的漢字也可英譯為同一個英語單詞。因此,江、河、川、溪、水都可英譯為river,例如:
(3)嘉陵江→Jialing River 螳螂川→Tanglang River(云南) 永定河→Yongding River
古田溪→Gutian River(福建) 漢水→Hanshui River
在旅游出行的諸多方面,漢英兩種語言在概念、習慣等表達上有較大差異,譯者只有適時運用語用充實策略,才不至于造成誤解。例如:
(4)源語文本:這個是有一張雙人床的房間,裝修雅致,溫馨舒適。(廣州某酒店)
譯語文本1:This is a twin room which is cozy, comfortable and tastefully decorated.
譯語文本2:This is a double room which is cozy, comfortable and tastefully decorated.
例(4)是關于“兩張單人床客房(漢語常指的標準雙人間)”概念的翻譯。譯語文本1粗看似乎沒什么問題,語句通順,語法也符合規范。然而,譯者忽略了一個事實:按照國際上的通用說法,twin room或twin-bedded room是兩張單人床客房;而double room是指只有一張雙人床的客房。如果將twin room和double room混為一談,肯定會給游客帶來極大的不便。
(二)含義類語用充實
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減少讀者的認知努力,使其更好地理解原文,充分獲取相應的旅游文化信息,譯者也可對某些詞匯作含義類的語用充實。當然,這種充實也是基于對源語文本意義的正確理解。例如:
(5)源語文本:濟公劫富濟貧,深受窮苦人民愛戴。(浙江蘭溪濟公紀念館)
譯語文本:Jigong,Robin Hood in China, who robbed the rich and helped the poor, was loved by the poor people.
源語文本中的“濟公”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對漢語讀者來說,沒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難。可對外國游客來說卻是陌生的,光靠字面譯解未必能讓游客理解和記住。從譯語文化中找到類似的人物形象(英國民間傳說中的俠盜羅賓漢)進行類比,可拉近讀者與漢語文化的距離,“濟公”這一形象也就能被準確解讀了。許多的風景名勝都與歷史典故、英雄人物有關,這就要求譯者掌握一定的譯語文化的背景知識,選用譯語中類似的歷史事件或人物形象進行有效的語用充實。例如:
(6)源語文本:大觀園是根據《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筆意,運用中國傳統園林藝術手法建成的。(上海大觀園)
譯語文本:The Garden was built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ing techniques conceived in line with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s in Tsao Hsueh-chin’s well-known novelADreamofRedMansions.
如果照字面意思翻譯,例(6)源語文本中的“筆意”只能翻譯為calligraphic style、 charm of stroke、meaning of a passage等,不能表達其固有含義。然而,此處的“筆意”指的是:大觀園是根據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描寫的建筑設計和風格來建造的。翻譯時,譯者須表達出這層意思,才能讓譯語讀者真正理解源語文本。
(三)主題類語用充實
主題表達了實體與整個事件的一種語義聯系,可為事件的描述提供信息[22]。言語交際中,交際雙方因為某些共識,可以省略包括主題信息在內的部分信息。翻譯過程中,緣于源語讀者與譯語讀者在認知環境方面的差異,無法共享隱含的主題信息,因而譯者就需要在譯語文本中運用適當的語用充實策略。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根據不同視角調節自己的思維方向,轉換分析角度,才能最終實現源語作者意圖與作品意圖的轉換[23]104。當涉及中國獨有的社會、歷史和文化信息時,譯者須作一些必要的主題補充,才能使譯語讀者真正了解中國文化。例如:
(7)源語文本:在遠古時代,秦淮河即為揚子江一支流。新石器時代,沿河兩岸便人煙稠密,孕育了南京古老文化,有“南京的母親河”之稱。入城后的內秦淮河東西水關之間的河段,素有“十里秦淮”“六朝金粉”之譽。
譯語文本:As a tributary of Yangtze River, Qinhuai River has a long history. As early as in the Neolithic Age, it nurtured the early settlers along its banks and was known as the mother river of Nanjing. Now, the river, especially the part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ter fords that run within the city limits,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culture and economy in Nanjing, bearing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osperity along the 10-li Qinhuai Riv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glories of the ancient capital of six dynasties”.[24]204-205
例(7)中,“十里秦淮”“六朝金粉”對于源語讀者來說,理解起來較為容易:秦淮河畔在歷史上曾經繁華一時,南京城曾是中國六個朝代的都城。然而對于譯語讀者而言,譯者如果僅采用直譯,將很難準確把握其中的含義。因此,譯者必須在譯語文本中以明示的手段把譯語讀者難以理解的隱含意義補充出來,如“the prosperity along the 10-li Qinhuai River”“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glories of the ancient capital of six dynasties”。
在旅游文本翻譯中,譯者經常會碰到一些有中國特色的口號、獎項名稱、標語之類的翻譯。這些漢語的口號、標語非常精練,多以短語形式出現,其含義卻很豐富。如果沒有一定的漢語基礎和文化背景,外國游客是很難理解這些口號和標語的,因此,譯者必須在譯語文本中作一些適當的調整。例如:
(8)源語文本:肇慶具有“三城五優”的顯著特點,成為中外朋友投資置業的理想寶地。
譯語文本:With a reputation of being a famous city, Zhaoqing has become an ideal and promising land for investors, domestic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25]26
(9)源語文本:國家旅游局已經連續6年推出大型系列主題旅游活動:92中國友好觀光年、93中國山水風光游、94中國文物古跡游、95中國民族風情游、96中國度假休閑游、97中國旅游年。
譯語文本:For six years running, the State Tourism Bureau has promoted large-scale serial thematic tourist activities. These were the Friendship Tourist Year in 1992, China’s Landscape of Tourism in 1993, Tourism Featuring China’s Historic Sites and Relics in 1994, Tourism Featuring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in 1995, Tourism Featuring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1996 and the 1997 Tourist Year of China.
四、篇章層面的語用充實
旅游文本翻譯中指示類和語篇銜接類的語用充實,源于漢英兩種語言在篇章結構、謀篇布局方面的差異,主要指句子內部的銜接或句子間的銜接。英語是一種形合的語言,常采用適當的連接性詞語使句中各成分之間或句子之間連貫起來;漢語作為一種意合的語言,其語句成分之間的銜接多依靠語義的連貫。因此,譯者在將漢語旅游文本轉換成英語時,須結合漢語文本的結構及英語表達的需要,適當添加相應的銜接手段,以實現最佳關聯。
(一)指示類語用充實
指示語對話語的理解有指向性功能。交際者根據語境準確理解指示語所表達的指示信息,是翻譯這類話語的關鍵。按其特點和范圍,指示語可分為五類:人稱指示語、時間指示語、地點指示語、話語指示語和社會指示語[26]76。在翻譯過程中,對指示語的處理并不是簡單地翻譯出其在源語文本中的所指,而是要將源語作者所處的語境與譯語讀者所處的語境相匹配。在遵循譯語表達習慣的前提下,譯者可從譯語讀者的角度來表達源語文本中的指示語[12]95。
文本對時空的處理會受到自身語言文化習慣的制約,因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作相應的轉換。在相關景點信息的漢語介紹文本中,常會出現“我國”“本國”“其”等指示語。例如:
(10)源語文本:我國政府將旅游業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加以考慮,這為游客的大幅度增長創造了機會。
譯語文本:By placing tourism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opened the opportunity for substantial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visitors.
人稱指示語是言語行為的參與者用來傳達話語信息的指代稱呼。“第一/第二/第三人稱”稱呼語及其賓格和屬格是語用學中典型的指示語。由于漢英兩種語言在思維方式和思維角度方面的不同,即便是指示同一事物,兩種語言的表達方式也各有不同。因此,譯者須作語言形式上的轉換,以使譯語文本中的人稱指示語能準確地表達源語的含義。如例(10),譯語文本將源語文本中的“我國”轉換為第三人稱“the Chinese government”。又如:
(11)源語文本:古往今來,這名山勝水吸引了多少尋幽探勝的騷人墨客!
譯語文本:No one can say for sure how many men of letters in history have been to this beautiful place to enjoy the charming scenery and the seclusion it offers.
漢語是典型的分析語言(analytic language),其動詞沒有時態標志,常常通過表示時間的詞或短語來表示時態,如“了”“過”等詞可用來表示過去時,“將”“會”等詞表示將來時。對于這些語法上的差異,我們只有遵照各自語言的表達習慣,補足相應的信息來達到交際的目的。例(11)中的譯語文本用現在完成時來表述源語文本中“古往今來”的含義,例(12)也使用了同樣的方法。
(12)源語文本:古往今來,愛的浪漫被視為霓虹,美得難以言狀。
譯語文本:Romance has seemed as inexplicable as the beauty of a rainbow.
(二)語篇銜接
不同語言在言語的連貫性或上下文銜接的規則上有較大差異。漢語語句之間大多沒有明顯的銜接詞,其邏輯關系隱藏于句子的意義之中,需由讀者或聽眾在接收信息時自動補足關聯詞。而英語語句之間的邏輯關系卻需用明顯的銜接詞來展現。因此,為使英語讀者能夠清晰地理解漢語文本中所隱藏的邏輯關聯,譯者就必須在漢譯英過程中添加銜接詞或利用其他銜接方式來明示語句之間的關系。
由于受傳統文化和習慣的影響,中國旅游景點的簡介中使用了大量的形容詞,尤其是四字短語。這種方式對于中國游客,頗具感染力,有一定的烘托作用,然而對于外國游客,則常會帶來理解上的困擾。在此類文本的漢譯英過程中,譯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判斷對漢語文本中的信息進行取舍或增減,并按照英語行文表達的邏輯結構進行信息重組,使之適合英語讀者的需求。例如:
(13)源語文本:這里三千座奇峰拔地而起,形態各異,有的似玉柱神鞭,立地頂天;有的像銅墻鐵壁,巍然屹立;有的如晃板壘卵,搖搖欲墜;有的若盆景古董,玲瓏剔透。(《武陵源風景》畫冊)
譯語文本1:3,000 crags rise in various shapes. They are like whips or pillars propping up the sky; or huge walls, solid and sound; or immense eggs piled on an unsteady boarder; or miniature rocky or curios.
譯語文本2:3,000 crags rise in various shapes:pillars, columns, walls, shaky eggs stacks and potted landscapes.
例(13)中,源語文本大量使用了四字詞語,且使用了并行對偶結構,在文字的描述上,將客觀景物和主觀情感融為一體,寄情托物,依形寫神。這正是漢語旅游文體寫作中常用的手法,其意圖是通過這種行文方式給游客創造一種意境上的美感,激起其游覽興趣。然而,西方人的思維偏重理性、突出個性。在這種思維影響下,英語旅游文本強調寫實,行文邏輯嚴謹,在表達上更強調直觀通俗,以客觀的具象來傳達事物之美,重視語言的實用性和信息的準確性。譯語文本1的作者忽略了上述差異,生硬地照搬源語文本的結構,逐字譯出,結果造成譯文言辭啰唆,言之無物,譯語讀者越看越迷糊。而譯語文本2的作者擺脫了源語文本形式結構的束縛,對其進行了必要的語用收縮,化虛為實,只將原文中的具體物象譯出,反而有利于譯語讀者的理解。再如:
(14)源語文本:桂林位處亞熱帶地區,冬、夏氣候溫和,加上桂林山川形態奇特,無論晴空萬里,一碧萬頃,或云霧繚繞,若隱若現,或淫雨霏霏,煙雨迷蒙,都展現出與眾不同的美態。(桂林旅游宣傳畫冊)
譯語文本:Situated in the sub-tropics, Guilin is blessed with mild winters and moderate summers. Furthermore, the unusual shape of Guilin’s mountains and rivers gives them a surreal quality and wondrous beauty; different at all times, be it in clear, foggy, rainy or hazy weather.
例(14)中,源語文本在介紹不同天氣條件下的桂林美麗景象時,連用了六個四字詞語的形容詞,期間只用兩個“或”字來銜接,將其分成了三組小句。對此,源語讀者不會有任何理解上的疑惑,因為他們會憑借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百科知識進行邏輯關聯補足,從而理解文本。但將其翻譯成英語時如也照本宣科,則只會使譯文晦澀難懂。因此,譯語文本的作者只是用樸實的語言告知譯語讀者:在不同的天氣條件下,桂林呈現出不同的景象風格,到底有何不同,則有待于譯語讀者自己來發現了。
五、結語
漢英兩種語言文化的差異導致諸多旅游文化信息的不對稱。如果譯者不充分利用自身的語言知識、邏輯知識、旅游文化知識以及其他百科知識,進行必要的語用充實,就無法實現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的最佳關聯。詞匯的選擇與表達、語篇的銜接與連貫是制約漢英兩種語言行文表達的關鍵。因此,譯者唯有充分考慮漢英語境的特點,對概念類、含義類、主題類、指示語類和語篇銜接類等語類采用適當的語用充實策略,才能保證譯語讀者信息接收的準確性。
旅游文本翻譯的效果既取決于對源語文本本身的理解,又受制于社會、文化等諸多主客觀因素。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實施的背景下,準確地傳遞旅游資源信息,讓游客真實地感受中國文化的燦爛,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當前,從語用學角度來探討旅游文本的翻譯方法、翻譯策略和翻譯原則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亟待學界的重視和關注。
本研究得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天津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文學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廣東省教育廳省級重大項目(人文社科類)“嶺南文化精品外譯的語用策略研究”(粵教科函(2015)3號)的資助,在此一并致謝!
注釋:
①轉引自連真然:《中國各種山名翻譯背后的學問》,發表于《上海翻譯》2014年第1期,第83頁。
[1]冉永平. 詞匯語用學及語用充實[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5):343-400.
[2]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86.
[3]Sequeiros R. Interlingual pragmatic enrichment in transl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2002 (34):1069-1089.
[4]Wilson D. Relevance, word meaning and communication: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lexical pragmatics[J].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2004, 103(1):1-13.
[5]冉永平. 翻譯中的信息空缺、語境補缺及語用充實[J]. 外國語, 2006 (6):58-65.
[6]陳吉榮. 論翻譯中的語用充實[J]. 外語研究, 2015 (4):77-81.
[7]徐天樂. 詞匯語用充實的順應性研究[J]. 牡丹江大學學報, 2011(6):53-55.
[8]張艷萍. 英語定語形容詞的語用充實及翻譯[J]. 長江大學學報, 2012 (3):79-81.
[9]張新紅. 論法律翻譯中的語用充實[J]. 外語研究, 2008 (1):22-29.
[10]張法連,張魯平. 談語用充實視角下的刑事判決書翻譯[J]. 中國翻譯, 2014 (3):93-97.
[11]郭淑婉. 關聯理論視角下法律翻譯情態意義的語用充實[J]. 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 2015(2):39-42.
[12]李成團. 詩歌翻譯的語用視角、語境補缺與語用充實[J].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 2010(2):77-82.
[13]王慧敏. 文學翻譯中的語用充實——以《臺北人》英譯為例[J]. 發展, 2015(4):88-89.
[14]張瓊. 語用充實視角下《傷寒論》反義同詞現象及翻譯策略論析[J]. 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 2014(12):1704-1707.
[15]Carston R. Thoughts and Utterances: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M]. Oxford:Blackwell,2002.
[16]Carston R. Enrichment and loosening:Complementary processes in deriving the proposition expressed[J]. Linguistische Berichte, 1997 (8):103-127.
[17]莫愛屏. 翻譯研究的語用學路徑[J]. 中國外語, 2011 (3):88-94.
[18]莫愛屏. 語用翻譯與語境關聯[J]. 衡陽師范學院學報, 2002(4):113-117.
[19]陳新仁. 論話語理解中的語義充實[C]// 何自然,冉永平.語用與認知:關聯理論研究.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1:337-347.
[20]李明. 商務英語翻譯(漢譯英)[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1]連真然. 中國各種山名翻譯背后的學問[J]. 上海翻譯, 2014(1):82-86.
[22]Frawley W. Linguistic Semantics[M]. New Jersey:Lawe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2.
[23]莫愛屏. 話語中視角現象的語用翻譯[J]. 外語學刊, 2007 (4):103-107.
[24]呂俊, 侯向群. 英漢翻譯教程[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25]吳偉雄. 淺談漢英翻譯的邏輯思維與表達方法[J]. 中國科技翻譯, 1996 (2):26-27.
[26]崔少芬. 簡析指示語的分類[J]. 語文學刊, 2015(8):74-76.
OnPragmaticEnrichmentinC-ETranslationofTourismTexts
LIUZhaoyang1,MOAiping2
(1.DepartmentofForeignLanguages,GuangdongAIBPolytechnicCollege,Guangzhou510620,China;2.CenterforTranslationStudies,Guangdong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Guangzhou510420,China)
Based on the study of pragmatic enrichment in intern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ourism text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ive categories of interlingual pragmatic enrichment:thematic enrichment, conceptual enrichment, deictic enrichment, implicature enrichment and text cohesion enrichment. Owing to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ourism text translation, which happens in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in intralanguage communication. The translator needs to find out the optimal relevance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to express clearly the meaning of the source text, which is largely constrained by the translator’s diverse knowledge including language, logic, tourism culture and others. Thereafter, the translator can convey exactly to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pragmatic enrichment;tourism text translation;relevance theory
H315.9
A
2095-2074(2015)06-0001-08
2015-11-01
劉朝陽(1978-),男,湖南衡陽人,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外語系講師,文學碩士;莫愛屏(1963-),男,湖南衡陽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主任,高級翻譯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語用學研究:語用與翻譯(主持人:莫愛屏)
譯事三元:語言—語境—交際者,是構成“語用翻譯”的主要內容。語言是表達社會、文化、認知等主客觀因素的載體;交際者(作者/說者、譯者、讀者/聽者)是特定語境下對言語交際中的話語進行加工處理的實施者;語境是人們使用語言進行交際的環境,包括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翻譯作為語言使用的特例,既離不開語言,又離不開語境,更不能沒有交際者。翻譯過程中,譯者充分考慮跨文化的因素對雙語表達中的語用充實(即意義的收窄和放寬)的制約(劉朝陽、莫愛屏),實際上是譯者身份在翻譯過程中的具體體現(申智奇);厘清認知翻譯中語義連貫的語境化制約機制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呂潔),是譯學前沿研究的重要內容。在當前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實施的語境下,提高接受者研究的認識(許勉君、蔣清鳳),并找出文化外譯的有效途徑和策略是豐富和發展語用翻譯的必由之路。語用翻譯及研究涉及言語交際的諸多方面,該領域的成果對翻譯教學與研究是有益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