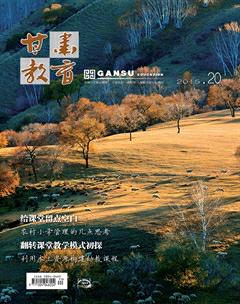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為什么出賣靈魂??
廖德凱
1934年6月30日,一個年輕的建筑師站在一間屋子里,望著一攤在德國大清洗中被槍決的一個熟人的血跡,決定像浮士德那樣,把靈魂賣給一個要做大事的黨派。隨后,他參與了戰爭并擔任了帝國軍需部長,用他的卓越才華和組織天賦(包括使用奴隸),使德國在盟軍的猛烈轟炸下,仍然保持著武器生產的速度與進度,延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時間。
這個年輕人被許多人視為納粹德國希特勒之后的二號人物,他叫阿爾伯特·斯佩爾;其靈魂的買主——“要做大事”的黨派,叫作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它更響亮的名稱是“納粹黨”。
戰后,許多人都在追問:斯佩爾和數百萬年輕人被納粹主義洪流所席卷,他們發自內心地投入到納粹主義的實踐之中,為什么這些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會受到誘惑,出賣自己的靈魂?美國歐柏林大學環境研究和政治學教授奧爾在《大地之心》一書中認為,是德國這個當時教育最發達的歐洲國家,“在最需要公民教育的時候,卻沒有公民教育”。于是,這些年輕人被技術因素迷惑了雙眼,將單純的技術作為自己所執著追求的事業。而這些他們狂熱投入的技術產出,最終給這個世界帶來了難以彌補的傷害。確實,如果沒有正確的“三觀”指導自身的行為,那么,那些有著卓越才能的人的能力越大,給這個社會所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
前文所述的奧爾教授,就致力于構建一個更加理想、更有道德、更有可持續發展影響力的教育體系。他認為,目前地球頻發的環境災難,其根源就在于教育的失敗;他相信,“以熱愛生命為基礎建立的教育,會讓我們的本能和潛能覺醒”。而在目前,這種“本能和潛能”在工業社會的功利心態下,很大程度上處于“休眠和荒廢狀態”。
不過,奧爾教授這種理想顯然不容易得到廣泛支持,特別是在技術席卷全球并改變了人們生存與生活狀態的今天,更多人迷信技術的力量。在我們的印象中,也常常有許多類似這樣的看法:科學是超越國界、思想的“客觀存在”,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而這,也成為“科學原教旨主義”誕生的理論基礎。
但無論是蒸汽機的出現、原子彈的爆炸,還是互聯網的產生和應用,以及附著于這些技術背后的奇思妙想,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從來不是自古就有的“客觀存在”。科學的原理和技術作為“客觀存在”的部分本身沒有思想,只有規律和物質,但是,科學家有思想!
正由于對于科技本身的迷信,以及對“術業有專攻”的極端化理解,使得目前教育在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間人為地設置了障礙。自然科學自不必說,就連經濟學這種社會科學,也過于放大了“客觀經濟規律”,許多經濟學家以“尊重客觀規律”為名,用“世界是這樣的”來對抗和抵制“世界應該是這樣的”。缺少對自然、對社會、對他人的熱愛,以冷冰冰的“規律”看待市場的運行。
“科學原教旨主義”為了“防止被情感淹沒”,提倡科學作為一種工具,可以服務于扭曲、狹隘、冷冰冰、無感情的世界觀,而不能為謙卑、敬畏、神秘、驚嘆等情感所影響。奧爾教授批評這種現象,指出激情、感情與真正的科學之間的關系,“不是對立的,而是錯綜復雜、相互依賴的關系。科學,在最佳狀態下,是由激情和情感推動的”。他得出一個結論:不要把四肢和情感隔離,而要學會協調,并訓練它們以更好地利用。
許多例子已經證明,缺乏責任、迷信技術和數字、沒有底線、沒有對生命的愛的“有能力”的人,會對社會帶來巨大的傷害。每一次災難,特別是人為災難,都會讓我們愛的本能和潛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覺醒,但這一次次用現實災難換來的覺醒,其代價卻是社會所無法承受之重。如果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才,都是缺少悲憫情懷的“技術控”,那么,最終人類的“客觀規律”,恐怕也只有走向毀滅一途。
理想的教育以熱愛生命為基礎,本科教育以通識教育為根本,讓杰出的科技人才首先成為具備愛的責任和能力的人,這大概是解決當前出現的種種問題的根本之道。
(摘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