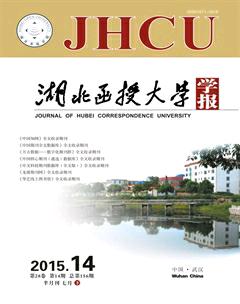韋伯宗教倫理觀的現代性思考
李雪君
[摘要]馬克斯·韋伯,德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被公認為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韋伯曾自稱他的宗教觀點是在馬克思設定的思想框架下進一步延伸和繼承的理論,但筆者認為,這種繼承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否定性的繼承。本文主要對韋伯關于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發展的原因,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對馬克思和韋伯關于資本主義興起的觀點進行比較分析,從而試圖表明兩個偉大的思想理論家的觀點之間的差異,但我們不得否認兩者的思想都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以及對從古至今關于宗教倫理觀點的巨大貢獻。
[關鍵詞]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中圖分類號]B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14-0089-02
一、導論
韋伯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等領域,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是馬克斯·韋伯的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其所提出和研究的論題影響深遠,也是最受爭議的現代社會科學著作之一。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簡稱《新教倫理》)一書中關于宗教倫理的解讀是構成本文分析觀點的前提,但是,基于筆者關于新教倫理中加爾文宗的起源和發展只是略知一二,所以本文主要就韋伯的資本主義興起的觀點進行解讀和對比分析,并試圖對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宗教現象進行理論聯系實際的分析。我們知道,我國的經濟體制是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多種所有制經濟方式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說,我國的市場經濟是與西方的市場經濟具有很大差別的,西方的市場經濟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我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原則和方法論,兩者之間似乎存在一種差異,甚至說是一種對立性。所以,在淺薄的知識背景下,分析這些問題,試圖尋找答案,這是一個非常寬泛和深刻的議題,也是非常有意義和艱難的過程。
二、韋伯宗教理論的現代性思考
(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所要表達的資本主義精神已經很明確。遵從禁欲主義最好的方法就是勞動,在現實生活中上帝為每一個人都安排了天職,人人都該為自己的職業辛勤勞動,把勞動視為生存的目的而不是其他,這就是“天職觀”。就像韋伯在書中所說,“除了粗茶淡飯和冷水浴之外,一劑既可用來抵御性的誘惑,又可用來對抗宗教質疑和道德淪喪的藥方就是:恪盡職守。而最為重要的是,要向上帝命令的那樣,更進一步地把勞動作為人生的目的。”需要強調的是,天職觀念強調的勞動是理性地勞動,包括對資本、生產方式、勞動手段等進行理性的組織安排和規劃,以及進行技術革新和科技進步都是為了能更好的勞動。清教徒的禁欲主義傾向使勞動者拋棄一切享樂主義的想法,信仰宗教的教徒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私利和財富,因為他們潛意識里認為這些都是上帝為他們安排好的,這樣只要是通過努力獲得的財富就都是理所當然的。
(二)宗教倫理與西方資本主義興起
韋伯認為,理性資本主義的產生,一方面源自理性的經濟生活的變遷,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參與經濟生活的主體,即人的行為和精神觀念。在任何一個時期,人都是因受到當時的文化觀念和精神風氣的影響而做出相應的行為,這種文化中既包含某種宗教的影響和牽引,又包括歷史傳統或者某些神秘力量的制約。因此,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很大且至關重要的關系。我們推斷,韋伯的宗教倫理思想是促進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韋伯認為,正是在新教改革的基礎上,新教倫理孕育出了所謂的“禁欲主義的天職觀念”,促使人們的經濟行為完全被理性化,使得各種經濟現象諸如資本積累等的出現和發展。韋伯還試圖解釋了有關西方資本主義產生的獨特性問題,他分別分析了兩種宗教改革,一個是加爾文派從應然的邏輯思想的角度所推行的改革,另一個是路德從實然的經驗角度出發所推行的宗教改革,這兩種改革的本意并不是促成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也不是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們的改革目的是一樣的,即靈魂的救贖,報答上帝的蒙恩和為上帝獲得榮耀。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其兩者的宗教教義產生的一種理性的觀念,致使后者為之受到啟發,成為了興起和發展資本主義精神的精神力量,致使很多經濟行為有了正當性和合理性。這種“偶然”產生的作用,即資本主義興起的獨特性,同時也顯示出與別的民族歷史發展不同的特征。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壯大也證明了這種獨特性。
三、韋伯與馬克思的對比
(一)韋伯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讀完《新教倫理》一書,會讓我們想到一個問題,即我們研究事物發展的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論,而韋伯的理論會立刻讓我們感受到似乎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存在差異,甚至說是理論分歧。因為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觀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切事物發生的決定性因素是現實生活中的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其中的要義是經濟因素是必要因素而不是唯一決定因素,且上層建筑反過來又服務于經濟基礎。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復雜而又多樣化的過程,其中包含了社會意識和上層建筑等對人類的經濟物質生活產生作用的部分。這樣來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與韋伯宗教倫理這種社會意識對人類物質生活的影響的理論其實并不相駁。也就是說,從作為具體研究方法的角度來說,馬克思和韋伯在宗教思想上的對立并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在這個意義上看,馬克思宗教思想和韋伯宗教思想又具有某種一致性和互補性。正如學者描述韋伯的觀點時說,“他在世界宗教系列比較研究這一博大的學術領域所作的長期探索已向人們證實:宗教與文化的關系是現代人文科學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研究課題,而且隨著人文研究的長足進步還將愈加顯要”。
(二)韋伯與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興起的比較
前面已經寫到了關于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韋伯在書中對于這一問題已經為我們說明了一條較為清晰的觀點闡釋。但是,之后韋伯的著作中有這樣一個觀點,即在中國和印度的宗教教義中,那些宗教意識中沒有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也是因此這些國家最終都沒有產生和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韋伯看來,他也承認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并提出宗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作用和影響。他用精神、意識等因素詮釋歷史,把宗教教義對人的影響認為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從精神、意識層面對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中的資本主義諸現象進行解釋,這無疑具有強烈的唯心主義色彩。當然,韋伯在書中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并用一種看似“中立”的立場去回避這一問題,“一般而言,即使是帶著最好的愿望,也不能切實看到宗教思想所具有的文化意義及其對于民族特征形成的重要性。但是,以對文化和歷史所作的片面的唯靈論因果解釋來替代同樣片面的唯物論解釋,當然也不是我的宗旨。”這樣看來,韋伯自身似乎也沒有明確地認定是新教倫理先存在并決定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觀點,而到底是先出現了新教倫理還是先出現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問題,韋伯明顯沒有作出很正面的回答。而馬克思早已論證過新教倫理是適應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產生之后及其發展過程最先對新教倫理的思想形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馬克思雖然也沒有否定過精神文化和意識等因素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但他明確表示了生產力與經濟基礎對于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因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主要借助生產力、商品、資本以及剩余價值等概念來分析資本主義興起的內在機制,深刻認識到西方市場經濟動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實質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家對利潤和利益的追求,即“資本家對利潤的無限制、無饜足的追求,推動著企業家不斷地進行企業內部和市場的分工,不斷發現新的生產方法,發明和使用新的技術及機器,并不斷拓展國內市場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很顯然,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發展道路歸根結底是由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經濟因素決定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宗教倫理等文化因素是屬于上層建筑內涵,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為經濟基礎提供精神動力。而宗教改革和一系列的宗教活動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力量為打擊和取代舊的封建勢力和封建宗教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它的發生只能促進人類思想進步和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不是決定發展道路的關系。由此,我們可以把馬克思的邏輯概括為,通過產生資產階級,進而進行宗教改革的一系列運動,使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從而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最終發展。
四、結論
實際上,在韋伯的觀點里我們可以體會到,資本主義就是關于新教徒在加爾文教的鼓舞下,崇尚勞動,拼命創造財富,同時實現資本的投資和社會再生產的過程。韋伯將這個過程的起源作為一個神話故事一樣的講述,為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過程涂上了一層神圣的光芒,也掩蓋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和階級意識。在韋伯看來,宗教思想的實質在于,它是資本主義國家某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理論,為資產階級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具有根本性的價值和歷史意義。
當然我們也看到,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宗教倫理觀,韋伯的宗教理論無論在哲學思想上還是在政治發展上都與馬克思主義的宗教思想和資本主義的觀點直接對立,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學習和借鑒一切我們可以學習的、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有價值的東西。所以,在理解和分析了韋伯的唯心主義觀點之后,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首先,正如我國的歷任領導人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不應該成為教條,它是我們學習和工作中的思想基礎和行動指南,是我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其次,韋伯將民族的長遠利益當做國家的最高價值目標的思想提醒我們,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等詞語并不是西方經濟的專利,它們本身也沒有資本主義的色彩,我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其經濟體系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這一點既要時刻明確又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孫宗偉.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動力——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解讀[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
(責任編輯:封麗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