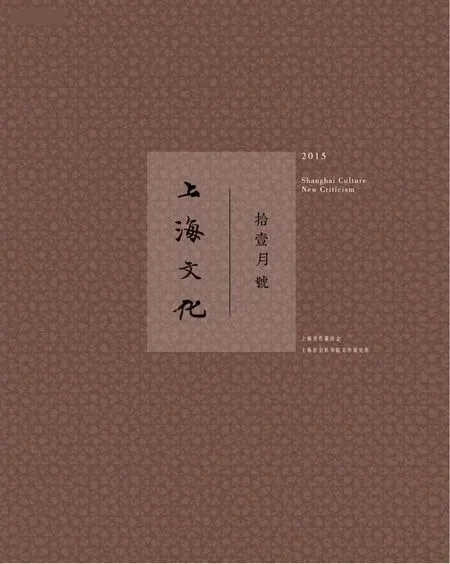雖有沖突,仍可和解李宏偉《平行蝕》
劉大先
雖有沖突,仍可和解李宏偉《平行蝕》
劉大先
《平行蝕》不是那種熟極而流、能夠讓人一口氣讀完的作品。它在結構上采用了類似裝置藝術的并置,敘述上的意識流動與電影蒙太奇自然地糅合,細節與場面的描寫精工刻畫、鋪張揚厲,更主要的是,它的主人公有著19世紀末期歐洲小說的自我反省和繁復的心理活動,這一切在當下以故事帶動情節為主流的小說寫作中稱得上另類——似乎重現了在新世紀以來幾乎已經被放棄了的技法探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接續了先鋒小說在形式上的探索。但是,一旦進入這個文本之中,就我的個人經驗,你會發現它絲毫沒有炫技的企圖,敘述中的種種技巧也并沒有帶來閱讀的障礙,它們只是延宕了閱讀的時間,讓讀者被迫進入一種緩慢的狀態中,給予他沉潛和反思的余地,帶來智性的樂趣,而不是像許多賽車一樣的小說,快速、線性、不假思索地奔向某個假想中的目的地。
這就像李宏偉本人,沉默寡言,有時候甚至有些靦腆,從來不會主動地進入一場寒暄式的交談之中。不過話題一旦開啟,關于文學或者寫作,你會感受到他內在的一種自足和自信。作為一個學哲學的資深編輯,李宏偉從事廣泛意義上的文學工作已經很多年,但是作品數量并不多,到目前為止只發表了幾個中篇和一本薄薄的詩集,然后就是這部《平行蝕》。相較于那些勤奮多產的作家,這簡直稱得上懶惰。可能因為并沒有打算從寫作中謀求內心滿足之外的利益,這讓他顯得氣定神閑。
但他其實是努著勁在寫,《并蒂愛情》、《來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有關可能生活的十種想象》這些作品都經過細致打磨——他比絕大多數批評家寫得還少,也經得起最為挑剔的批評家的眼睛。《平行蝕》開始寫于2003年,前后修改了許多次,到出版時已經有十年之久。當然,努著勁也未必一定就會寫出好作品,但至少顯示了他對文學依然保持了一種內在的敬畏、對自己的寫作抱著精益求精的有點不合時宜的態度。將《平行蝕》放入大部分已經非常世故的“70后”作品中間,就可以發現這是真正的有難度的寫作,顯示了李宏偉平和散淡外表下的雄心:他處理的是整個20世紀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一代人的精神成長以及一個社會的內在轉型,最終要解決的是人如何與歷史、現實以及自我和平相處的問題。這是我們時代為數不多具有思想性的文學文本。
將《平行蝕》放入到大部分已經非常世故的“70后”作品中間,就可以發現這是真正的有難度的寫作
說到“70后”或者“80后”,其實即便是社會學的代際意義上來說也是個偽概念,因為某個歷史中偶然性的十年,其內部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完全不能用斬釘截鐵的時間節點進行硬性切割。從一般性的直觀印象而言,“文革后”到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倒更像是一代人:一方面政治權力格局變化帶來了主導性意識形態的轉型,從而使得時代文化主潮發生了嬗變;另一方面影像藝術、電子游戲等在技術上的發展帶來了感官體驗和美學接受方式的變化,而信息高速公路和新媒體那種交互式傳播在這代人的人格塑形時代還沒有完全取代傳統的大眾媒體。生于1978年的李宏偉就是這代人中的一個,在《平行蝕》中可以發現這種作為記憶出現的年代背景是如何隱微潛在而又頑強地滲透到他的思想、想象與行為之中。不過,如果因此而將他敘述成一個“代表性”的個案,那是非常粗暴和怠惰的思維方式,他只是在處理自己的個人經驗,這種個人化經驗也許會卻并不必然帶來普遍性。
形式與意義
梁鴻鷹在序言中稱《平行蝕》為“成長小說”,確實不錯,但李宏偉并沒有采取一般成長小說那種通過線性敘事獲得高潮,進而達到躍升的路數;也不是全面地鋪展開主人公蘇寧的生活平面,在社會關系的聚集中烘托出性格的形成;他是營造了一個立體的建筑,以蘇寧十二歲時候在四川小鎮的事件記憶、大學畢業后在北京的漂泊生活為“夜”與“日”兩個生活段落,哥哥蘇平的人生軌跡作為平行的線索交織在他生活之中。中間穿插著兄弟倆1981年高涼山、1985年洗馬水庫、1987年上街中街下街、1989年鑲水鎮、1995年湖南、1999年自安村、2002年北京的時空節點發生的點滴故事。這些不同層次的時空故事經由閃回和意識流動,融合在一起,頗類似于略薩(Mario Vargas Llosa)、阿斯圖里亞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等作家那種“結構現實主義”。
不同人物與事件的拼貼呈現了世界原本的客觀和公正,作者從世界的創造者下降為世界呈現的中介和工具。只是結構主義自身往往會因為不可避免帶有先驗的預設而顯得僵化,世界渾無涯際且變幻不已,并且充滿各種糾纏、隙縫、漏洞,任何一種結構都是殘缺不全的。李宏偉讓小說的最后一部分“紀傳”,對蘇寧的女友、同學、老師、朋友、哥哥、情人各自進行了相對獨立的行狀勾勒,大約就是要彌補意識到的不足,而溢出于結構之外,設立一個個交錯的點。這些章節和人物都各自擁有自己的獨立性,它們彼此之間卻又相互關聯、互相影響。敘事人的身份不斷變化,而敘事人本身也在過去與現在的多重世界中自由轉換視角,這就如同樂高積木,每個具體的組件都單獨成型,但只有彼此鑲嵌、拼砌、組裝在一起,才構成了完整的成長過程:事件像積木一樣疊加起來,時間如同魔方嚴絲合縫,人物則是碰撞的分子。《平行蝕》創造了一個世界,而不是描摹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與真實的世界同樣完整和多樣化的世界。
如何言說現實,其實是困擾著新世紀以來中國小說的最大問題之一。觀察者發現,越來越多的小說趨向于故事化,在敘述和情節上下功夫,而在描寫與結構上則放任自流,甚至忘記了形式也是內容的另一面。小說的故事化當然使它的娛樂性加強,某種程度上也更加便于向其他藝術形式的改編,比如影視與戲劇。但語言本身的修辭功能無疑也是情感與思想表達的途徑,細節與結構也體現了觀念的內在展開方式。
李宏偉放棄了故事式的講述方法,而是賦予情節與人物自身以主體性,讓它們通過自己的組合完成整個敘事,從而使得蘇寧的成長成為世界的生成。因果鏈條在這個敘事里斷裂了,雜沓的事件與紛至沓來的情緒自行發生化學反應,但是,貌似毫無章法和邏輯可言的前后情節與蜂擁而至的人物及念頭,竟然奇異般地獲得了一種內在的和諧——蘇寧及他的哥哥蘇平的社會遭遇與精神成長中的一塊塊印記碎片慢慢聚合在一起,讓個體經驗形成了一幅時代精神般的圖景。
小說情節從1980年代的終結開始,直到當下依然延續著的現實。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就是完整性的喪失與碎片性的興起,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面臨的是一體性意識形態的全面瓦解,主體性合法性地位的黃昏,個人從集體性的事實與幻覺中退回到近乎原子化的狀態。但這種原子化狀態固然不再是原始個人的土豆般的存在,也與現代式的個人主義并不完全相同,它已經不再有啟蒙的信心與熱情,只能尋求孤獨個體的精神救贖,等而下之的只是謀求務實的物質與消費的滿足。這種碎片式的存在,正是需要碎片拼圖的形式表達出來,因而《平行蝕》是我們時代真正的“當代”小說。
80年代的終結
“當代”在《平行蝕》中是以1989年“短20世紀”的終結為標志性起點。這一年發生的重大事件甚至波及遠在四川綿陽的寧靜而偏僻的小鎮。向往著“盛宴”的少年蘇平和他的同學們通過電視、報紙來理解發生在遙遠地方的歷史激情,而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將是1980年代的終結。“1980年代”在后來的歷史敘事中已經被賦予了諸如改革開放、思想解放、人文熱情、啟蒙思潮等種種標簽,但是身處歷史中的人并無這種后見之明的自覺,他們憑著當時的感受乃至本能行動。他們的動因就像蘇平所說:“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不用自己的腦子想,不用自己的身體感受。將來,遭到的豈止是嘲笑,是掠奪和奴役。”幾個帶有理想主義氣質的少年充當試圖參與歷史的主體,體現出刻意將“1980年代”從既定意識形態話語中剝離出來的沖動,而更為極端的是李宏偉是讓蘇寧這個十二歲少年的眼睛來觀察和體驗,就進一步將歷史現象學化,讓歷史自己直觀呈現。
這個將成年人排除在外的童心化的歷史直觀,更多是一種情緒體驗,顯然與理性認知的“真實性”大相徑庭,但也正因為此,宏大歷史事件擺脫了抽象的意識形態論斷而獲得了真切的生命。蘇平和他的同學們打算去北京參加盛宴,但只有錢買一張火車票,蘇寧在懵懂中拿到那張票,踏上了去往火車站的旅途。我們可以看到蘇寧行為與思緒的混亂,不停穿插著的回憶和聯想,總是打斷和延宕事件的進行,直到他在火車站被父親帶回家。
這是個極其簡單的情節:試圖遠行到廣闊世界的少年戛然而止的行動,就像一場波譎云詭的夢。在交織現實與回憶的心理流動中,超現實主義的淡入淡出,被強行終止的少年行動,就像在強力下改編了軌轍的歷史一樣,形成了一種關于20世紀中國歷史的隱喻。而在這個轉型的時期,歷史是什么樣的呢?“這個偉大事件的唯一意義,就在于它要被我們錯過,我們現在創造歷史的方式,就是和它錯身而過。它的高蹈,它的不切實際,也只有錯過才能賦予其意義。如果不錯過,它也許只是一團混亂一陣狂歡,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事實證明,“錯過”確實是一代人的歷史命運。蘇平和蘇寧他們都錯過了表面上看去最為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但這個歷史事件的主體顯然不是他們這一代人的,他們即將在迅速到來的新自由主義、消費主義、資本邏輯的社會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哥哥蘇平很快在大學畢業后找到了進入歷史的途徑,他進入了律師的行業,成為時代的主流人物,參與主流的社會行為之中,并且似乎已經忘卻了少年時代曾經激情澎拜的精神探索。對于他而言:“錯過,是為了開啟新的層面,錯過也就是迎面撞上。迎面撞上了錯過而已。”通過他在湖南經手的一個案子,國有資產流失的內幕見于青萍之末,新時代的腳步舉重若輕地悄然來到。弟弟蘇寧卻沒有那么有驚無險地平穩過度,事實上他才是真正試圖進入歷史并且將這種企圖貫穿到日后大學生涯和畢業后的生活之中的。少年時代的記憶唯有給他帶來了創傷,他在年深日久的后來生活中必須要完成與歷史的和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與哥哥其實是兩代人。
歷史與和解
作為另一代人的蘇寧,在蘇平乃至他所代表的主流社會中如魚得水的人們眼中似乎成了個精神病人。“我們不適應時光,僅此便令人傷感”。多年前出走火車站的夜晚成了他記憶的黑洞,不斷吸噬他在現實中的能量,他必須不停地返回到那個精神起源的原點。生活中一些可以要被遺忘與摒除的私密記憶,反倒因為隱藏行為而變得更加得到彰顯,這段過去一直攪擾著他的現在,而在現實中他似乎也一直難以找到合適的定位。他成了“多余的人”。這個世紀末色彩的形象充斥在現代性興起之際的世界文學各種文本之中,他又有什么不同?
大學畢業之后,蘇寧并沒有像一般人一樣找一份穩定的工作,而是轉入了一種“觀察者”的生活,“我借助路人的面孔來尋找進入他們內心世界的方法,我猜測他們的各項社會符號,以為憑此能夠通達他們的內心世界。但往往到后來,一張張面孔接踵而至,淤塞在我眼前,它們晃動而模糊,彼此相似又不盡相同,除了粗重的近于窒息的喘息,一覺醒來,前一天的漫游和觀察根本難以留下任何深刻印象”。但是這個波德萊爾意味的“游蕩者”,同時也是黑塞“荒原狼”般的自省主人公,他很快意識到自己大張旗鼓的吆喝著觀察,恰恰證明了與世界還保持了距離。“生活是完完全全地綿延著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打斷它,也就是說沒有起伏。”這讓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精神難題成為不可能——精神問題從來無法靠精神和思想本身去解決。
但是,蘇寧其實并不是精神病人,他只是保持了完整的精神性,沒有被物化,雖然這種精神因為在易受影響的成長早期遭受過挫折而一時難以修復。他與神秘的出租汽車女司機冬子之間的相濡以沫或者說同病相憐,證明了擁有創傷記憶者之間的共情。他們都必須找到與歷史、現實、自我和解的途徑,才能真正進入生活,也就是進入歷史,而不是成為游離于社會之外的觀察者或者神秘而奇怪的邊緣人。蘇寧的同學洪英的一段話可以視為對這種創傷后退縮的反思:“只有不適應時代的窩囊廢才會裝出一幅1980年代遺老的樣子感慨不已。1980年代在校的一批人并非像你們說的那樣個個都是抒情詩人,而1980年代生的人也并非都不考慮你們所謂的意義問題,只不過,他們中考慮這個問題的人,都知道自己該如何行動,如何去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而不是空談。再說,都什么年代了。還在拿‘一代人’這種可笑的詞語來強行地讓自己置身于集體概念……你要不就是因為與現實的脫節而自傷自憐,要不就是因為懦弱和尋找借口。”“行動”和“空談”的辯證法無意中像一束光投照在徘徊不定的游蕩者內心。
這番話不僅是對蘇寧說的,因為有著形形色色精神困惑的人不止是他,丁楸、俞曉磊、武源、劉明、洪英、冬子都有著不同的癥結。他們彼此成為鏡像,他們的形象、行為與思考充實、填補了蘇寧主觀所無法涉及的其他方面。小說中有一個章節寫到眾人在哲學老師武源家的聚會,連續地出現鏡子與臉的意象,這是康德式的主體與福柯式的反主體在進行天人交戰,而拉康的大他者無處不在。最終李宏偉還是讓不同話語交鋒運行的軌跡呈現出來,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道:“‘紀傳’寫到的這七個人,退到了同樣的位置,他們只代表自己發聲,沒有誰領唱,沒有哪一個的聲音代表作者的立場。”所謂的主題思想就像一粒延異的種子,不停播撒出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就像許多年以前(1999年),蘇平與父親在祖母墳頭關于遠方生活與世俗生活的那場對話一樣,這些蘇寧的同齡人之間也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對話,盡管各自的觀點和理念不盡相同,所選擇的道路也各有差別,但它們完成了對于差異性的共存的可能性,共同繪制了當代青年歧路叢生而又并行不悖的精神圖譜。這些人并不能用“一代人”所能概括,所以《平行蝕》寫的并不是一代人的精神史,而是處于同樣時空中不同的精神面貌,它們之間可能貌合神離,也可能咫尺天涯,無論如何不能用某種單一的話語所能概括。
最終,蘇寧決定結束自己的觀察者生活,以普通的完全體力勞動者的身份存在于世。這并不意味著他放棄思考,而是認識到可能純粹體力有著接近精神生活實質的最佳途徑:“我已經做好了準備。我知道無論我停下來觀察與否,生活終將毫無意義地流淌而過,但是我已經做好了準備。”信仰如果尋找不到,那就以行動代替,這可能是蘇寧所能找到的與歷史和解的唯一出路。李宏偉通過對這個出路的提點,揭示了我們時代青年的精神底片——已經無法再有某種可以讓人激情澎拜、奮不顧身的單一的理念,更多人意識到理念本身也許就是虛妄的,因為精神無法脫離實踐自行產生,所以轉而投入實際的行動之中。于此,李宏偉在勾勒了當代青年精神圖譜的同時,實際上也展示了20世紀作為一個革命世紀“極端年代”的結束。現在獲得的各種自由和理念,雖然有沖突,但也可以和解和共存,各行其是,相安無事。
編輯/張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