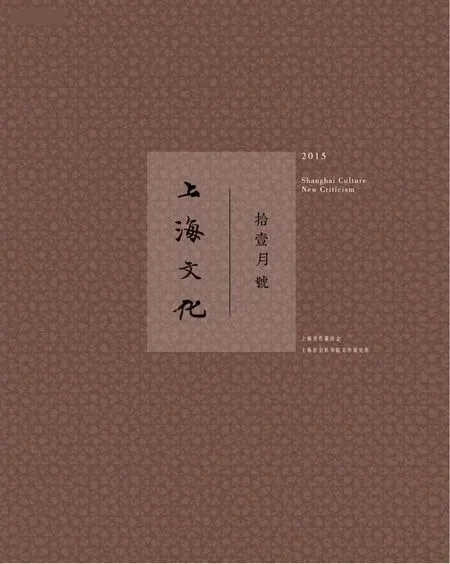詞的活化讀蕭開愚的《內地研究》
鄧寧立
詞的活化讀蕭開愚的《內地研究》
鄧寧立
他所占據的土地,只是他的雙腳佇立所必需的土地,他所擁有的依靠,只是他的雙手所能覆蓋的面積。
——卡夫卡《日記》
一
第一個詞最重要,因為第一個詞決定了整首詩的基調,它的音高、強度和走向。它定義句子,并在某種程度上拿捏旋律,掐準節拍。我們來看《內地研究》的第一行:
在河南的地壤中埋伏著一臺吸塵器。
值得注意的詞不是“地壤”,而是“吸塵器”,必須小心這個詞帶來的那種半高的強度和半現代化印象。它稍微陳舊,過時,不開闊,然而仍然來自現代生活中慣有的東西:一件器皿(在這里,由電驅動說明了什么)。關鍵在于,為什么要用這個半高度、半開合的詞來開始這首詩?人和吸塵器相接觸的地方帶來一種驚悚式的效果,讀者的腦中隱約出現一幅圖景,正因為排除了“人”,所以人的存在在這幅圖景里才變得不可或缺,并且由慣常所處的中心挪向了邊沿地帶。
它是個復合詞,一個舶來字眼,與前面定下血脈基調的“河南”和“地壤”兩個詞形成鮮明的對比。它擺放在這里使得第一行的結尾變得很重,鎮紙般壓住了句子的一頭,詩句的肯定語氣和平直的陳述氛圍(“在河南的地壤中埋伏著一臺……”)也加強了這種效果。機械的重量、單純的目的和“器”的緊窄韻腳呼應,然而,“埋伏”與“在……地壤中”卻又帶來了某種傷感的陳舊,像一幀來自過去的快照,一則訃告。“吸塵器”中的塵土與“地壤”呼應,半遮半掩地帶出了“出土”這個詞,這才是這行詩的真正目的。
于是,一首長詩便由這個名詞開始了,以名詞開始一首詩,尤其是長詩相當冒險,“吸塵器”在這里起了定音錘的效果,在一開始便把弦擰緊。這給了我們什么樣的啟示?首先,從這個完全稱不上純粹的詞我們獲得了某種警告:接下來的詩句是不規則的,混亂的,隨意安排韻律和節拍的,假如我們讀得更細致一些,能夠從中得知某種半機械的混合物將會以音高定準的姿態重復出現在全詩中,但這點我們以后再說。可以確認的是,作為句子里唯一一個三音節詞,它的體積不容小覷,它占據了過多的位置,而這不可能屬于偶然:它已經在提示我們即將到來的顛覆和叛亂。
我們繼續往下讀,讀者的困難到第二行就顯現出來,“屈尊臺閣”和“含悲”并不屬于你經常會在詩歌里看到的字眼,它們意味著什么,除了給閱讀帶來巨大的障礙?讓我們假裝粗心的讀者,跳過它們往下進行,接下來的句子絲毫也不讓閱讀的過程容易些,你會一路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直至第四句的中途,你遇到了一個“我”,在“粉紅的花生內含平流的黃河”和“亂倫的病毒的淵藪”中間,“我”第一次以親昵招待你,它舒緩密集名詞和長短句帶來的壓力,短暫提供了喘息的空間。那么,“我”干了什么呢?答案令人想起“吸塵器”那個逼仄、隨著詩句進行而不斷重復,并且越來越讓人喘不過氣的韻腳——“我派遣記性……調查所謂開始。”
“開始”給“吸塵器”打了個模模糊糊的眼色,比“記性”更公開和險惡。細心的讀者能發現,一開始搖晃的韻腳在這里由兩個“i”敲定下來,仿佛兩根釘子釘住木板。到此為止,我們勉強進行到了一頁的一半,我們得到了什么?不多,除了一些名詞。它們無規律可循,既有“交叉感染”這種醫學用語,也有常見的“紙袋”。詞語更替頻繁,長句與短句相接,中間這個“我”微弱得近乎看不見。與其說“我”與所有其余詞語有所互動,不如說照應了這一句開頭的“粉紅”。一種高度明朗的亮色——而且是純色——的視覺效果直接將我們引向“我”,而在此之前,“漏洞”、“幽空”和“漩渦”,形狀與災難程度上都將“我(wo)”中的元音步步推進,“我”的出現順理成章,是對空空的“紙袋”的又一次驗證。
到這里,我們總算是真正開始入座了。我們面對的是一次沖擊,詞語在不對等層面上向自己的對立面發起猛攻,不協調到處都是:“摸黑”迎著“宏觀”的頭撞了上去;“母親”這個詞分掉了“工薪”一半的面積,卻只能以回音形式存在于后者繁重、枯燥的新聞式效果中;“繁殖”被“負數”這個中立的、擠不出血的數學用詞所抵消。對立到處都是,以至于詩人像在追求一種碎片式的效果,“碎片就在那里,以一種非審慎的方式存在,先于任何努力。我們制定計劃,然而,當行動的時刻到來時,‘我們倉促行事,讓匆忙和粗糙的形式比有條不紊的工作更好地講述歷史事實’”(德勒茲《惠特曼》)。十余行后,詩人帶領我們回到了“漫天垂下的聽診器碰到考證枯樹的父親——”。前文提到,某種半機械混合物將以定準音高的姿態重復出現在全詩中,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用指出“聽診器”和“吸塵器”兩詞的相似程度,它們結構上的相近,以及它們都是由(不在畫面中的)人手操作這一點。相對于“吸塵器”來說,“聽診器”的機械程度有所下降,但這并不是由于它的構造,而是由于緊跟著它的“父親”,“父親”和在“工薪”中茍延殘喘的母親一樣,也在“聽診器”投下的醫學式、散發著消毒水氣味的面積中茍延殘喘。它用來校準音階,作為前者的回音而存在,但它的后面緊跟著一個破折號——一聲延長的呼喊,如同枯樹指向天空的枝條,如同父親干瘦的手指,形象上的酷似綿延畫面感,最終,這根手指和垂下的聽診器勾勒出的一個個問號一起——通過“遺產”,“結扎”,“墳墓”,一路指向“死亡”。
我們面對的是一次沖擊,詞語在不對等層面上向自己的對立面發起猛攻,不協調到處都是
但讓我們先不要沉溺于“所有的詩歌都在談論死亡”的陳腔濫調,來看看這里的半機械混合物和此前出現的有什么不同。它不再是“一臺”,變成了大面積的、大量的,“漫天垂下”既指體積也指幅度,從密度和廣度來說,都遠勝于此前埋伏的“一臺”,只不過在這里,每一副聽診器都是此前那埋在地壤里的吸塵器的對等物,以一種更隱晦的方式,彎曲的橡膠管的曲度模擬了那只從未伸出的扶在聽診器上的人類手臂。和“吸塵器”一樣,它不那么現代,也不算古老(事實上,兩者發明的時間相隔不過數十年)。并不完全是巧合,作為隱喻的封閉管道都是它們最初的結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被保留到今天,令人想起第三行的“蛇管”。聽診器不需要電的啟動,但其發明的過程就隱藏著某種啟示:“一群孩子在玩耍時,一些小孩在圓木一端刮木頭,而另一些孩子的耳朵無意間貼近了圓木另一端,突然高興地歡呼‘聽見了對面的聲音’。”(雷奈克《間接聽診》)通過干預,陌生而未知的另一端——破折號的另一端——暴露出來,發出聲音。在音韻上,這個詞起到了什么作用?破折號如同路標,將我們指向一個“扮演這些地點的這些地點”,漸漸地,“佳期”變成“低地”,直到我們走到不可避免的結局:“……師傅渡河。/得到一撮灰,/和一個人質”。“人質”為這趟旅程定了性,圓木的另一端發出聲音:器械變成了人。
和“河南”銜接“吸塵器”的句式一樣,“洛陽”銜接著“拖拉機”,后者以一種音韻上的靈巧為即將到來的“托勒密”做了足夠的準備工作。這是第三種人手操作的機械,它在自己的詩行中同樣處于不容忽視的中心地位,它與地表相關,而“眺望是托勒密的”——“我們為何只有三個?”半高度的機械,它們與土地不可分割的聯系,它們打散節拍(“加過倍”無疑包含了打破雙音節詞的野心)的努力,都伴隨“吸塵器”一起出土了。“地下室”是另一個與土地有關的,半封閉和押著同樣韻腳的詞,它不屬于機械,但它多用途的外形,建筑出身,以及隱晦地使人想起那部同名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這點,令它與機械處在同一高度上。
回到長詩的開頭,“吸塵器”提出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將由“地壤”——一個民俗的,地理的,同時地質的詞——回答。“地壤”謙卑地站在這部作品的開頭,帶著一種“不宜提及的死亡味”(W.H.奧登《1939年9 月1日》),“埋伏”和它連用在一起,令人想到棺材,感到迷惑,聞到濃烈的泥巴氣息——如果你和我一樣被冒犯了,這意味著我們多少做對了什么,好的詩歌冒犯人,并且總有一個靈敏的鼻子。我們已經站在第一級上了,讓我們繼續往下走。
二
“上海”提醒地點的變換,出現了一個“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讓第二部分變得更好讀了嗎?類似于個人傳記,它是否獲得了某種敘述角度?但不要忘記,“他”和“上海”實際上都來自于“地壤”,就像“吸塵器”和“地下室”深植于“地壤”中的“地”一樣,“他(ta)”中的“a”是直接是從“ang”中萃取出來的開闊、敞亮的元音,而“上”和“壤”則有著不容忽視的押韻。“他”,真正的源頭仍然來自那個隱晦,在這第二部分里沒有出現的“壤”。驗證這一點的是“邊疆”,一個同樣屬于土地,遙遙呼喚著“地壤”的詞。現在,除了偶爾被稱作“少年”,“他”和“他們”出現在幾乎每一行里,高調,鋪張,不再是第一部分虛弱的“我”,這告訴我們,主旨不同了,“我”和“我們”變成了“他”和“他們”——如果這還不能說明什么,看看地理上的形象改變吧。
《內地研究》的第二部分力圖建造一堵墻,或在竭力給予讀者關于墻的形象,這種要求曾經被真實地提出來(“求真的法術:撞墻。”),“集裝箱”的出現,“釘床”和“視野”的出現,都是為了指出這堵墻。“監獄”令人想到圍墻,“縣界”和“邊疆”,也與墻相關。暗地里,墻仍然屬于“地壤”的延伸,與泥土相關,同“地下室”同屬建筑物,是第一個在這首詩里佇立起來的高度。既然有墻,就有墻內和墻外,于是,“少年背后洪水著蚊蟲去到上海”,他背叛和離開了一堵墻(“洪水”——沖倒——墻),卻想要進入另一堵(“上海的監獄他進不去”)。少年失敗——自我教育——的歷史,其實是墻的歷史:“某日在墻下行便,發覺……”,“他們在隔膜的另一邊”,“環境優美,黃綠的大塊切割和點綴”,“等著金屬在滿身冷卻,他擔心指甲指出圍墻”,“獨眼凹在墻角,甲蟲慢爬它的陰影”,“在睡眠中,/山西、河南和陜西聯成一派觸覺”,最后,“他囚禁在他們的唾沫”,“唯獨構想的監獄是真實的”。
在這一部分,詩句致力反對形象的投遞,反對因為語言順利而最終導致結論的生成,反對形象,甚至反對墻體本身。因此“少年”,或者“他”,在這里不應被當做一個主人公,一首詩的敘述性口吻的寄主,被描寫和抒發的對象,事實上他被混亂和隱喻所割解,他是一張暫住證,一塊臨時允許人進出的區域,他是“幽曲煉成真理,堆砌在假山。/假設的禽獸啃來啃去”。他不影響時間,反而詞語以一種破壞的方式取消了時間對他的影響,詞語——和句子——取代時間而成為他唯一的存在形式。這個“人”被碎片所削弱,一種嶄新的表達方式呈現他的痼疾,這種表達方式高度濃縮隱喻,挑戰甚至無視了語法,句子擰曲到了難以讓人理解的程度:“索性裸眼睡覺,睡他的暫住證”,“他瘦得鋒利,像貧瘠培育的刻薄”,還有“他是定額內的,在睡眠中”。“裸眼”這個名詞被用作副詞,“暫住證”當成了一張供人入睡的床,諸如此類的扭曲俯拾皆是。再如“聽著旁邊校辦工廠的呼呼聲”,“呼呼聲”勾勒出了工廠的父權,它的麻木狀態,緊接著“擋不住的頹勢/局促過來,撲他的呼吸”,頹勢有人的高度和體積,它在呼吸,而不是后面的“他”。“呼吸”是奔著“頹勢”而去的,并且很清楚會在這里造成什么樣的效果。它在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擺脫我們對這首詩竟然試圖講述什么的懷疑,利用任何一個詞語的錯位迫使我們放棄從中讀出什么的希望,因為它所做的——和這個少年所做的一樣——只有懷疑、對抗和破壞。它的“擺設面貌”可以被三行詩恰當地描述:
囚犯睡在死路,在檢察的間斷插入僥幸的驚悚,
黑戶的女嬰突來一晌啼鳴。
家庭攔阻法庭,悲劇是悲劇眼睛的人的悲劇。
混合物仍然存在,只不過如今它們與人相關,基本色調屬于城市,和“聽診器”和“拖拉機”一樣,彰顯一種半高度的信心
家庭和監獄是互相對照的兩個部分,一道圍墻把它們隔開。他雖然已經身為“囚犯”,然而只要“黑戶的女嬰突來一晌啼鳴”,他就依然受困于家庭“僥幸的驚悚”。這張囚犯的臉,他的間歇式中斷,沒有持續的面貌,只有“檢察的間斷插入僥幸的驚悚”,“驚悚”在這一行的末尾投射出一束光,一種閃電式照亮,既是“檢察”的分岔、微弱的回聲,亦照亮了下一行開頭的“黑戶”。這張速寫的肖像是由“死”開始的,“黑戶的女嬰突來一晌啼鳴”為它提供了遠景,使它在遙遠的喉嚨襯托下愈發令人驚悚。那么近景呢?“家庭攔阻法庭,悲劇是悲劇眼睛的人的悲劇。”——我們看見了這張面孔的眼睛,“悲劇”重疊了三次,第一個較弱,第二個最強,而第三個則像是前兩個微弱的尾巴——通過“悲劇”遞進的方式,我們與這雙眼睛完成了一次對視:接上目光,然后近距離地凝視,最后,長久的被人遺忘的回顧。這樣一次對視里,句子完成了“家庭”到“法庭”的嬗變,人物命運得到揭示,而這張肖像的最后一筆——“人”——也完成了。
混合物仍然存在,只不過如今它們與人相關,基本色調屬于城市,和“聽診器”和“拖拉機”一樣,彰顯一種半高度的信心。在這一部分開頭,“他領導一伙周口少壯盜集裝箱”,“集裝箱”完全是個城市的字眼,喚醒我們內心的城市風景,這仿佛是個頗有希望的開頭,不幸的是,結構和音調上,它的先驅仍然是“地下室”和“吸塵器”。它的外形讓人聯想到濃縮的監獄,這是個封閉、工業化、剛冷的字眼,和它的前身一樣,半現代、半過時、屬于上個世紀,仍然只有一半的高度。假如“集裝箱”讓我們俯瞰城市,那么接下來,“鐘點工”和“老虎機”直接將我們的目光拉向街道,拉向墻的角落:家庭。
和“鐘點工”和“老虎機”聯系在一起的“妹妹”、“弟弟”出自家庭,但兩個單一音節構成的詞不管在音律上,還是詞語結構上都敵不過復合詞,“鐘點工”、“老虎機”的重量勝于“妹妹”和“弟弟”,體積上也占絕對優勢。“老虎機”勝過了“人”,機械已經由最初的發明啟蒙者變成了引誘人墮落放縱的工具,這是“聽診器”的另一頭,“妹妹”、“弟弟”呼應了“考證枯樹的父親”和“夜紡”的母親。在破折號的另一端,“漫天垂下的聽診器”碰到的是“鐘點工”和“老虎機”,“人”在這里讓人恐慌地沒有位置,而詩人在第一部分就已經預見到令人絕望的結局:“孩子,給父母喂奶吧!”的諷刺呼喚,以及“現在,給祖先留下遺產”,得到的不過是“……七個白天……七個夜晚”。
接下來的詞都成為了“老虎機”和“集裝箱”的余音,比如“暫住證”——一個地點和收容場所;“肺氣腫”——一種疾病;“充氣娃娃”——欲望,工業產品和概念;“私生子”——血緣關系的結痂。不外乎變形,墮落,人與社會關系的畸形結合,或是欲望的失敗。這就是“老虎機”和“集裝箱”帶來的東西,遺留在它們封閉的箱形結構里的東西。這些現實的殘余物,“起來一摸,是床邊鞋的注腳”,“真實晃眼,人道怎么框架得住”,在對它們的失望下,更頑強的長方形出現了:監獄。
只有監獄,兇器合法運動,
只有監獄,沖鋒含而不露,
只有監獄,沉溺在過去,打撈著真相,證實什么發生并且邪惡,
……
“操場”、“工地”和“戲臺”有著同樣的長方形,但只有“監獄”得到了重復,和“在睡眠中”不斷被強調一樣,它旨在通過單調的重復抗爭終會到來的結局。而結局,是什么呢?“趁其尚未器皿(又一個可怕的長方形!)和溶解。”這是一行令人震驚的詩,震驚程度比得上前面的“父親撇嘴如故,像塊工地”,兩行詩都蘊含著某種程度的暴力,后者實際上寫出了“父親……工地”這樣戰栗的等式。把“器皿”這個名詞用作形容詞,使讀者模糊憶起前面一系列封閉形態的箱子(“吸塵器”,“集裝箱”,“老虎機”,“監獄”),器皿的根須深入歷史,它的兩腳穩穩地踩在工業生產和手工制造中,它的出現比“溶解”更令人意想不到。它與溶解逆向,它自己本身的發音方式就有一種封閉的共振。它穩固,仿佛水泥,這本身就已說明了什么。
三
第三部分,速度加快,漂浮在字里行間是金錢的各種表達方式。換句話說,經濟。在一篇創作談里,詩人談到:“第三部分處理了河南,陜西和山西三省自分稅制實施起共十幾個年頭的財政預算報告和稅收年度文件,我采用省市縣三級公布的公開材料,所針對的相關分析及其理論展望,分別出自三個省的社科院和廳屬以及市縣局屬的財稅專職研究人員”
(蕭開愚《多余的話》)。
出于取材原因,語言也經歷了自己的稅收稽核,所有熟悉的表達經歷了地方上的財政精簡,“整治重點”則落在了“文件和報告”上。讀者面對財政和稅收術語,頻繁的數字列舉,以及直接采自官方報告的整個句子:
《河南省契稅實施辦法》:自2008年11月,首購90平米及以下,稅率1%;90至144平米及以下,2%;144平米往上,4%。
可憐的讀者還沒恢復過來,就被更多的數字,更多的列舉和術語所淹沒。“撤消幕布、道具和燈火”以后,“裸露的臺面不怎么羞澀”。在前兩部分,我們遇到了土地、人物,隨后需要的,則是尊嚴上的平等。經濟,作為一種“準確的學問”(W.H.奧登《1939 年9月1日》),還有什么比這更平等的呢?數字由等式兩邊組成,正如名字把兩個未知的世界聯系起來,名字是召魘,數字則啟動了整團狂怒的黃蜂。這里我們來到的是身體圖像的延伸,是法律……“被不了解的法律所統治是多么痛苦啊!……因為,法律的本質必然導致其內容的隱晦”(卡夫卡《中國長城》)。
疾病進入詩歌,在這里,它進入得更加猖狂,“琳瑯紛至,像腎結石的顆粒激動了齒輪”,“血沒人要了,艾滋病救助三點一億,太少”,“地方椎間盤突出,中央皓滿而旁溢”,到處是病,連“作者”也被傳染了(“飛機傳播皮膚病,癢它的作者”)。一副“扭曲的骨架騰挪著,樹枝代替樹干”,再次呼應了“考證枯樹的父親”。我們看到了一具軀體,它咀嚼,“回啐好不瑣屑”,它說話、動手,“打折扣、官腔、落水狗”,它“活像合同的弱者”。這具軀體是經濟的,一切表現從屬常規,“笑分五類,對應商品五種”,在這里出土的不再是“吸塵器”,而是一部“印鈔機”,是“試驗田”和“無底洞”。
關鍵不在于如何理解用詩歌語言寫成的一份經濟報告,而在于如何理解由詩歌語言(官方、半官方語言和口語)所維系的一個行政區域,它是一個龐大帝國的縮影,它的規劃、它的收益和分成,都被拓印到了語言中,貨幣的流向變成詞語的流向,而稅收等級的劃分繼承為不同用語之間的上下關系。通過把“日常經濟的一點警惕”轉型為“日常的厲害”,稅收、財政和預算擁有一種歷史性向度,重新為語言所用。“人”不再被稱作人,而變成一系列群體,“人”投身職位、親緣關系、地方架構和社會地位的變形,“包工頭”、“主任、干小姐活的女兒”、“教師”、“學子”、“農民”、“河南人”、“糾察隊”、“下崗職工”……稱謂本身就能告訴你一部結構史。對表面的重新釀造,造就了韻律的新奇險境,例如:“醫社保”與“二三比小”押韻,指向“減災、調價與平衡進口”,最后“覆舟”同“腹腫”一拍即合時,我們仍能聽到數十行以前那個音調中庸、平折的“茍活”。
除“印鈔機”外,我們來看看“桴鼓”。這是個當代漢語里面已經很少用到的詞,但它自身包含了從拿起鼓槌到鼓槌碰到繃緊的鼓面、發出聲音的一整套動作,甚至包括敲擊時迸發的聲音。
……桴鼓傳統的淵面,……
語氣上,“桴鼓”延續了前一句“何妨并駕”的年代感,音韻上則暗合“函數”,然而,它的歷史感與“函數”、“金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核舟記》),更早則有“提桴鼓立軍門”(《史記·田叔列傳》),“教化興行,應如桴鼓”(《路史·后紀三·炎帝》)。把“桴鼓”作為動詞,與“傳統的淵面”聯合(“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音調上有鏗鏘之感,畫面上則因為刻意而為的不協調而兼具速度和擂鼓的重量,與“桴鼓”的涵義對應,由此可見作者詞語取樣的寬度。
來自《圣經·創世記》的“淵面”,引出了第三部分的另一個主題:面。對表面的重新利用,為表面找到了煥發和棲息之地。表面取消深處,但并沒有令深處消失,而是把原本縱向的活動變成了橫向。這是數字和列舉的目的,“進入深處并隱藏其中的動作讓位于向側面輕微滑動的動作;深處的動物變成沒有厚度的紙牌形象”(德勒茲《劉易斯·卡羅爾》)。沒有被解釋過的,數字,作為政策說明或遞進……本身就代表一種形象,問題在數字中壓制為平面,出來的是長條狀的匯報語氣句子,狀如工資條。“數學很好,因為它創立了面,并讓一個世界得到安寧,在這個世界里,深處的混雜將是令人恐怖的……然而,深處的世界依舊在表面之下低沉地吼叫,并威脅要使表面爆裂:怪物盡管倒下,躺下了,卻仍然糾纏著我們”(德勒茲《劉易斯·卡羅爾》)。為了深處的怪物能夠存活,表面必須足夠光滑,足夠平整,薄得恰到好處,能夠纏繞起來,以隨意的形狀接近自己的反面,“畫卷的帶子纏繞起來,形成一個長方形!不再是畫紙本身纏繞在一起,而是其中被表現之物纏繞在它的表面”(德勒茲《劉易斯·卡羅爾》)。
“表面的荒謬”,它“不讓任何東西經歷意義……因為荒謬的多樣性足以解釋整個宇宙,解釋它的恐怖和榮耀:深處,表面,立體或纏繞的表面”(愛森斯坦《雜耍蒙太奇》)。
四
閱讀《內地研究》的開頭時,我們已經談到,里面有一多半的詞語屬于“地壤”的延伸,是那片偏狹、不規則、刻意脫離中心的土地上長出來的東西。這個具有考古學意味的詞,為許許多多別的表達提供了養分,從視覺上而言,“地”是封閉的,“壤”則已經被翻耕播種過,它們能夠囊括一切與地面相關的東西,不管它們有沒有根植或從屬土地的能力;另外的詞則屬于“吸塵器”,一個更眼前、與自身關涉的詞。從修辭層面考慮,兩者都激活了屬于自己的傳統和韻腳,但另一方面,不管是格律上還是視覺上,兩者都代表了來自不同源頭的危險,前者來自血液,后者來自組織的衰弱和硬化。讓我們短暫地回到第一部分,回顧一下“地壤”在其中如何得到闡述:
他們硬化。土質吸收他們的外形。
土質:含化著,排泄和除名,到底忍住。
土質:這種贊成態度,這種擱淺,這種栽培,這種不加甄別的親昵,這樣黃昏在牛蹄,這樣為邊區隆胸。
下下一行是“唯獨這里,地質矯枉過正”,但暫時不需提到它。需要提到的,是第一部分,在所有土或壤,地或質(包括疆域、邊界)出現的地方,其相鄰的植物都半死或將近死亡,“麥地休眠,農民進城”,“這是地殼,抽屜套著抽屜”,“地質做過結扎,像空煙盒”,它們排列出的形象揭示一種“癌癥般的枯槁”,不是已死、將亡,就是在一種僵硬麻木并且意識不到自身癥結的狀態中等待死亡,或是將睡夢(“休眠”)當作了存活的常態。在接近第一部分結尾處,甚至出現了“死亡給地壤核心進去一副骨骼”這樣駭人的句子。這就是“凡穿地四尺,為壤五尺,為堅三尺”(楊輝《九章算法》)的這種物質在這首長詩里的形象:空有外殼,中心虛泛,無法賦予任何事物生命力,自身已經習慣麻木并接納死亡(“死亡……核心……骨骼”)。在這一形象面前,“收盡播種,跟電梯到地下室下載的,/都是我們所恓惶的”,空洞的核心激起它對象同樣空洞的恐懼,“收攏不了什么,想起一點什么”,它所提供的并非收成而只有回憶。第三部分的“淵面”正是來源于這樣一個形象(“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當我們朝下望去,只有無盡無邊的空虛。確定“地壤”的性質的,還有第三部分的兩行詩:“三地本是留白,影射旁邊的硬黑,/順帶四面邊緣,層級深闊的空缺”——從深度看,從層次結構看,情況改變了嗎?沒有,它仍然是第一部分中“排斥焊接……眾人無倒影”的那片土地。
回顧這個貫穿全詩的形象,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第四部分的開頭。“會當廣植幽篁”——這是這片土地上第一次長出綠色的、向上拔節的植物,它以某種祈使的姿態站在第四部分開頭,蒼勁,迎風搖擺,好像上一部分結尾的“夙愿”的一個微弱的回聲,一個遙遠的背影。表面來看,這個句子音調開闊,飽含希望,可“幽篁”仍然是“地壤”中長出的東西,那個暗示著它出身的韻腳,不管多么敞亮,立刻把我們重新帶回“含化著,排泄和除名”的世界。在第四部分,這片土地長出了許多東西,而它們大多數都與種植或者試圖種植的行動相關,稍后我們會看到“種菊”、“林莽”,“地壤”第一次露出它的根(“灌木的殘根淤積在殘根上面”),會不止一次看到果實(“沒有通過檢驗沒有批文的果實”,“刀槍不入的果實”),且不說所有這些植物都有自己的傳統(比如“種菊”),有自己的色彩、出身和名諱,這是否表示著“地壤”擺脫了必然的命運?但“果實”很難成為真的果實,而“樹不落葉,不落就不落吧”,所有的植物最終都與某種暴力的進場連接在一起,被“砍伐”、“修剪”和“整理”,如果這一切還不足以說明,詩人甚至直接指出:“綠色是個觀念,是恐嚇。”了解這一切以后,回頭來看“幽篁”,便會知道這根綠色的手指所指向的,還是那片“幻覺走偏,忽左忽右”的風景,還是那片半死之地,“會當廣植幽篁”終歸成為落空的希望。畢竟,在漫長的詩歌傳統里,“幽篁”更多地與孤獨、悼亡、困境有關,它是死亡之物,懸崖邊的恐怖,一張幽魂的臉:“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后來。”
更深入理解這種綠,理解它為什么被放在一整部分的開頭:
話說回來,搏斗由來已久,不只綠與綠的變種,
綠色有時黑,有時紅,有時灰不溜秋,
動物有時是怪物,有時是人物,有時交媾著交流交媾,
……
綠色反常,恐怖,以規模壓制混亂,此類反常和恐怖來自于同一片“地質家的羅盤隨配隨成對”的土地。那里的的植物不像植物,它們“按桌椅和散架的形狀,鋸子和錘子的用途”成長起來。這一部分關于綠色,然而陸續現身的綠色無不類似人工的小丑。以虛幻、不存在的竹林開頭,以同樣不存在的枯草結尾(“古風猶如草枯”)——雖然,真正的結尾是“鳴條”這個死氣沉沉,甚至預示了一個朝代的覆亡的詞,但為了保留虛假的希望,還是允許我們把目光停留在枯草上吧,它孤魂般的聲音呼應著開頭那張哭泣的臉,“草枯”于風中的搖曳召喚著“幽篁”,還有比這更清晰的對應嗎?“因為對一位詩人來說,詞語及其聲音比意念和信念更重要。說到詩,起初依然是詞語”(布羅茨基《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
諷刺的是,在植物不像植物,綠色不像綠色的詩歌世界里,“人”卻呈現出植物般的面貌,被拉平到了植物的水平,和植物被修剪成人工形狀一樣,唐突對抗協調,扭曲違背工整。“為他涼拌——鐵青的——轉基因。/他著書立說,科普我們,/綠色,已第二次革掉一半,/……/刀槍不入的果實,叫他獨吞,/……”當像“轉基因”這樣一個在文學中使用頻率相當稀疏,在詩歌則更近乎前所未見的詞出現時,如果我們把它就這樣放過去,意味著我們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讀者,或者是相當懶惰的讀者,看你愿意選擇哪一種。“當一個名詞被超過一個形容詞修飾,尤其是在紙上的時候,我們就會變得有點兒起疑”(布羅茨基《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而當一個名詞看似沒道理地出現,而且是在紙上的時候,我們就會變得不止“有點兒”起疑了。這條變異的莫比-迪克在船上撞出了一個洞,假如亞哈船長不這么自信,我們的船差些沉沒。正是這個洞口的打開,令別的和“綠色”相比幾乎是怪物的詞能進入這首詩,比如“β-胡蘿卜素”和“金米”。這個闖進來的怪物,再讀幾行,才能躲避它帶來的疑慮和驚訝。
名詞……一個沒有火種的普羅米修斯。“以個人的名義,他向宙斯發出了挑戰,令其成為世人的笑柄。這個無政府主義者觸及并撼動了我們身上那些未知的,敏感的區域”(喬治·杜梅澤爾《普羅米修斯或高加索》),這個穿鑿出來的洞穴,仿佛亞哈——也即詩人——意志力追尋的對象,它來自綠色,但站在“綠色”的另一邊。它的注腳——正如“地壤”的注腳是種植和生產一樣——是遺傳和導向。結合“科普”、“改制”和“城鄉結合部”,另一種歷史拔地而起,與“幽篁”、“戴勝和蟬”的歷史相對立,每一種都在另一種中找到自己的回聲。“轉基因”有這種作用:普羅米修斯舉起了火把。它讓人想起亞哈的獨白:“你再聽著,——下等人。所有肉眼看見的東西都不過是紙板做的假面。但是,在每個事件中——在活生生的行動中,那些無可置疑的行為——在那里,那未知的,但是合乎理性的東西,會在毫無理性的假面之后顯露,逐漸成形,凸現它的特征。如果人要出擊,就應擊穿假面!若不擊穿圍墻,囚徒怎么到得了外面?對我來說,白鯨就是這面墻,它在近處堵住了我。有時候我覺得,圍墻外面什么也沒有。但這已經夠了,它給了我任務。它就壓在我身上”(麥爾維爾《白鯨》)。“人類寧愿選擇對虛無的意愿,也不毫無所求……”(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幽篁”和“轉基因”立在“淵面”兩端,完成了第四部分,后者乃是已被遺忘的“在河南的地壤中埋伏著一臺吸塵器”的一個后裔。它的韻腳,對那臺機器的補充,它們近親般的外貌——這是一次回交的過程,野生近源種的基因流已經轉移。
五
我將談論詩人的一些特定手法,比如刻意將兩個讀音接近的雙音節詞并排放置,造成類似鐘擺的效果。這種技巧大膽得危險,因為刻意而為的近交和共生,不免表現出對教育的蔑視(在任何一種語文教育里,人們首先教你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區分兩個讀音相近的詞),它同樣打破了基本的寫作規則,即能用一個詞表達你的意思時,別用兩個詞。而詩人不僅用了兩個詞(把所有的選擇都用上,不選定一個),還公開地表示這并不是由于疏忽或過分粗魯而犯的錯誤,詩人確保他的讀者知道這一點,因為他很快便在不同的主旨下一再使用同樣的手法,甚至把這種手法變化加強,以便人們不會產生誤解。避免相同韻腳的字眼出現在一行詩里的本能愿望,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任何詩歌都不愿意在一行詩里同時應付兩個雙音節詞(通常來說,一個就夠了),更別提它們還有相同的韻腳;另一原因則更重要:這令詩人顯得軟弱,控制不住自己的詩行,他的聲音晃動和搖擺,以至于不能選定一個敲定自我的詞語。這些理由都很充分,在開始寫作時是有道理的,但莎士比亞說過(雖然是通過哈姆雷特之口說的):“顧慮把我們都變成了懦夫。”這種并置顯然有勇敢得多的動機。那么,為什么路西法(別忘了,他原來也是天使)和天使要相聚?鐘擺為何晃動?
第一個詞是出現,而第二個詞,才是時間抵達和離開的方式,它表現真正的在場
一些近音詞由“和”聯系在一起,比如“無非砍伐和濫伐”、“野兔和野物概出”,另一些直接用句號,或逗號連接,如“產量。計量。過量。”、“像血糖、血脂和血壓”;經過變化加強的手法則直接把三個以上的近音詞,或兩個讀音相去無幾的詞聯系在一起,如“使走動連坐走婚,跟走獸跟抽風一樣,日子何必日夜”,以及“真大膽,真瘋了,該用煙酒整治研究”。我們沒能看見投入水中的東西,只望見水面在瘋狂晃動,留給我們的正是這種晃動,晃動還要過一陣子才停止,在它停下來以前,我們無法判斷這里的語言到底有多深,無法通過調查核定聲音的積水線、防水線和警戒線。自然,擲進去的是讀者自己的目光,一開始造成晃動的物體已經不復見,但水面仍然晃動、移位和顫抖。小范圍的顛覆和混亂,目的不僅僅在于語義學上的冒險或玩弄手法,而在于讓讀者看到第二個詞。它并不簡單地等同于第一個詞的疊加。第一個詞是出現,而第二個詞,才是時間抵達和離開的方式,它表現真正的在場。如果說第一個詞是出生,那么它之后到來的詞才是宗教。由于接近和緊靠,第二個詞才能被清晰地看到,因為有“日子”,“日夜”才有具體而鏗鏘的形象,“日夜”帶出了“日子”里那個推遲到來的夜晚。
另一手法是重復,如“他們像灌木的殘根淤積在殘根上面”、“山頭枯對山頭”、“我們睡入灰燼,流水的灰燼”,第二個詞在第一個詞的死亡上出生,它是只雌蜘蛛,吃掉交配后的雄蛛。“性食同類”時而意味著一種推進(“我們不死,我們有不死性”),偶爾打響一種反叛(“我們遵道而行,道而不是道德”),在《內地研究》第五部分,這種手法出現得尤其頻繁,讓人想起“地獄看到/天堂從天堂中墜毀”(彌爾頓《失樂園》),第二個“天堂”只剩下空殼,第一次被提到時,它已經在自己的回聲中墜落,這個“地獄”看到的蛻盡的空殼,已經變成了地獄,加速的地獄,故而“驚恐的它想要逃走”(彌爾頓《失樂園》)——即使“天堂”,在被重復時也墮落成“地獄”,其余的詞也不外如是。第五部分重復得最多的是“我們”:“我們的老家和祖墳”、“我們的回憶”、“我們的小韓”、“我們的灰燼”——“我”在“我們”的疊加中不斷虛弱,走向自我稱述的反面,最后,“我們”變成了什么?
我們模仿道路開襠,是道理及其目的,是流水的灰燼,
我們過河、回潮,給火藥捂在燃過的燃點,兩腿發軟。
一路漫長的墜落之后,“我們”不過一些“流水的灰燼”。
“小韓”當然不是“我們”的,“我們的小韓”這種諷喻和“我們是老子的老子”一樣,來自口語,表達了對待口語和書面語不分厚薄的態度。能夠使用第一個詞的作者很多,但能駕馭第二個詞的作者寥寥無幾,在什么時候,第二個詞能發揮它的最大功用?在被重復到近乎癲狂的地步的時候,而這正巧證明它地位的虛弱,它不被理解的現狀和缺席:“我們寫歷史,讀歷史,我們的反復縮短并壓扁歷史,我們抄襲不走樣,我們反歷史,/……”通過“歷史”的不斷重復,“歷史”反而走樣了。重復意味著對實體的反對,因為實體首先是獨立的、可相互區別的事物;重復同樣摒棄了交流的欲望,確立了作品獨一無二的面貌和藝術家自己的形象:“制造某種東西的愿望,也許永遠是藝術家自己能意識到的最費心思的事情,它是獨立于時間外的一個常量。真正發生變化的是他的媒介,他對口語和書面語的態度,他感興趣或有能力感知的事物,他想要與之交流的觀眾”(哈羅德·布魯姆《讀詩的藝術》)。
從鐘擺的沉重一晃(也許并沒有偏離原本的位置多少)中詩人竊得了少許時間,非常少,無法用刻度來衡量,幾乎沒有重量,它是居住在修辭里的時間,是《芬尼根的守靈夜》里“再多給馬克先生三夸克”的時間。在這一個單位擺動的時間里,居住著修辭所試圖跨越的最大跨度,從“計量”到“過量”的距離,也就是鐘擺的一晃過程中,有我們的全部恐懼:“如果我們不知道恒星距離我們有多遠,那么對它們就會簡直說不上什么來。天上一顆不顯眼的小小星點可能是地球跟前一個本身并不發光而只不過反射陽光,本身還不到一米的東西,但也可能是一個光強相當于整整一個星系,由于遠在宇宙深處而原來的壯麗景觀不被人們辨認的天體。想要根據地球上可以直接測量的間距去推測宇宙中的距離,這絕非容易”(魯道夫·基彭哈恩《千億個太陽》)。
每一個被寫出來的句子都不過是多數話語的殘留物,而每一個作者都像在同一場戰斗中幸存
在詩里提到醫院這個詞,比在廢棄之地真正建造一所醫院要困難得多,因為不管承認與否,當一個人坐下來寫作之時,他語言中的大多數就成立了。但所謂的少數,真正存在過嗎?相對于大多數而言,它們簡直無法看見,只有在你意識到無法讓它們在作品中發聲時,它們才會真的在場。它們的使用頻率并不低,其中一些恰恰很高,而且常見、平凡,被無數喉舌(私人的和半公共的、智性的)輪番擁有,然而它們無法進入創造性寫作的命運與此無關:它們被選擇性地忽略了。社會共性話語造成的集合,在頭腦內部累積的沉淀,比任何個體所能想象的要深入得多。它根深蒂固,有自己的矯正色、自由體和發聲器官。它自帶一段歷史。事實上,這并不令人驚訝,考慮到使用“風景”還是“風水”本身就存在著一種刻意而為的視覺性偏移,這種選擇最終將決定焦點所在,而是否把“地層”替換為“底層”,效果則是致命的。那么,當你坐下來決定你要寫作的時候,表面上看,寫作……正在自然進行中,但每一個被寫出來的句子都不過是多數話語的殘留物,而每一個作者都像在同一場戰斗中幸存。究竟是詩無法容納醫院?還是一個像醫院這樣的詞(籠統,中立,可以在口語和官方話語中存活),以及與它類似的詞不能輕易進入一首詩?這種選擇自然的嗎?我們可以深思熟慮地說是,即使實際上,早在作者學會寫作之先,早在成形之先,作品就已經學會避開它們。作品受過訓練,不去招惹沼澤或者語言中的礁石,作品遭受自然光源的投射,向后蔓生出巨大的人工陰影。
每一個詞都帶著自己的大寫的概念,它叢生的環境和社會人工學,這使投射在紙上的最終表達更像是它的剪報,小于原生詞整體的全部。其中一些詞未達紙上就已經死亡,另一些,在運輸過程中,意義產生折損,或在我們沒有注意到以前悄然折身,回歸書面語的跳躍、檔案的穩固以及官方報告的平衡。在這樣的單調呈現中,寫出來的東西很快終結于一道巨大的水壩,橫亙在人與遠處可以見到的風景之間。唯一的人工造物,把自己偽裝成自然風景,自豪于它不久以前還與自然風景相去無幾的面目。我們像在書寫一種停滯的平面,它更類似一面鏡子自身的單義反復,而非意識的真正歷程。“一個詞的命運,取決于其不同的上下文,取決于其使用頻率。在俄語印刷品中,‘耶夫雷’出現的頻率之少……擁有某種類似于四字粗口或性病名稱的地位”(布羅茨基《小于一》)。創造性的狹窄:隱瞞首先由自我隱瞞產生,隨后又被偏移和荒廢排除。你身體的某個部位,你的故鄉在方言里的發音,人口普查的數目,小數點在一句話里的位置,全都被同樣的事物排除,它們找不到進入,那道路許久以前被荒廢。寫作者,他的語言如此穩固,這與他是否優秀或合格無關,值得慶幸(或者不)的是,作品愈平庸,言語愈穩固。處于中間位置的大多數作者,他們的作品已被自己事先審查過了,他們在一團又一團的氣候話語里遷徙。
我像“緊緊攥著一個佛羅林,大步沿著白金漢大街朝車站走去”的那個年輕人,看到“那個具有魔力的名字”就在頭頂,卻發現它名不副實的時候,“我意識到一種靜默,就像禮拜結束后教堂里充溢的那種靜默”,在這種靜默中,我開始寫作,在一長段自我校正中掙扎著尋找自己的聲音。奇怪的是,人很容易開始習慣:急迫并不存在,沒有必要改變。當聽到一個詞的時候,你不僅希望在報紙上讀到它,你還渴望自由地使用它,至少保留自由使用它的權利,甚至能夠——擁有一種產生自厭惡的、朝向一個明確存在對象表達鄙夷的權力。但事實是另外的情況,你聽到和讀到的詞往往沒有同一面貌,它呈現出來是一回事,落腳在你所熟悉的語言中又是一回事,寫作變成一種防腐劑,其過程則衍生為去腐處理,你看到的擁擠栩栩如生。當我看到一個詞,看到它所從屬的一整個句子和所有站在它身后的表達,我不再產生厭惡或喜愛的愿望,不會流連擁有它的幻覺,我自知它不會在我的語言中留存多久,它需要的不是詩人也不是歷史,只是“棍子插進食管,聽力所以尖銳”。它通過我所表達的,并不會比它通過大部分語言而達成的更少或更多,因此,我只會像那個被現實的緊密織物所欺騙了的年輕人,“明白自己滯留不去也無濟于事,卻在她的攤位前流連著”,最后,“我抬頭凝視著黑暗,發覺自己是受虛榮驅動又受虛榮愚弄的可憐蟲;我的雙眼中燃燒著痛苦和憤怒”(喬伊斯《阿拉比》)。
大部分時候,我們讀到的是擁擠!擁擠代替意象的呈現,把閱讀悄然轉換成視覺的廉價體驗。但這樣一部作品,混合了官方語言、半正式語言、歷史語言和社會化語言中的幸存者,收治了口語、書面語和地方方言中的遺骸流民,解散了公文和新聞報道中的集合隊列,聚焦了夜聊閑談里的邊角碎料。詞在詩行里旁若無人地進進出出,在頁邊角,在每一行的底部,在詩的開始,在句號和冒號的陣前,在段落的末端。“內地”透露了它的野心,產生了一種圍欄式效果,然而,這樣大規模的擴張仍然前所未見。
假定亡者活著,我們反而值得惦記。
值得惦記的是“我們”而不是“亡者”,記憶存活在我們身上,我們的詞語,我們關于活著的假定,都將在我們身上完成出生,蘇醒,死去,這一行詩里面沒有任何一個對象真正活著,然而它卻揭露了寫作的身份。區別是,它試圖揭露的是寫作本身,而并非寫作者。寫作,是對時間盡頭衰頹的認證,是對體內群島的肯定,假定亡者活著,從而惦記起“我們”。一個詞語在我們身上存活的全部長度,取決于諾特先生在房間里觀察自己走動的方式(而不是他實際的走動方式),取決于紐沁根太太在巴爾扎克的措辭下說過哪種方言,取決于有人在一篇文章里告訴我們“你們代表著梯子”(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取決于今天你在談到自己時,決定說“你”還是說“我”。你自己的詞語,你的恐懼,你不被說出的全部,都是一副寫作的指紋——哪怕你不是一個寫作者。時時刻刻,一個真實的詞語與一份真實的記憶之間的爭斗,造就一些事情得以在語言中最終被表述出來的機會。基本上,這是寫作者所真正干的,而不是人們以為他在干的事情。今天你的一個詞語被說出后能否被聽見,明天你的表述里的一個構成部分能否表達出它的意思,是由整體語言被忽略,被轉述,被閱讀,被取舍的歷史決定的,如果我們“假定”亡者活著,那么就該惦記自己的歷史。讀一讀這首長詩,“趁其尚未器皿和溶解”。
編輯/張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