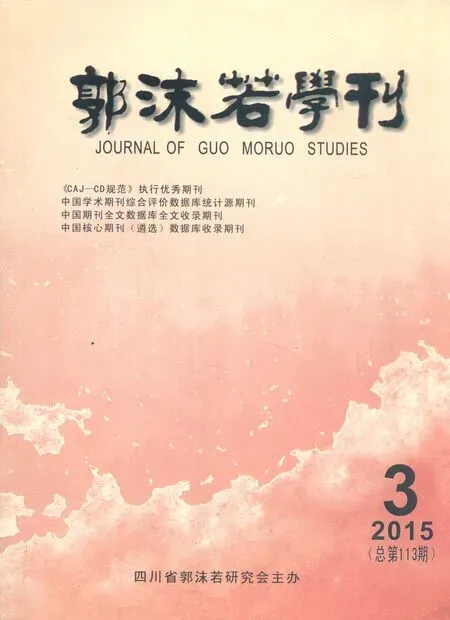郭沫若《戰聲集》中“們”之意象考釋
逯艷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山東濟南 250014)
郭沫若《戰聲集》中“們”之意象考釋
逯艷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山東濟南 250014)
《戰聲集》作為郭沫若抗戰初期的詩集,出版于《恢復》之后、《蜩塘集》之前,詩集雖然只收錄了二十一首詩歌,但其潛在的文化價值卻相當豐富,而學界對此關注不足。《戰聲集》開篇詩作《們》中的“們”意象,不僅串聯起整個詩集,同時還在郭沫若后續詩集中頻繁出現。借助“們”這個意象,郭沫若從《戰聲集》開始的“大眾化”詩歌創作理念逐漸脈絡清晰。為了實現詩歌的“大眾化”,郭沫若在《戰聲集》中采用智性鼓舞與感性動員相結合的策略,在實現“小我”向“大我”自覺轉變的同時指向無產階級的“烏托邦”,顯露出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和熱望。由此,郭沫若抗戰期間為了文藝“大眾化”降格詩美表象背后潛藏的深意便獲得一種解釋的可能。
郭沫若;《戰聲集》“;們”;大眾化“;烏托邦”
“詩集《戰聲》由戰時出版社出版,收詩二十首,附《歸國雜詠》手跡。”“《戰聲集》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作品,一九三八年一月,作為《戰時小叢書》之三,由廣州戰時出版社出版發行。”“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海益群出版社出版《蜩塘集》(附《戰聲集》)。”1957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二卷完整收錄了《戰聲集》,而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中的《戰聲集》就據此編入而成。
《戰聲集》最初作為《戰時小叢書》之三于1938年出版發行,收錄《們》、《詩歌國防》、《中國婦女抗戰歌》、《歸國雜吟》等二十一首詩作。《戰時小叢書》是“抗戰期間北新書局編輯出版的叢書,共四十四種,所收文章包括田漢等《八百孤軍》、阿英等《鐵蹄下的平津》、巴金等《戰時小說選》,郭沫若等《毀滅的中國》等。”學界曾據此從抗戰背景入手研究郭沫若此時詩歌創作風格的轉變,但其研究重點往往停留在郭沫若詩歌審美品格層面,而這也相應遮蔽了《戰聲集》的深層文化指向。
一、從《們》看《戰聲集》之前后
《們》是《戰聲集》的開篇之作,是整本詩集中感情最激昂、最豐沛、最有力的一首。詩作中的“們”被“你”指代,通篇使用“我”對“們”(即“你”)傾訴表白的口吻:
們喲,我親愛的們!
你是何等堅實的集體力量的象征,……
你今天已有一套西式的新裝,
這新裝于你真是百波羅地合身。
哦!
Mn!
Mn!
Mn!
Mn!
你可不是Marx和Lenin的合體?
你可不是Michelangelo與Beethoven的和親?
你是“阿爾法”和“哦美伽”,
你是序言與結論。
你在感性上的荷電,智性上的射能,
是多么豐富而有力的喲,
……
我們,咱們兄弟們,同志們,年輕的朋友們……
我便勇氣百倍,筆陣可以橫掃千人。
詩作《們》中的“們”作為“集體力量的象征”,指向“豐富而有力”的“我們”、“咱們”,即“兄弟們”“、同志們”、“朋友們”,而這種“們”性質的群體意象在《戰聲集》中屢見不鮮。《戰聲集》中除了《歸國雜感》、《給彭澎》和《“鐵的處女”》之外,剩下的十八首詩作都出現了“們”——《國防詩歌》、《前奏曲》、《紀念高爾基》、《民族再生的喜袍》、《戰聲》、《血肉的長城》、《只是靠著實驗》、《相見不遠》、《所應當關心的》、《中國婦女抗敵歌》、《人類進化的驛程》和《題廖仲愷先生遺容》中的“我們”,《給C.F.——“豕蹄”獻詩》和《唯最怯懦者為最殘忍》中的“他們”,《抗戰頌》中的“同胞們”以及《瘋狗禮贊》中的“它們”。這種集中表現群體意象的現象在《戰聲集》之前是否已經存在呢?
距離《戰聲集》最近的詩集《前茅》和《恢復》均出版于1928年,從時代背景和詩歌創作時間看,《恢復》是最接近《戰聲》的詩集。在《恢復》中的二十四首詩作均作于1928年,然而這二十四首詩的內容指向并不統一,即不但有書寫家庭和感情方面的《歸來》、《得到了安息》和《歇司迭里》,還有懷念故鄉和童年時光的《夢醒》、《峨眉山上的白雪》和《巫峽的回憶》。在這兩類較為個人化和私語性的詩作中,郭沫若更多采用第一人稱“我”,偶爾用第三人稱“她”,幾乎不使用人稱復數代詞。然而,《恢復》中還有一類詩作反映了大革命失敗后的階級斗爭和社會現實,比如《述懷》、《詩的宣言》、《我想起了陳涉吳廣》、《血的幻影》、《如火如荼的恐怖》、《傳聞》、《戰取》等。在這類詩作中,郭沫若也使用了表示復數的“們”,比如:
要殺你們就盡管殺罷!
你們殺了一個要增加百個,
我們身上都有孫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變成無數個新我。
我們昨日不是還駕御著一朵紅云,
為什么要讓它化成一片血雨飛散?
我們便從那高不可測的火星天里,
墮落到這深不可測的黑暗之淵。
權且不論《恢復》集詩作中的感情走向和“我們”、“你們”所指代的內容是否與《戰聲集》一致,《恢復》中群體性指向的“們”單從數量上是遠少于《戰聲集》。那么,繼《戰聲集》十年后出版的詩集《蜩塘集》又有什么變化呢?
《蜩塘集》收錄了郭沫若1939年至1947年之間的詩作,由上海群益出版社于1948年出版發行,1957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時增刪若干首,1982年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按照《沫若文集》第二卷編入。在《蜩塘集》四十七首詩歌中,除《蝶戀花》、《滿江紅》、《水龍吟》、《燭影搖紅》、《詠史》、《松崖山市》、《題〈南天竹〉》和《金環吟》等二十首舊體詩之外,剩下的二十七首新體詩中只有《和平之光——羅曼·羅蘭挽歌》、《斷想四章》和《中國人的母親》三首使用了單數人稱代詞“我”或“你”,所以《蜩塘集》中“們”出現的頻率遠超過《戰聲集》。
從1928年出版的詩集《恢復》到1948年出版的《蜩塘集》,1938年出版的《戰聲集》恰處在承上啟下的時間節點上。“們”作為一個獨特的意向,并非《戰聲集》獨有,但從《戰聲集》起“們”卻成為一個常見的意象。為何如此?“們”難道只是表示復數的人稱代詞嗎?《戰聲集》之前之后的詩集出現的“們”又有什么不同指向呢?《們》中郭沫若說:“我和你相熟了四十多年,真正的相識才開始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的今天。”這里“真正的相識”又指什么呢?
二“、抗戰所必需的是大眾的動員”
《戰聲集》中《們》點到“一九三六年”和“九·一八”,這在《給彭澎》和《相見不遠》中都再次出現。眾所周知,日本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攻占我國東北,在“‘九·一八’已經滿六周年”的1937年“,我們要把這血的記憶重溫一遍”,而“今年的重憶卻與往年不同,因為是已經發動全面抗戰”,即“今年為‘九·一八’雪恥的全面抗戰已經開始”——“真實的全面抗戰應該是國家社會內的一切設施的戰時機構化”,來“完成我們這次神圣的全面的立體戰爭”,這種“立體戰爭”需要把全國的力量集中起來“,全國的學術、產業、政治、經濟、教育等,在平時都要有充分的素養,而且是有系統有計劃的素養”。所以,在全面抗戰的時代洪流中,郭沫若在《們》中說:“我和你相熟了四十多年,真正的相識才開始在一九三六年‘九·一八’的今天。”這里的“真正的相識”暗含了郭沫若對“們”的新認識,也就是說,“們”在《戰聲集》指代的對象已經與詩集《恢復》不同。《們》中的“們“”今天已有一套西式的新裝,這新裝于你真是百波羅地合身。”這里的“百波羅”是英文popular的音譯,意為“大眾化的”。由此,郭沫若《戰聲集》中的“們”指代的是大眾。
然而“,大眾”同樣是一個內涵模糊的復數名詞,指向并不具體明晰,所以郭沫若在《戰聲集》中給出了這些線索:
你這是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心聲,
是一九三六年的正確的指令。
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生命,
是國亡與忘,國存與存。
同胞們,我們放聲高呼:
高呼我們中華民族的再生,
高呼我們民族戰士的英武。
愛國是國民人人應所有的責任,
人人都應該竭盡自己的精誠,
更何況國家臨到了危急存亡時分。
早在1936年春,郭沫若曾指出“國防文學”用“‘國防’二字概括文藝,恐怕不妥”,因為“國是蔣介石在統治著”,而在日后閱讀《八一宣言》時“經過幾天的思考,體會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矛盾,‘國’是被帝國主義欺侮、侵略的‘國’。”這才接受了“國防文學”口號的合理性。以上詩文中出現的“四萬萬五千萬人”、“國”、“同胞們”“、民族”等代表的“大眾”已經升格到民族的維度,指向與日本這個侵略國相抗戰的整個中國的民眾。
既然這是“民族危急存亡時分”,那么“一切文化活動都應該集中于抗戰有益這一焦點,必須充分大眾化。”也就是說“,中國目前急需的是政治性、煽動性的東西,目的在于發動民眾。”既然“抗戰所必需的是大眾的動員,在動員大眾上用不著有好高深的理論,用不著好卓越的藝術——否,理論愈高深,藝術愈卓越。反而越和大眾絕緣,而減殺抗敵的動力。”同樣的觀點在《抗戰以來文藝的展望》中再次出現過:“應吸盡文人的潔癖,盡量地大眾化。”
在這種理念指導下,郭沫若透過《戰聲集》中《詩歌國防》一詩指出“:詩歌本來是藝術的精華,它有音樂的渾含,造形美術的刻畫,任何藝術的成分……節奏的成分歸根只有兩樣,或是先揚后抑,或是先抑而后揚,前者使人消沉,后者使人激昂。”然而,此時“我們的民族需要的是覺醒而不是睡眠,催眠歌的音調應該暫時放在一邊。”所以“,我們要鼓動起民族解放的怒潮,我們要吹奏起鏟除漢奸的軍號,我們要把全民喚到國防前線把侵略者打倒。”這也就是說,郭沫若認為只要詩歌通過“先抑后揚”就可以發揮“使人激昂”的功效,從而能“把全民喚到國防前線把侵略者打倒”。由此,《戰聲集》中詩作都具有一種全民抗戰總動員的情感基調,注重了詩歌的通俗性和節奏性。比如《前奏曲》一詩:
全民抗戰的炮聲響了,
我們要放聲高歌,
我們的歌聲要高過
敵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后的勝利是屬于我們,
我們再沒有顧慮、逡巡,
要在飛機炸彈下
爭取民族獨立的光榮。
全民抗戰的炮聲響了,
我們要放聲高歌,
我們的歌聲要高過
敵人射出的高射炮。
這首詩共三節,每節四行,主要押“e”韻,整首歌簡單明了,號召全民在“飛機炸彈”下“爭取民族獨立的光榮”,氣勢雄渾,情感昂揚。其中第一節和第三節完全一致,讀起來頗像歌曲,易記好懂,十分符合抗戰時期文化水平不高的民眾和軍士所接受。這種性質的詩作還有《抗戰頌》、《血肉的長城》和《民族再生的喜袍》等。然而,除了這種從大眾層面對全民抗戰的智性鼓舞之外,《戰聲集》還潛藏著郭沫若另外一種動員策略,而這就要從《歸國雜吟》說起。
三、《歸國雜吟》的感召策略
“臨到國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時候,不幸我已被帝國主義者所拘留起來了。不過我絕不怕死辱及國家,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唯有以鐵血來對付他。我們的物質上犧牲當然很大,不過我們有的是人,我們可以重新建構起來的。精神的勝利可說是絕對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國的同胞們!”這是郭沫若1937年7月上旬,與金祖同談及“七七事變”后下決心歸赴國難之際,為躲避日本當局的迫害,抱著赴死的決心寫的《遺言》——“希望當自己萬一遭到不測”,金祖同“能帶回國內發表”。同時,郭沫若聯系金祖同購買回國船票時,賦詩一首表達自己志向,而這首詩就是《歸國雜吟》之一:
廿四傳花信,有鳥志喬遷。
緩急勞斟酌,安危費斡旋。
托身期泰岱,翹首望饒天。
此意輕鷹鶚,群雛劇可憐。
《歸國雜吟》是《戰聲集》中唯一一組舊體詩,作于1937年7月14日至10月10日之間,是郭沫若拋妻別子孑身一人“歸國前后隨興感奮”而作。整組詩作充滿高昂的戰斗情緒,抒發放棄“小我”家庭為“大我”事業的激越情懷。所以,不管是“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情”中暗含的與家人分離的隱忍和不舍,還是“四十六歲余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中流露的為抗戰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決心和悲壯,抑或“清晨我自向天祝:成得炮灰恨始輕”中顯示的視死如歸的肝膽和豪邁,這些情緒與《戰聲集》中其他詩作相比,使人更容易從情感層面受到抗戰的感召。
盡管《歸國雜吟》是郭沫若在《戰聲集》中唯一流露“小我”情感的詩組,但是這類感性話語卻不僅僅只是郭沫若私人情感的獨語。通過對照郭沫若《歸國雜吟》詩組創作時間前后,即1937年7月14日至10月10日之前后,又會有什么發現呢?這又要重新回到《們》這首詩上。
在《們》中,郭沫若在提到“們”這個意象時說:“我們,咱們弟兄們,同志們,年輕的朋友們……”,從這個排列順序看,“年輕的朋友們”作為“們”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能歸并到“弟兄們”、“同志們”之列,是“我們”的特殊組成群體。聯系1936年11月7日,郭沫若應邀前往明治大學所發表的《青年與文化》演講一文,他對青年人這一群體十分看重“:文化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最后最高的階段而又有發展向更高一層階級的那種努力的表現,而世界所有的一切文化,都是青年人創造出來的。”
既然青年們創造了“世界所有的一切文化”,而“在目前我們中日兩國的戰爭,不正是兩個陣營的短兵相接嗎?抗戰可以說是理性與獸性之戰,是進化與退化之戰,是文化與非文化之戰。”那么,對青年們進行抗戰動員的意義特殊而深遠。然而,“年輕的朋友們”畢竟不同于“弟兄們”和“同志們”,所以不能僅靠諸如“我們的民主是眾志成城,我們的將士是一德一心,這民意,這士氣,是我們的劍和盾,這為敵人的飛機大炮所炸毀不盡。”這種外在呼號吶喊式的動員形式,同時這也是為什么郭沫若會在1936年9月5日《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中呼吁:“把青年的公平,勇敢,犀利,敏捷,明朗,熱誠,好群等種種積極的美德發揮出來。”到了1937年8月11日,郭沫若在南市民眾教育館為百名文學青年演講時,發出“我和你們一起,上前線去,走向民族解放的戰場,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神圣的抗戰,獻給親愛的祖國!”的動員聲音時,將自己流亡日本的經歷敘述出來,并表示自己“在外流亡十年期間,朝夕都在思念親愛的母親,終于冒死回到祖國的懷抱”。同類情況早在1937年8月2日,郭沫若出席中國文藝協會上海協會和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為其舉行的宴會致詞中——“此次別婦拋兒專程返國,系下絕大決心。蓋國勢危殆至此,攝全民族一致精誠團結、對外抗戰外,實無他道,沫若為赴國難而來,當為祖國而犧牲,謹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這里的七律詩就是1937年7月24日用魯迅韻所作的《歸國雜吟》之二。
至此,從這一層面上說,郭沫若的《歸國雜吟》中的確飽含著“小我”的情感因素,就像他在1937年11月20日詩作《遙寄安娜》中所說的:“雖得一身離虎穴,奈何六口委驪淵。兩全家國殊難事,此恨將教萬世綿。”但這種“小我”情感卻也可以從“大我”犧牲精神的情感感召層面,被當成抗戰感性動員的一種策略。
時至1937年11月30日,郭沫若為《沫若抗戰文存》作序時指出,雖然文存中十五篇短文“都是在抗戰中熱情奔放之下,匆匆寫就的”,但是“有一點卻可供讀者的借鑒,那便是抗戰的決心。”而郭沫若所謂“抗戰的決心”又是一種什么決心呢?
四“、普羅列塔的詩的殿堂將由你的手中建起”
《戰聲集》中有一首詩題為《給C.F.——“豕蹄”獻詩》,最初發表在郭沫若歷史題材小說集《豕蹄》上,這本小說集于1936年10月由上海不二書店出版。詩作全文如下:
這半打豕蹄
獻給一匹螞蟻。
在好些勇士
正熱心地
吶喊而又搖旗,
把他們自己
塑成雪羅漢的
春季。
那匹螞蟻,
和著一大群螞蟻,
在綿邈的沙漠
無聲無息
砌疊
Aipotu。
詩作最后的“Aipotu”是英文Utopia的倒寫,意為“烏托邦”,指空想中的理想的社會組織。郭沫若在1924年8月9日曾給成仿吾寫過題為《孤鴻》的一封信,信中指出“烏托邦”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因為“甚么人都得隨其性之所近以發展其才能,甚么人都得以獻身于真理以圖有所貢獻,甚么人都得以解脫,甚么人都得以涅槃。”然而“,這種世界是一個夢想者的烏托邦嗎?是一個唯美主義者的象牙宮殿嗎?不是!不是!我現在相信著:它的確是可以實現在我們的地上的!”可是“,烏托邦”的理想世界又該如何實現呢?
《戰聲集》中有一首詩題為《給彭澎》,詩中所云“普羅列塔的詩的殿堂將由你的手中建起”,其中的“普羅列塔”是英文Proletariat的音譯,意為“無產階級”。然而,這種階級意識在《戰聲集》之前的《恢復》集中已經出現:
我是詩,這便是我的宣言,
我的階級是屬于無產。
我們還有五百萬的產業工人,
他們會給我們以戰斗的方法,利炮,飛槍。
在工人領導之下的農民暴動喲,朋友,
這是我們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他們應該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和親,
他們應該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盟。
……
他們有三萬二千萬以上的貧苦農夫,
他們有五百萬眾的新興的產業工人。
詩中的“工人”和“農夫”代表的“們”指向“無產階級”,是“大眾”的構成要素。正如郭沫若在《革命與文藝》中所言“:一個階級當然有一個階級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那一個階級說話。假如你是站在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反對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贊成革命……時代所要求的文學史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中國的要求已經和世界的要求一致。”郭沫若既然是站在“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陣營,那么他替被“壓迫階級”說這樣的話:“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旋渦中去。”這種“大眾化”的文藝理念,正是郭沫若在《普羅文藝的大眾化》中的觀點“:大眾化……正是無產文藝目前所應走的一個階段,一切創作都應該以能影響大眾為前提。”
然而,又該如何沿著“無產階級”的方向“打開民眾解放之門”呢?在《戰聲集》中還有一類悼念性質的緬懷詩,比如《悼聶耳》、《紀念高爾基》和《題廖仲愷先生遺容》等。郭沫若通過這類詩作抒發一己對故人的私人情感之外,還都將這些故人定位在一個承前啟后的坐標系中,而這種承接又與“們”代表的大眾不無關聯:
大眾都愛你的新聲,
大眾正賴你去喚醒。
……
聶耳啊我們的樂手,
你永遠在大眾中高奏。
我們是以文字為鐵槌,以語言為鐮刀,
我們應該學習著高爾基,繼承著高爾基,
用我們的血、力、生命,來繼續鑄造。
嗚呼先生,你是忠于革命者的典型,
我們要追蹤你的血跡前仆而后起。
透過這些詩句,郭沫若將這些已故的文化名人放置在開放式的紀念平臺上,認為正是“同一是民眾的天才,讓我輩在天涯同吊”,所以紀念他們的意義就不囿于“小我”的情感場域,而是要在“們”的深廣層面上做大眾式的精神普及。所以,如何紀念聶耳——“我們在戰取著明天,作為你音樂的報酬!”;如何紀念高爾基——“把高爾基六十八年的工程承繼起來,這才是紀念我們巨人的唯一的正道。”;如何紀念廖仲愷——“聯俄,容共,扶助農工,這都是中國革命并世界革命的根底……我們要追蹤你的血跡前仆而后起。”而之所要進行大眾的精神普及,是為了實現早日“烏托邦”——“這種時代的到來,這種社會的成立,在我們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見,使我們的后代得以早日解除物質生活的束縛而得遂其個性的自由完全的發展。”
五、余論
郭沫若曾在《新文藝的使命》中說的“:抗戰初期,一般的作家們受著戰爭的強烈刺激,都顯示出異常的激越,而較少平穩的靜觀。因而,初期的戰爭文藝在內容上大抵是直觀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動的……這責任不能全怪作家,因為一般的讀者和工作者也耐不得紆緩。”也就是說,由于抗戰洪流的沖擊,作家在“異常的激越”的情緒下進行文藝創作,勢必會因缺失“平穩的靜觀”弱化創作的審美品格,從而匯流到“耐不住紆緩”的集體無意識的河道。對郭沫若而言,這種降格審美品質的態度在《〈鳳凰〉序》中就有體現:“我要坦白地說一句話,自從《女神》以后,我已經不再是‘詩人’了……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有些人是特別的喜歡,但我始終是感覺著只有在最高潮時候的生命感是最夠味的。……我實在不大喜歡這個‘詩人’的名號。”不喜歡“詩人”名號的觀點在1936年9月4日《我的作詩的經過》一文中早有痕跡“:我對于詩仍然沒有斷念的,但我并不像一般的詩人一樣,一定要存心去‘做’……我高興做個‘標語人’‘,口號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詩人’。”
既然郭沫若自己對“詩人”有這種理解,也表示從《女神》集之后自己的詩作“不夠味”,那何以又會發出這種心聲——“我自己的本心在期待著:總有一天詩的發作又會來襲擊我,我又要如冷靜了的火山重新爆發起來。那時候我要以英雄的格調來寫英雄的行為。”所以,郭沫若從《戰聲集》之后的詩歌創作采取降格詩美的處理策略,又不能被簡單認定成“異常的激越”的沖動之舉。從這一層面上說,郭沫若建國后詩歌審美水平嚴重低下的現象并不是“建國后”的突變,透過《戰聲集》以及他在抗戰初期的“大眾化”理念,郭沫若建國后詩歌審美缺失又能從一定程度上找到接續的節點。然而,當我們看到郭沫若弱化甚至犧牲詩歌審美品質的降格現象時,也不能忽視其中被遮蔽的深層意義。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個力驅使郭沫若降格詩美,那必然會有一個反作用力讓他寧愿犧牲詩美,而《戰聲集》中的“們”意象便是尋找并揭示這種反作用力的一次有益嘗試。
(責任編輯:王錦厚)
注釋:
①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1892-1978)》(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頁。
②《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卷說明部分,第1頁。
③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53頁。
④《沫若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編寫組,萬仁元方慶秋王奇生編:《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頁。
⑥《們》作于1936年9月18日,載1936年10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號。
⑦《如火如荼的恐怖》作于1928年1月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頁。
⑧《血的幻影》作于1928年1月10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07頁。
⑨《們》作于1936年9月18日,載1936年10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號。
⑩《相見不遠》作于1937年9月15日,載1937年9月18日《戰線》第二期。
?《相見不遠》作于1937年9月15日,載1937年9月18日《戰線》第二期。
?《相見不遠》作于1937年9月15日,載1937年9月18日《戰線》第二期。
?《九一八的國際紀念化》作于1937年9月18日,載1937年9月18日上海《救亡日報》。
?《所應當關心的》作于1937年9月1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頁。
?《全面抗戰的再認識》作于1937年9月15日,載于1937年11月上海《抗戰半月刊》第三期。
?《們》作于1936年9月18日,載1936年10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號。
?《們》作于1936年9月18日,載1936年10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號。
?《給彭澎》作為1936年3月9日,載1936年6月15日《質文》雜志第一卷第五六合刊。
?《民族再生的喜炮》作于1937年8月20日,最初題為《民族復興的喜炮》,此處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頁。
?《抗戰頌》作于1937年8月21日,載1937年8月19日《抗戰》第一號。
?《血肉的長城》作于1937年8月22日,載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報》。
?林林:《這是黨喇叭的精神——憶郭沫若同志》,《悼念郭老》,三聯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頁。
?林林:《這是黨喇叭的精神——憶郭沫若同志》,《悼念郭老》,三聯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頁。
?林林:《這是黨喇叭的精神——憶郭沫若同志》,《悼念郭老》,三聯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頁。
?《抗戰與文化》作于1938年1月18日,載1938年6月20日《自由中國》月刊第三期。
?載1937年8月10日《立報》。
?《抗戰與文化》作于1938年1月18日,載1938年6月20日《自由中國》月刊第三期。
?《抗戰以來文藝的展望》作于1938年5月8日,載1938年5月8日《自由中國》月刊第二期。
?《詩歌國防》作于1936年11月11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頁。
?《詩歌國防》作于1936年11月11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頁。
?《詩歌國防》作于1936年11月11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頁。
?《前奏曲》作于1937年8月,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頁。
?殷塵:《郭沫若歸國秘記》,上海言行出版社1945年版,第19-21頁。
?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1892-1978)》(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2頁。
?《歸國雜感》之一作于1937年7月14日,原題為《郭沫若題詩》,載1937年8月4日《大晚報》。
?《歸國雜吟》分別作于1937年7月14日、7月24日、7月27日、8月7日、8月30日、9月8日和10月10日,出自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1892-1978)》(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2-362頁。
?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頁。
?《歸國雜吟》之二作于1937年7月24日,原題為《歸國志感》,載1937年8月7日《新民報·百花潭》。
?《歸國雜吟》之六作于1937年9月8日,載1937年9月13日《救亡日報》中《前線歸來》一文。
?《歸國雜吟》之七作于1937年10月10日,原題《郭沫若先生近作》,載1937年10月10日《立報》副刊《言林》,是郭沫若為《言林》的題詞。
?《青年與文化》,載1937年2月10日《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
?《理性與獸性之戰》作于1937年8月25日,載1937年9月1日《文化戰線》旬刊創刊號。
?《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作于1936年9月4日,載1936年9月5日《文學大眾》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載1982年11月26日上海《青年報》。
?龔濟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1892-1978)》(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頁。
?載1937年8月3日《大公報》。
?《遙寄安娜》作于1937年11月20日,載1938年5月10日《雜志》月刊創刊號。
?《<沫若抗戰文存>小序》,出自《沫若抗戰文存》,上海明明書局1938年版。
?《給C.F.——“豕蹄”獻詩》原題《獻詩給——C.F.——》,作于1936年5月23日,最初載于郭沫若小說集《豕蹄》,此處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頁。
?《孤鴻》作于1924年8月9日,載1926年4月《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51)《孤鴻》作于1924年8月9日,載1926年4月《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52)《孤鴻》作于1924年8月9日,載1926年4月《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53)《給彭澎》作為1936年3月9日,載1936年6月15日《質文》雜志第一卷第五六合刊。
(54)《詩的宣言》作于1928年1月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頁。
(55)《詩的宣言》作于1928年1月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80頁。
(56)《黃河與揚子江對話》作于1928年1月7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頁。
(57)《革命與文學》作于1926年4月13日,載1926年5月16日《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58)《革命與文學》作于1926年4月13日,載1926年5月16日《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59)《普羅文藝的大眾化》作于1930年1月12日,署名麥克昂,載1930年3月《藝術月刊》創刊號。
(60)《人類進化的驛程》作于1937年10月5日,載1937年10月10日《救亡日報》。
(61)《悼聶耳》作于1935年9月18日,載1935年10月10日《詩歌》第一卷第四期中的《聶耳紀念特輯》。
(62)《紀念高爾基》作于1936年6月22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頁。
(63)《題廖仲愷先生遺容》是郭沫若為廖仲愷的題詞,最初形式是手跡,用《郭沫若題詞》為題載于1937年8月20日《立報》副刊《言林》,此處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頁。
(64)《紀念高爾基》作于1936年6月22日,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頁。
(65)《題廖仲愷先生遺容》是郭沫若為廖仲愷的題詞,最初形式是手跡,用《郭沫若題詞》為題載于1937年8月20日《立報》副刊《言林》,此處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頁。
(66)《孤鴻》作于1924年8月9日,載1926年4月《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67)《新文藝的使命》作于1943年3月10日,載1943年3月27日《新華日報》。
(68)《序我的詩》原題為《<鳳凰>序》,作于1944年1月5日,最初載于1944年6月重慶明天出版社版《鳳凰》。此處出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08頁。
(69)《我的作詩的經過》作于1936年9月4日,載1936年11月10日《質文》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70)《我的作詩的經過》作于1936年9月4日,載1936年11月10日《質文》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I207.22
:A
:1003-7225(2015)03-0020-07
2015-07-22
逯艷,女,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