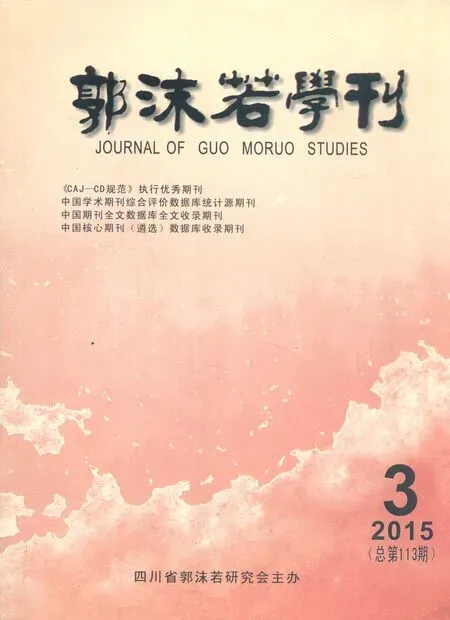郭沫若的“獻辭”與梁實秋的“感想”
王錦厚
(四川大學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郭沫若的“獻辭”與梁實秋的“感想”
王錦厚
(四川大學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新年伊始,報刊編者往往要約請有影響的名人撰寫一點獻辭之類的文字,談自己對過往一年的觀感,或個人的境遇;新的一年的展望或個人的打算,以啟示讀者,當然也含有祝賀之意。這里,有三篇內容不盡相同的文字,作者是我們極為熟悉的名人。一篇是郭沫若撰寫的《新年獻辭》,內容是這樣的:
新年獻辭
轉瞬便要到一九四三年了。
雖然在目前還在準備過冬,但已透感著新年的新氣。
一九四二年雖然同樣在烽火中過渡了來,過渡著在,而且還要過渡下去,但東西法西斯蒂的毒焰已不再有往年那樣猛烈了。
納粹在斯大林格勒又要舉行一次雪葬“,皇道”在太平洋上,正在舉行水葬。
一九四三年大概是和平破曉的一年罷。
我們高奏起文藝的軍號來賓寅這和平的曙光,但不可忘記:在目前還得開辟兩對第二戰場——
西歐一個,緬甸一個。
小說一個,批評一個。
詩歌和戲劇應該加緊戰斗下去,但小說和批評不可再冷落了。
這篇“獻辭”的手跡刊發于1943年1月15日桂林出版的《文學創作》一卷四期。后來分別收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三輯,《抗日戰爭時期桂林文藝史料選輯》。1944年1月1日桂林出版的《當代文藝》創刊號又刊發了他的“元旦獻辭”。如下:
轉瞬之間,民國也快三十三年了。在這一年,全世界或許是更加有變化之一年,歐洲戰場或許可能把納粹瓦解。東方戰場的前途還不能作出同樣樂觀的透視。但,戰場盡管怎樣變,為爭取民主主義的勝利這個目標是永遠也不會變的。法西斯的迷夢破滅了。在逐漸加強的晨曦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的字幕:“一個戰爭,一個世界,一個民主的文化。”
梁實秋所撰寫《一點感想》,全文如下:
《一點感想》
中國文人有“元旦試筆”之說,聽說美國人有“新年決議”之習。我今應征寫幾句新年感想,蓋亦未能免俗。天下大事,國家前途,以及有關大眾的事,凡非我所能把握或左右者,我皆不愿說,說亦無益。新年將到,看看日歷越來越薄,不能不有“鬢發催人驚歲月”之嘆,這時節心中確有一股與往常不同的感覺,說出來也未曾不可,事關一己,與人無涉。
我覺得:一生數十寒暑,能做些什么事?大部分時間及所做的事,都是受別人的支配。以過去而論,我所進的學校,我所讀的書,我所追從的教師,我所就的職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外界的勢力的支配,而不是我自由選擇的。受人支配并不一定就是吃虧,也許早年自己尚未成熟的時節,若自由起來,結果將不堪設想,更貽后悔。不過,一個人的生活勢不能長久受外界支配,自主自決的范圍總要越來越擴大才好。到了新年,特別感覺“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于自己未來若干年時間,不能不趕快設計。我這一生究竟要做些什么事?不能不預為考慮。做了這個,做不了那個,時間只有那么多。環境也許不容許我實現我的設計,但不可不設計,不可不盡力做去。若是失敗了呢,那就是失敗了。
兒時作文有一個題目“人貴立志說”,到現在才明白這題目怎樣解釋。人生最快樂的事,無過于“能做自己所愿做的事。”
這篇“感想”是作者應刊之約撰寫的新年獻辭。刊發于1944年1月號重慶出版的《時與潮文藝》的《時與潮增刊》3卷6期。
三篇文字充分應證了“文如其人”的真理。前兩篇著眼的是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闡述的是國際國內的形勢,指明的是文藝界努力的方向;后一篇著眼的是個人,闡述的是自己的經歷及追求。如果將兩人的文字放在1943年—1944年,抗戰由相持轉入反攻的大背景中加以透視,其立場、情懷、個性以及文字風格迥然相異,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了。文字雖短,然而,對研究兩人的生平,乃至當時的形勢,應該說都是值得注意的史料。特提供出來,供研究者們參考。
2015年5月
于成都川大花園寓所
(責任編輯:陳 俐)
2015-07-22
王錦厚,男,四川大學出版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