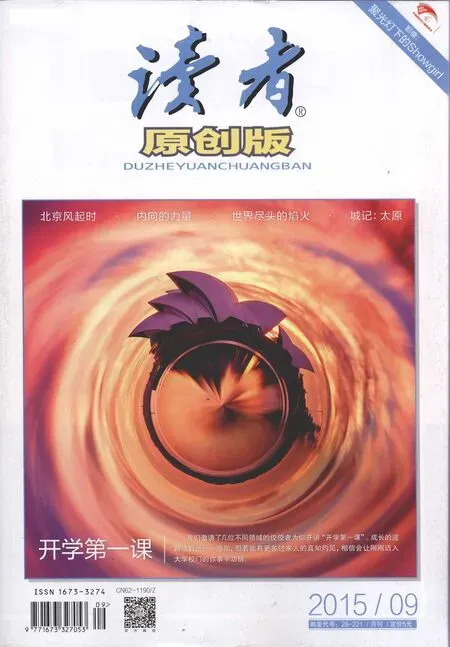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
文_ 韓 晗
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
文_ 韓 晗
茶 座
在一次面對大學生的講座上,一個女生告訴我,她想成為一名職業作家,希望我能給她一些建議和鼓勵。我問她是學什么專業的,她說自己學的是國際貿易。
臺下開始有噓聲,因為那時中國剛剛加入WTO,國際貿易是很好的專業,很多學生畢業之后直接和一些大公司簽約,可謂是供不應求。一般都是學中文、哲學的學生轉系去學國際貿易,居然還有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愿意做職業作家?
既然要我給建議,我就很坦然地告訴她:“你想做一名作家,這很好,但請不要把寫作當職業,否則你會很痛苦,甚至窮困。”
“怎么會?”這個女孩子質疑道,“那么多作家都拿著很高的稿酬。”
“全國的作家有很多,多到你想象不到,那些網絡寫手,也可以說是作家,但是單靠寫作就過上好日子的有幾個人?”
臺下鴉雀無聲。
講座結束之后,我在臺下與這位女生閑聊。我告訴她,國外知名的作家,很多都是律師、企業家、醫生、編輯、大學教授、工程師,而中國知名的作家,也大多是教授、官員、記者、編輯。
“韓老師,您是不是太‘勢利’了?”這個女孩子有股執拗勁兒,“如果我愿意固守清貧,或者說我家里很有錢,愿意讓我寫一輩子呢?”
“那你恐怕沒有東西可寫。”我只好實話實說,“創作的源泉是生活,為了寫作而寫作,你只能陷入惡性循環。”
看她有些困惑,我只好建議她讀一讀文學史,特別是野史。如果海明威不是水手,他可能寫出《老人與海》嗎?卡夫卡的律師生涯,讓他的小說在法律、人性的描寫上獨樹一幟。而余秋雨正是因為戲劇學教授的身份,才可以在散文中旁征博引,將戲劇理論與寫作理論相結合,創作出有懸念的散文。
這個女生沉默了,周圍旁聽我們對話的人,也都沉默了。
“寫作是一個虛構的過程,哪怕你寫的是散文。”我進一步補充,“但這種虛構是來自生活的,你如果只是一個單純的寫作者,那么你的生活會很貧乏,你的寫作也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她拿出自己的筆記本,讓我給她寫一句贈言。我想了想,寫下這么幾個字:“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
評 刊評 刊
看了“親愛的小孩”,就想起那些年我挨過的打。那時候,父母工作忙,壓力大,也沒有什么科學的育兒觀,對我的管教辦法只有一個字:打。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拆了手風琴,媽媽什么都沒說,拎起我一頓猛揍。現在父母幫我帶女兒,有一回說起那次挨打,媽媽也奇怪 :“要是現在,小孩子拆了手風琴,說明孩子有探索精神,干嗎要打呢?”但每當媽媽對我不滿意,總會來上一句:“知道你現在為啥不夠好嗎?那是因為后來我打你打得少了!”她不知道,我成年之后所有的不自信,都源于那些年被打擊的自尊和被忽視的小情緒。(特別報道“親愛的小孩”)
—大雨小雨嘩啦啦
充斥我們的電腦和手機的,都是各種美圖或搞笑圖,要么比生活美,要么解構生活的沉重,而馬宏杰是在呈現真實的生活,不美化,不虛構,一跟拍就是幾年,甚至幾十年,讓人在照片中感受時間的力量,看到時代的演變。希望能有更多這樣的紀實攝影師,記錄我們生活的時代。(《我的鏡頭從不說謊—專訪馬宏杰》)
—霉兔咻
很早之前就知道另維—NBA美女主播、作家、留學生……總之,就是我眼里的“人生贏家”。在她誠意滿滿的專欄中,我看到了一個勤奮、糾結、善于思考人生的姑娘。更沒想到的是,《社區學院》讓我看到一個曾經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另維,也讓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既然鳳毛麟角存在,為什么不能是我呢?”(《社區學院》)
—懷雨憨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