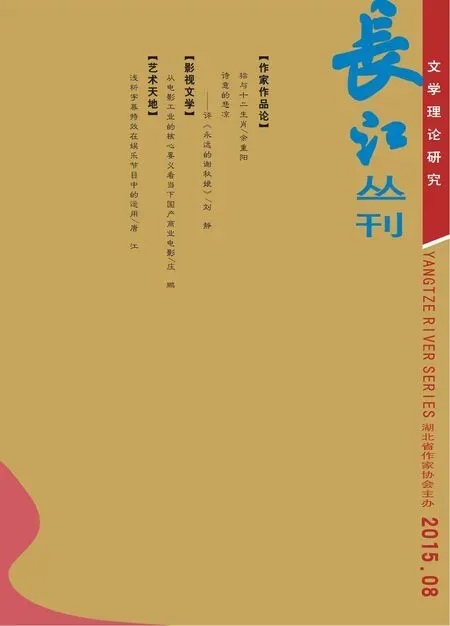淺析斯賓格勒與《西方的沒落》
陶力溶
(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長春 130000)
20世紀初,德國學者斯賓格勒發表了著作《西方的沒落》。該書以全新的視角解讀歷史,闡述了西方文化所面臨的危機,并試圖揭示危機所產生的根源,引起了西方文化界的強烈反應。在世界文化發展多元化的今天,以今人的視角對其問世的影響進行剖析,或許有一些新的認識。
一、關于“文化”與“文明”
斯賓格勒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演變應被稱為“歷史的世界”這個世界與“自然的世界”有著本質的不同,是一個有著自我規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當中“文化”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基本單位。
斯賓格勒花了巨幅筆墨來敘述文明和文化的差別。僅從他提出的觀點出發可以看出:文化的象征是人文精神,文明的自然科學,文化時期的文化更理想主義,文明時期的文化更物質、功利,藝術陷入形式的桎梏之中。文化的宿命是文明,而文明并將走向沒落。斯賓格勒所說的西方的沒落,并不是整個西方文化的沒落,因為他所說的西方文化只是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文化,而且這個階段的文明沒落以后在西方將會出現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出現預示著新文化形態的到來,這是一種有機論的世界觀。
按照自己的理論,斯賓格勒將以往的世界分為八個自成體系的文化,即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古希臘羅馬文化、伊斯蘭文化、墨西哥文化,還有就是西方文化。這八種文化在價值上都是等同的,他明確表示:“不承認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等占有任何優勢地位,他們都是動態存在的個別世界,從分量看來,它們在歷史的一般圖景中的地位和古典文化是一樣的。”
二、關于時間感
道格拉斯著寫的《西方世界的興起》是從經濟角度出發,將經濟學理論返回到歷史中用來解釋歷史演進的事實,為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角度。而《西方的沒落》則從時間感和類比方法來分析。以人對時間認識的發展為線索,來看西方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可以看出人們的需求,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對時間的要求越來越高。
并非所有的民族都不存在強烈的時間感,也不是所有歷史感的民族都是有時間感的。《西方的沒落》中提到,歐洲人與其他地方的人不同地方之一就是有歷史感,這一點使得歐洲人非常重視時間的流動。
中國擁有十分長久的歷史,卻沒有精準的計時器(沙漏之類的計時性能是在算不上精準),我想這其中原因大概是潛意識中對我們來說時間只是事件發生的副產品。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一些鄉村村民使用以記事記時的方式,會有“我在解放后3年出生”這樣的說法。用陰歷計時在當時也是少數的。也許就是因為西歐時間感的萌芽,使他們提早適應了工業時代緊迫的節奏。
三、悲觀主義的宿命論
斯賓格勒認為,時間與命運是可以互換的名詞,未來是可以預測的。歷史世界中每一種文化都有生長盛衰的周期性規律,這種周期性是不可逆轉的,是每一種文化的宿命,一種文化的生命運行周期不依賴于任何認為因素,而是一個命運注定的生命周期,這就是斯賓格勒闡釋的宿命,也是人類文化發展的趨向。
他認為每一種文化都要各自走完生命歷程:前文化階段、文化階段、文明階段。而文明階段就是每一種文化發展的最后階段。由此他得出西方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法蘭克王國的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第二階段是基督教文化;第三階段則是西方文化的衰落時期,而斯氏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方文化開始衰落的時期。
這種宿命論定義促使歐洲人對西方文化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進行重新定位并修改,不得不說是具有積極的警醒意義。但也可以看出來這并不是以客觀世界發展規律為標準的,而是帶有歷史的主觀性,也就是作者視覺上的主觀性,因而顯得這種悲觀宿命論有不科學、不準確的嫌疑,畢竟社會文化的興衰怎么會只以人的意志來決定,更不可能預先設定。盡管如此,斯賓格勒的思想對于今天的史學者們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寶貴財富,值得為之探索。
[1]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2]歷史與時間:斯賓格勒與<西方的沒落>[EB/OL].教育學刊.
[3]侯西安.斯賓格勒的觀念[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