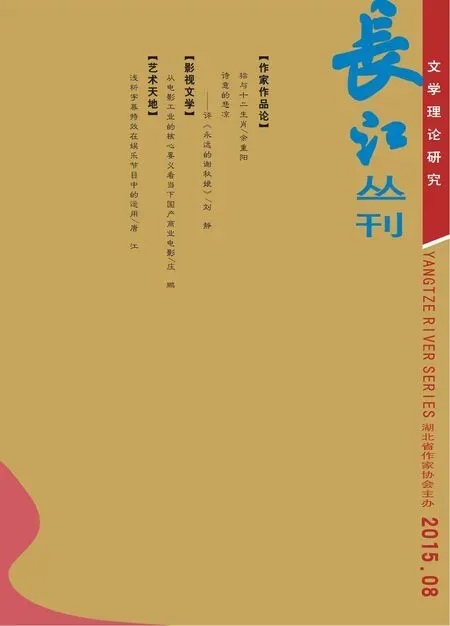建基于非歷史性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護
——再論柯亨的社會“物質性”與“社會性”相區分的理論基點
趙 璟
(河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鄭州 450052)
建基于非歷史性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護
——再論柯亨的社會“物質性”與“社會性”相區分的理論基點
趙 璟
(河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鄭州 450052)
柯亨在1978年發表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這本書中,詳細闡述了社會“物質性”與“社會性”的區分,并力圖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作辯護。本文主要闡述了柯亨是如何區分社會的“物質性”與“社會性”的,并試圖對這一區分進行利弊分析。
柯亨 社會的社會性 社會的物質性 歷史唯物主義
G·A·柯亨1941年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爾一個猶太工人的家庭,其父母都信奉共產主義。柯亨是英國倫敦大學的哲學教授,是英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他的許多著作都是圍繞歷史唯物主義展開的,在1978年發表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這本書,使他以“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的重要代表而一舉成名。
一、柯亨為什么要區分社會的“物質性”與“社會性”
首先,柯亨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一個最基本的區分是社會的“物質屬性”和“社會屬性”。《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這本書正是圍繞這一區分來寫的,“這使得作者能暢達貫通地討論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階級不平等的根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社會革命的意義以及共產主義的性質,等等。”[1]
其次,柯亨認為“物質性”與“社會性”的區分就是“內容”和“形式”的區分,這種區分有助于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有利于揭露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的物質過程。
此外,柯亨受到家庭環境和學校教育的影響,從小就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特殊的情懷。柯亨出生于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猶太人家庭,其父母積極的組織工人們反抗工頭和警察的壓迫。柯亨4歲時,被送入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猶太人創辦的學校里讀書。
最后,受到當時政治局勢的影響。1952年,受“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政府對柯亨所在的學校進行排查,外籍教師被驅逐或迫害。在這種情況下,柯亨積極采用分析哲學的方法,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的核心辯護。
二、柯亨怎樣區分社會的“物質性”與“社會性”
柯亨在書中,詳細的介紹社會的“物質性”與“社會性”,他認為這是理解馬克思歷史理論的鑰匙,并指出馬克思也作了和他一樣的區分。柯亨提到:“馬克思經常注意嚴格區分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經濟的或社會的特征”。[1]
(一)“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奴隸。紡紗機就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一樣……”[2]在這里,柯亨指出資本是關系不是物,黑人只有在奴隸社會這個特定的社會形態下,才具有“奴隸”的社會屬性。同樣,紡紗機只有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關系中,才具有“資本”這一社會屬性。
(二)“從社會角度來看,既沒有奴隸也沒有市民:兩者都是人〔這樣說是錯誤的〕。這樣他們就是在社會之外的。是一個奴隸或是一個市民,這是社會決定的,即人A和人B的關系決定的……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區別實際上只在于從社會的觀點來看。”[3]作者認為,馬克思是從兩個角度來分析的,一方面是“馬克思聯系到社會決定人A和人B的關系”[1],這是從社會角度看他是什么樣的人,即人A是奴隸就不是市民,人B是市民就不是奴隸;另一方面是從物質角度來分析的,即人A和人B都是人,此時物質的存在是獨立于社會形態的。
(三)“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表現在一物上,給此物一種特殊的社會的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所生產的各種生產資料之總和。”[4]柯亨認為不變資本是具有一定社會性質的物,生產資料不是資本,生產資料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即被社會某一部分人所獨占時,才能成為資本。
社會是一個客觀存在體,具有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柯亨指出:“社會的物質或內容是自然,其形式是社會形態。”[1]他認為物質屬性是一個物理存在物,而社會屬性,則是一個社會的標簽和資格。“物質描述抓住的是一個從屬于社會的自然”[1]。從柯亨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認為物質性是指事物對象的天然屬性。社會性是一事物處在某種社會關系中所具有的屬性,它是一種關系屬性。他指出:“這些界限的區分是根據社會的內容和形式之間的區分。人和生產力構成它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賦予內容社會形式。”[1]
此外,柯亨還介紹了社會的“物質性”與“社會性”兩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他認為任何一個事物都具有物質性和社會性,但是,“社會特性不可以從它們的物質特性推演出來,正像雕塑的造型不能從它的質料推演出來一樣。”[1]即“物質性”推演不出“社會性”,“社會性”是獨立于“物質性”的。另一方面,柯亨認為“物質性”是性質屬性,是與生俱來的。
那么如何將物質從社會狀況中劃分出來呢?柯亨指出:“一個描述是社會的,當且僅當它需要把人(指明或不指明)歸屬于相對于另一個人的權利或權力。”[1]從而,“他能夠這樣使用它,屬于物質狀況,而他是否有責任對某人這樣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則是社會狀況的事實。”[1]在這里,他把“社會性”歸結于一種實質的“權利或權力”。柯亨認為:“物質描述抓住的是一個從屬于社會的自然。”即我們可以將物質性從社會狀況中劃分出來,這樣描述是可行的。
三、對這種區分的學界評價
學者孟慶龍認為,柯亨對“物質性”和“社會性”的區分是值得肯定。“一方面,他促使人們重新重視馬克思的經典文本;另一方面,柯亨引薦了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即分析哲學的邏輯分析和概念分析方法,為馬克思主義研究開拓了一種新的研究路徑。”[5]
劉禹杰指出:“社會的“物質性”與“社會性”的劃分,使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有了進一步的了解。”[6]
此外,陳偉認為:“雙重屬性的區分具有革命性意義。首先,它有利于思維認識上的深化,使社會這一概念的內涵更加豐富,從而使我們可以更加有效地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其次,它有利于加深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再次,如柯亨強調的那樣,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也基本是運用了自然的和社會的之間的區分。”
柯亨在雙重屬性的區分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學者孟慶龍指出:“一方面,柯亨期望的“清楚明白”的目的不僅未能達成,反而使得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變得更為混亂;另一方面,由于柯亨固守形式的分析方法而否定真理的辯證法,從而使得他對這一理論的認識是極其膚淺的。”[5]
劉禹杰指出柯亨對社會從物質性和社會性來劃分的說法不夠嚴謹,應明確指出是對“社會中的物”或“物的社會”的劃分。此外,柯亨還論述了活勞動和死勞動的支配關系,劉禹杰提到:“從物質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和勞動方式都沒有改變,所以勞動者并不真正地從屬于資本。而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勞動者的勞動活動卻在為擴大資本服務,死勞動支配勞動。這就與柯亨闡述的生產力首要性命題相矛盾。”[6]
四、如何看待這種區分
(一)這一區分的積極意義
首先,這一區分是社會的形式和內容之間的區分,這有助于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有利于更加有效的分析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可以對資本自詡是創造物質財富不可替代的手段產生懷疑。”[1]
其次,從柯亨對“物質性”和“社會性”的區分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只有了解基本概念的含義,才能正確的分析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系。柯亨引薦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及其他學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再次,度是關節點范圍內的幅度,在這個范圍內,事物的質保持不變;突破這一關節點,事物的質就會發生變化。柯亨指出:“當在各種社會形態中被創造出來的物質總和超過了容納它的社會的時候,革命就要到來。內容突破了形式。”[1]這一觀點運用質量互變規律,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社會形態的更替。
(二)這一區分的問題所在
柯亨將“物質性”和“社會性”相對,而我們通常將“物質”與“精神”相對,“社會性”和“自然性”相對。他將“物質性”等同于“自然”,混淆了概念。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辯證統一的。人的自然屬性是社會屬性賴以生存的前提,而人的社會性制約著人的自然性,人的自然性受人的意識的指導,具有強烈的社會色彩。
除此之外,對于“物質性”與“社會性”的關系問題,柯亨認為二者是彼此對立,無法相融的,它們是社會生產過程的不同方面,內容和形式、物質和社會之間是沒有邏輯聯系的。那么,馬克思又是如何定義“物質性”的?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了正確地理解物質概念的方法和角度。他指出舊唯物主義把人當作認識對象,而不是改造對象;他強調實踐的意義,批判了舊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指出了舊唯物主義的缺陷是不了解實踐活動的意義。馬克思認為物質不僅有感性的自在存在,還包含實踐內涵。因此,要在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上來理解物質,物質世界是包含了人的主體性的物質世界,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結果。因此,物質具有社會性。可見,物質性和社會性是密不可分的,而不是柯亨所說的兩者是沒有必然聯系的。
總之,柯亨的社會“物質性”與“社會性”相區分的理論并力圖在馬克思思想的框架內重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這對恢復馬克思思想的本來面目,正確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但是,柯亨在論述社會的“物質性”與“社會性”時,夸大了兩者的對立性,沒看到兩者的聯系和相互作用。致使他未能真正把握唯物史觀是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規律這一真諦。這無疑對歷史唯物主義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因此,如何從整體上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實質從而更好地維護歷史唯物主義,還需要更加細致的研究。
[1]G·A·柯亨.岳長齡譯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2]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3]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孟慶龍.柯亨社會的“物質性”與“社會性”的區分理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J].社會科學,2011(1).
[6]劉禹杰.論柯亨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辯護之得失[D].長春:吉林大學,2013.
趙璟(1989—)女,漢族,河南南陽人,河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