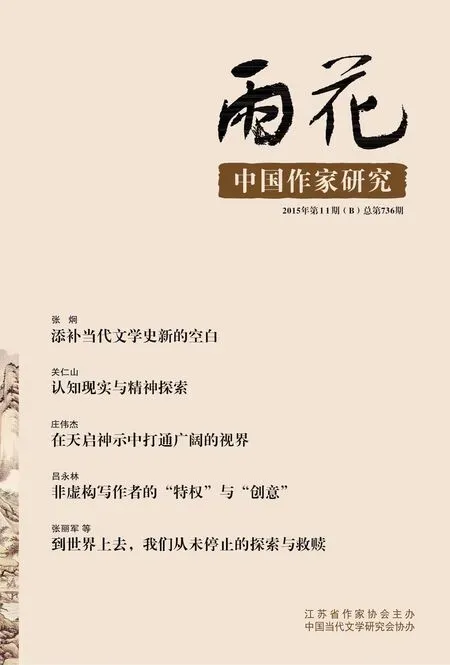認知現實與精神探索
——談長篇小說《日頭》的創作
■關仁山
認知現實與精神探索
——談長篇小說《日頭》的創作
■關仁山
對作家來說,存在的勇氣就是寫作的勇氣,我們首先要有面對現實寫作的勇氣。當下的現實,既復雜難辨,又變動不拘。直面這樣的現實,其實難度很大。難點在于對時代生活的認知上。如何深刻認知當今變動的現實與復雜的鄉土是橫亙在作家面前必須正視和思考的難題。現實有丑惡,但作家不能丑陋;人性有疾患,但作家內心不能陰暗,要有強大的愛心,要熱愛腳下的土地,熱愛土地上勞動的農民。因此,作家的內心要不斷調整,要有激濁揚清的勇氣,還要有化丑為美的能力。自己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還要從反思中給人民以情感溫暖和精神撫慰。這其實是精神層面上的雙向互動。作家所需要的這些精神力量,要經常補充,不斷更新,辦法就是要到時代的熱流、基層的民間和普通的大眾中吸取精神力量。這個時代可能存在不少問題,但向前行進,是主流,是大勢,作家應與自己所處時代肝膽相照。
就文本仔細一想,宏大敘事帶來厚重,同時也是笨拙的,如果作品藝術手法單一,全能全知的視角較為固定、重復,人物類型也相對單調,沒有從文化角度深挖其行為根源。只寫問題,這些問題隨著改革的進程解決了,小說還有讀的必要嗎?沒有必要讀的小說還有必要寫嗎?創作中,我常常懷疑自己的藝術能力,同時也懷疑小說。小說到底有沒有面對土地的能力?有沒有面對當今社會問題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實和問題本身,由政治話題轉化為文學的話題?“三農”的困局需要解開,我創作的困局也需要解開。我走訪中發現,農村的問題很多,如農業現代化、土地所有權、農產品價格、農村剩余勞力出路、貧富分化、城鎮化拆遷、農村社會保障、怎樣融入城鎮生活等等。農村走進了時代的漩渦。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農村非但不能跨入現代社會,甚至會出現混亂、停滯或倒退。農村問題急迫而嚴峻。鄉土敘事還處在摸索階段,怎樣才能找到適應新情況的新的寫作手法,讓我們困惑,我無法面對這樣巨大的農村變化。一個小村莊,有幾十億富翁,有中產,有一般貧困戶,還有很窮的農民。怎樣概括它?這是一個嚴峻而復雜的問題。仇視城市嗎?廉價謳歌鄉土嗎?展示貧苦困境嗎?整合破碎的記憶嗎?每一個單項都是片面的,應該理性看待今天鄉土的復雜性。土地流轉也好,城鎮化也罷,都需要時間來印證。這些流動的、新鮮的、不確定的因素,給我帶來創作的激情,以我們對農民和土地的深愛和憂思,描述這一歷史進程中艱難、奇妙和復雜的時代生活。
話題回到《日頭》這部小說上來,這部小說創作源起,要說到“天啟大鐘”,這部小說是由天啟大鐘而起的。我的故鄉稻地鎮有這樣一口大鐘,與北京懷柔紅螺寺的天啟大鐘是一對兒。由大鐘聯想到這部小說的十二律結構。我這人有個習慣,總是在小說開筆之前,把自己的構思講給朋友聽,在朋友那里獲得驗證,然后我才有寫作的信心。有一次,我瀏覽河北作家網,一位朋友給我留言:你的創作不錯了,但還有遺憾,不能回避今天殘酷的現實,才能寫出真正的好作品。這個留言給我觸動很深。過去歌頌土地多了一些,這一篇再也不能與農民的苦難擦肩而過了,要加強批判色彩。換句話說,就是讓自己這部作品能夠遵從內心,遵從藝術,勇于探險。寫農民的書,怎樣才能做得好?有人說,農村小說只有寫得不像農村小說了才有可能出現好小說。《日頭》跳出了農民種地的傳統模式,拋棄了原來用過的精神資源,帶著憂患意識去寫一種新的形態。農民的生活伴隨著苦難和眼淚,小說必然是沉重的。這類小說必須面對沉重的問題和嚴峻現實,所以說,作家必須是勇敢的。這對我是個嚴峻的考驗。我在寫提綱階段,不斷對自己說:前面有《天高地厚》和《麥河》,這是“農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書,一定要面對良心說真話。所以,在風格上就尖銳一些,大膽地探索一些問題,寫出時代的漩渦,寫出新農民的精神裂變。其實,小說解決不了所有的精神問題,但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態,代表時代的良心。我想以此引起社會的注意,如果真正為中國農民著想,就應該認真地去考慮解決這些問題。即使一時還不能做到位,也要將此作為長遠目標來努力。以此看來,我想借助金沐灶這個人物在思想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遠一些。不知讀者會不會滿意?
回想創作期間,我多次到農村搜集素材。寫作過程很痛苦,其間,確實出現過比較理想的寫作狀態。比如,故事的傳奇性,人攪著事,事推著人,農民在生活中探索性地往前走,這本身是故事,作品有了逼真的寫實,這是不夠的,作家要超越現實。顯然,這需要作家的想象力,將現實打碎再加以重塑。我想應該在隱喻和象征中建構傳奇。我想在故事和人物身上抹上一層傳奇色彩,讓他們部分地異于常人,異于常理。然后又在玄幻、詭秘和神奇中回歸常人,回歸常理。另外,我在這部小說中格外在乎故事,故事性、傳奇性、情感性的渲染使小說有效地避免了簡單化、概念化圖解現實的弊端。故事的背后有一個影子,時而在明亮中顯現,時而在黑暗中隱沒。
有的小說是讀味道,有的小說是讀故事。《日頭》故事性較強,講述了文革紅衛兵砸鐘傷人、焚燒魁星閣,以及后來大鐘埋入墓地被盜,城鎮化拆遷挖湖挪鐘事件,強拆中的自焚事件等一些傳奇事件。我想在隱喻和象征中建構傳奇,故事的傳奇性會給小說增加野逸風格,會淡化政治色彩,所以熱鬧的背后我還是想讓讀者讀故事背后的東西。真正有價值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背后的思想和文化含量。城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殖民,這一慘烈的過程,用孟繁華先生的話說,那是鄉村文明的崩潰。我們目睹了崩潰,還是要呼喚新的文明形態的建立。比如說,按佛家的因果關系來說,文革壓抑人性是因,改革開放中人性的解放就是果。而人性大解放中,人性在金錢面前的瘋狂,造成人格裂變的果。人格分裂的因,又造成如今國人精神困境的果。這些東西都與鄉村文明的崩潰相關。
必須埋下問題,浮起追問。我塑造的農民金沐灶是個民間思想者,借助他對這些問題進行追問,這樣方能帶領讀者思考。一幕幕活生生的事件促使金沐灶對“文革”后的日頭村生活產生了深刻真切的頓悟與認識。面對著自己心愛的火苗兒,金沐灶痛心疾首地說:“火苗兒,我對不起你。我不配提愛情。燒掉魁星閣、砸毀天啟大鐘的時候,日頭村人的心里是不是黑暗一片?是不是到處充滿仇恨?可是誰來化解仇恨?誰來拯救苦難?流血的悲劇還會在日頭村重演嗎?我以為沒有‘文革’,悲劇就不會重演了。然而,我錯了。事實遠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在資本時代里,你姐姐大妞留下的那只腳、披霞山鐵礦流血慘案、披霞山大火、汪老七的死、大拆遷中的強暴、失地農民的血淚,這都是悲劇啊……”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強調,金沐灶的這段話語,也是我們今天每一位善于思考的人的心中吶喊。《日頭》沒有對城鎮化引起的弊端過分情緒化地詛咒,而是通過金沐灶試圖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結合中,從“人心”的角度思考城鎮化的正確方向。從體制上看,我們目前的城鎮化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野蠻性。錯誤的政績觀與惡意資本的聯手,會傷害農民的,資本與權力對人性的扭曲和變異是觸目驚心的。這時候我想成為鄉村文明的審視者,特別是體現在土地屬性上的追問和審視。比《麥河》謳歌土地更進一步,土地屬于誰?這是個重要問題,我想在故事的背后探微農民的精神困境與迷失的文化根源。
由此,我想起鄉愁話題。因為我的童年、壯年和青年都是在冀東平原一個小村莊和小縣城度過的。小時候,在大槐樹下,聽盲人唱大鼓、算命,下雨了,下雪了,我們到外面看雨,看飄舞的雪花,那是怎樣愜意的事情?在長期的農業文明中,農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幫,溫暖而閑適。古老和諧的農家親情,一直是我們這些走出鄉村游子的精神慰藉。惡意資本和極權對這個氛圍的沖擊和破壞,使鄉村正在經歷著一場從沒有過的震蕩。農民的命運的沉浮和他們的心理變遷,在這一時期表現得尤為豐富、生動。在新的躁動、分化和聚合中,孕育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裂變后的鄉村和農民,懷著難解的憂患和繁復的向往走向了歷史的新形態。
我走進開始新生活的農民中間就想,他們是新人還是舊人?一個生活在城里的人,看見農民、土地和莊稼,還能感動嗎?還能感動,說明我還能寫鄉村小說。《日頭》小說中的毛嘎子在天上的云頂議論抒情,其實是在癡人說夢,他還會圍繞二十八星宿解夢,他在天空中見證了一個村莊由興盛到消亡的過程,但是,他是超脫的,因為超脫才是樂觀的,他離太陽最近身體是溫暖的,作家應該以溫暖寫冷酷,喚起的不是仇恨,而是對同情、憐憫、善良和博愛的憧憬。實際上,我是借毛嘎子的嘴說出我心中最溫暖、最隱秘的東西。這東西就是鄉愁和戀鄉情感。
二十八星宿照亮了我小說里人物的內心,太陽照亮了大地。我贊成一個說法,小說要照亮生活。也就是說,小說最重要的是要點燃或者“照亮”人性中最柔軟的東西。這柔軟的東西是珍貴的,那就是大地鄉情帶來的悲憫和愛。守住這樣的東西,那樣我想,就會達到深掘現實的目的而讓精神飛揚起來。
(作者單位:河北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