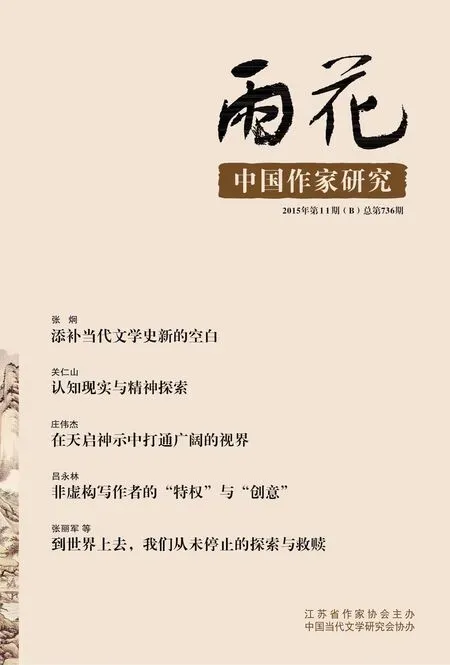《日頭》:中國鄉土文學中的一部力作
■楊立元 楊 揚
《日頭》:中國鄉土文學中的一部力作
■楊立元楊揚
《日頭》是關仁山繼《天高地厚》《麥河》之后“農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目前農村文學中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力作。在這部作品中,作者更加注意探尋人的心靈和時代的真相,追求宏大敘事和史詩意識,以求寫出反映一個時期或一個時代農業發展、農村變化、農民生活的具有史記意義的鄉土文學。最值得稱道的是作者一改前兩部對農村改革的歌頌,而是專注于對中國農村幾千年來的封建流毒、延續至今的中國農民劣根性進行了揭露,尤其是對在改革開放以來,鄉間勢力與資本實力、官場勢力的合謀聯手對農村生活境遇的惡度破壞,對鄉村文明的深度摧殘都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力度。如果說這部小說是魔幻現實主義的精心之作,不如說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一部力作。我們知道,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市場經濟和外來資本侵襲,鄉村文化發生了質的變化:寧靜和諧的鄉村文明和傳統的倫理道德受到了巨大的破壞,鄉村傳統的道德觀念、價值取向、文化結構等都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隨著工業對鄉土資源瘋狂地侵占、掠奪,人們所歌頌和向往的田園風光一去不復返了。農民的家園被破壞,利益被損害,尊嚴被損傷,作為從農村成長起來和生活的關仁山,感到了無限的傷感和傷痛。強烈的憂患意識促使他對當下農村道德失衡、精神異化、文明衰落的境況和原因進行了真實的敘寫和深度的揭示,對鄉村政權的腐敗和鄉村文明的衰落進行了深刻地揭露,這對我們深刻認知農村現狀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所面臨的困境,無疑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首先揭示了鄉村文化的毀壞。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鄉村文化是傳統文化的深厚基礎,鄉村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深重基石。保護鄉村文化亦是保護中華文化和文明。在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現實環境對鄉村文化和中華民族文化的極度破壞。作品的日頭村是一個文化村,有源遠流長的文脈,“傳說村里出過文武兩個狀元,三十一個進士,六十八個舉人,出過尚書、侍郎、翰林和御醫”。“天啟大鐘、狀元槐和魁星閣”是日頭村的文脈,也是日頭的文化符號。盡管幾百年來,作為文狀元的金家和作為武狀元的權家作為日頭村的兩種勢力進行過無數次爭斗,權家人聚眾砸天啟大鐘,拆魁星閣,金家人最終保住了文脈。但在“文革”中魁星閣毀了,大鐘埋了,小學校長金世鑫也因為為了保護天啟大鐘吐血而死,最后就剩下一棵孤零零的老槐樹也險些被鋸掉。但在半個世紀后,開發商與村官勾結,在日頭村蓋樓時,卻為了既得利益,還想把狀元槐挪移挖掉。后來,人們搬出了日頭村,住進了樓房,這時“狀元槐突然不綠了,枝枝杈杈,枯了”。這喻示了鄉村文化徹底衰落和鄉村文明的最后消亡。但作品中也表現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捍衛和守候,金沐灶和他的母親以及鄉親們誓死保護狀元槐,金沐灶為了建魁星閣九死而不悔,最后重新鑄就的天啟大鐘被重新掛在了狀元槐上,鐘聲響徹日頭村。“狀元槐又活了。它的枝條又綠了,它又突出了新綠葉,嫩嫩的,彰顯青春活力。狀元槐死而復活,預示著啥呢?”這預示著中華文化一定會復興,鄉村文化一定會復活。
其次是揭露了鄉村政權的腐敗。異化的社會環境對鄉村政權進行了惡性的腐蝕和侵浸,造成了鄉村政權的腐敗。一些村官成為村霸,他們專橫跋扈,恣意橫行,成為新型的惡霸土豪,如《日頭》的權桑麻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解放前他要飯當乞丐,是苦日子里滾出來的,解放后他憑著對富人的仇恨與兇狠當了村官。他強奸了地主女兒,還把地主推進燕子河淹死了。他敢想敢干,帶著一個由二十九戶貧雇農和四條牛腿組成的農業合作社,在青石板上創高產,轟動全國,當上了全國勞模,見過毛主席,去過莫斯科,在“文革”中成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改革開放以后,他辦鋼廠,建立起了一個鋼鐵王國,村辦集體企業成了他權家的企業。他招商引資開發披霞山鐵礦,與外資袁三定相互勾結,又相互傾軋。他為了既得利益組織挑撥村民械斗,制造鐵礦流血慘案,借機牟利聚財。多年來,盡管很多人狀告他,他都毫發未傷,從解放后一直到死,都是日頭村支書。雖然金沐灶大學畢業后當了披霞山鄉鄉長,與他有了抗衡的能力,最后還是敗在他的手下,被他玩于股掌之中;外商袁三定雖財大氣粗,投資幾個億,但也斗不過他,只好把給他的股份由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了百分之四十。于是他篤定:只要他不死,這日頭村的權永遠是他權桑麻的。他下臺后,安排自己的兒子權國金當書記,死后依然陰魂不散,籠罩在日頭村村民的心頭,使得人們聞聲色變。由此可見,權桑麻是現在農村一個村霸土豪式的典型人物。他手黑心狠,想整倒誰就整倒誰。起初他也有功于日頭村,后來有權有勢有錢以后,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宗法勢力和巨額資財為所欲為。凡與他作對的人,他都要置于死地而后快,尤其是對文化人的摧殘,如對兩個省高考文科狀元金沐灶和汪樹的迫害。他對金沐灶的迫害原因源于祖上延續至今的家族爭斗,雖然金沐灶后來有一定的權力和姐夫袁三定的資金支持,并有了告倒他的證據,但最后的勝利者還是他,卻使得金沐灶丟官失職;對于汪樹的迫害卻僅僅是因為汪樹考上大學后,在接受他的資助時沒有給他下跪,以致在汪樹大學畢業后,他當人才引進讓其任鋼管廠副總,把汪樹一步步引入他設的陷阱中,使得汪樹名譽掃地,最后精神崩潰失瘋,可謂用心歹毒。他膽大妄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村里無所不用其極,為所欲為,甚至要動用資金,想把北京天安門原樣搬進日頭村。盡管他在位幾十年歷經風雨,但其權力權威卻巋然不動,盡管有人多次想置他于死地,但他都能夠憑借多種手段和各種關系逢兇化吉,真可謂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無所不能,無所不通。他正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憑借家族和黑惡勢力,與外來資本合謀掠奪鄉間資源,然后再用手中的金錢收買政府官員們,尋找自己的保護傘。這幾股勢力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形成為一個利益集團,“這個團體嚴重阻礙自由創新,它以犧牲市場效率和公平為代價,攫取個人的巨大財富”,并嚴重地敗壞了黨風、民風、鄉風,因而致使幾千年建構的鄉村文明毀于一旦,豐富的鄉間資源幾年間被耗光殆盡。由此可見,權桑麻這一典型形象既是中國現在農村基層腐敗村官的真實寫照,也是鄉間黑惡勢力的形象表現。這正如作者所說:“這個人物形象本身就涵蓋了中國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史。權桑麻建立的農民帝國,集專制、嚴密、混亂、愚昧、迷信、短視、功利、破壞于一體,他所構建的資本、權力、‘土豪’三位一體的利益格局,成為中國社會利益鏈條的象征。權桑麻死了,但他的陰魂不散,他的脊骨保留在兒子權國金身上,也象征著權桑麻專制體制的實質性延續”。①
再次是呈現了農村的破敗。日頭村是當下境遇中農村的一個縮影,暴露了現今一些農村假繁榮真凋蔽的真實境況。日頭村因為鋼鐵廠的建立和鐵礦的開發,使得生態文明遭到極大破壞,美麗的披霞山“成了光禿禿的和尚了”,鐵礦的粉塵使得日頭村烏煙瘴氣,“植被被污染得百年之內都不會再生長了”。“燕子河污染成黑泥湯子河了,血燕喝了燕子河水毒死一片一片的”。由于污染,村里癌癥病人也越來越多。權國金掌權以后,借搞城鎮化之機,與開發商強占耕地,強拆房屋,強令拆遷,以牟取暴利,逼使汪老七以自焚抗暴,使失地的農民變成實業的農民,只好靠打工或其他手段謀生;搬進樓房的農民因為沒有牛棚,只好把牛趕進樓房的客廳來飼養。村里貧富懸殊在一天天拉大,權家和袁三定瘋狂斂財,把資金轉移國外,土地補償款被權國金和開發商挪用和貪污,而村級集體資產卻基本為零,村民上訪告狀無濟于事。這些也都是目前農村所存在的嚴重問題。
第四是批判了民間集體無意識。鄉間腐敗勢力橫行無忌,固然是多種原因所致,但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民間腐敗集體無意識縱容。在中國民間歷來有“不以腐敗為恥,反以腐敗為榮”的民族心理,它成為了左右群眾的一種政治文化氣場。成為了產生腐敗的溫床和土壤。如《日頭》中村民對權桑麻的敬畏和羨慕,因為他是權力和金錢的象征,死后仍舊魂附權國金的身上,靠骨頭給兒子傳達指令,控制百姓,使得要補償款的村民一聽到他的聲音,聞聲色變,恐慌不已,“紛紛逃了”。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足見權家父子的威懾力:“權國金不管在哪兒現身,人們向他行注目禮,咋看他,咋像他老子。那背著手踱步的姿勢,那斜著眼睛看人的表情,那說話慢條斯理的樣子,那學他老子口頭禪:媽個蛋的。盡管是笑著說的,威懾力照樣厲害。因為,大家伙聽著,感覺跟權桑麻說的一樣。有不少時候,人們聽見明明是權國金在說話走路,可卻是權桑麻現身。揉眼睛再看,就是權桑麻。越揉眼睛看得越清楚。就止不住渾身打哆嗦。人們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權桑麻根本沒死。他還活著,活在日頭村的犄角旮旯,活在每一個人的腦瓜頂上,好像日頭還繞著權桑麻一圈圈地轉哩”。所以,人們對權家父子唯命是從、忌憚恐懼。這不僅說明了權家父子的強勢,也說明了村民素質的低差。正是這種民間腐敗的集體無意識不僅使日頭村的村民失去話語權,失去與腐敗勢力抗衡的能力,而且對日頭村以金沐灶為代表的先進力量有著強大的制約和阻礙力。這樣,小說就從文化的深層探究了如何產生腐敗以及如何根絕腐敗這一重大社會問題。可見,必須要從民間文化基礎和民間集體無意識來著手,提高農民的反腐敗意識,才能從根本上徹底鏟除腐敗。
《日頭》的出版,標志著關仁山這個“農民之子”,腳踏堅實的大地,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由當代農村的歌者變成了一個批判者,這無疑標志著作家批判精神、憂患意識和人文情懷的增強,創作力度和生活厚度的加強,我們希望他能夠更好地為農民鼓與呼,創作出代表一個時期的作品來。
注釋:
①張繼合:《訪作家關仁山:關于〈日頭〉和“農民三部曲”》,《河北日報》2014年9月12日。
(楊立元:唐山師范學院;楊揚: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