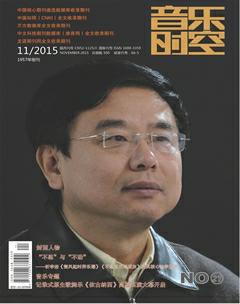談徐州琴書的師徒傳承與師生傳承
摘要:徐州琴書自形成以來,以口傳身授的師徒進行傳承,三百年來培養了大量的優秀藝人,成為蘇魯豫皖一帶有較大影響的曲種,豐富了一方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20世紀50年代后,徐州琴書的傳承出現學校集中教育的師生傳承形式,與民間的師徒傳承并行。通過60年的教學成果比較,可以看出,師徒傳承更具優勢,應是培養優秀琴書藝人的主要傳承途徑,而師生傳承可以作為補充形式存在。文章通過對師徒與師生深層關系的剖析,提出師徒關系中所形成的如同家人般的關系,是師徒傳承優于師生傳承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徐州琴書 師徒傳承 師生傳承
中國傳統音樂分為民歌、說唱、戲曲、歌舞、器樂,雖然歷史上有音樂學校的集中傳承(主要是指宮廷樂坊),但口傳身授的師徒傳承是主要形式。徐州琴書從明清時期的時調小曲發展為說書的曲種,在三百年的過程中,同樣沿襲傳統的師徒傳承形式。近三、四十年,中國從典型的農業文明逐步轉型為與世界接軌的現代化社會,所有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文化都受到現代文化的的挑戰,這也是世界范圍內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在面臨的問題。幸而,從聯合國高層專家到普通民眾都已意識到這個問題,紛紛開始著手保護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使得傳統文化近些年受到普遍關注。徐州琴書在這個氛圍中,于2008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識之士紛紛加入保護隊伍。筆者認為,徐州琴書當下問題,是要尋求一條傳承的路徑,特別是優秀藝人的傳承路徑。只有優秀的琴書藝人才能擔當起徐州琴書開枝散葉的重任,才能承擔起吸引觀眾的首要責任。
通過調查,筆者發現徐州琴書除了沿襲傳統的師徒傳承,還采用了集中教學的師生傳承形式,兩種傳承之間有何異同,對徐州琴書的傳承有何影響,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一、師徒與師生
從現存資料與筆者調查所獲資料中可以看出,徐州琴書的師徒傳承分為家傳與師傳兩種。所謂家傳,即師傅與徒弟為親戚關系,如父女、父子,叔侄等血緣關系,如徐州琴書名家崔金蘭拜自己的父母崔文寶、楊士喜為師。師傳,即招收家族成員以外的徒弟,徒弟之間不存在血緣關系,如民間著名琴書藝人惠忠剛拜師王作迎。無論是否具有血緣關系,師徒關系的建立都必須通過拜師儀式加以確定。拜師儀式上,徒弟送給師傅一定的束脩,并以酒宴邀請業界有頭有臉的前輩作為見證人。通過這樣的儀式,等于向社會宣告師徒關系的正式確立,師徒的這種關系的建立的公開,實際上也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師傅要承擔起授業解惑的責任,徒弟對師傅盡以尊重與敬仰。即使出師后,徒弟逢年過節都要孝敬師傅,這種持續的關系使得師徒之間猶如親人的一般。也有徒弟在學習的過程中,與師傅的子女產生戀情,結成配偶,成為一家人,如惠忠剛后迎娶師傅王作迎之女王秀梅。
師徒傳承中最為重要的環節是師傅會根據業界的行輩,給徒弟一個輩分的字,這個標明徒弟輩分的字,是其進入業界獲得同行認可的一個標志性記號。行業輩分是在家族輩分之外衍生出的另一種“家族”輩分,標志著血緣關系以外的另一個重要的人際關系,對師傅與徒弟都產生一定的制約,同時彼此也產生一定的責任。
1958年,徐州市戲校的琴書班正式開啟了徐州琴書的師生傳承。教師與學生兩者之間為單純的教與學的關系,學制為3年。
二、師徒與師生傳承的比較
從調查可以發現,1958年開辦的徐州戲校的琴書班,選用的琴書老師是當時社會上著名的琴書藝人,有楊士喜(第十七代傳人),孫成才(第十八代傳人)、朱邦俠(第十八代傳人),他們出生于20世紀30年代,基本沒有受到過正規的學校文化教育。在教學方式與內容上,三位教師沿襲傳統的方式,并沒有形成初步的教學大綱與教案,也沒有教材,學生是在教師的口傳身授的教學下學會了唱琴書小段。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徐州市歌舞團又委托戲校分別招收了3批琴書學員,由藝校培養的魏云彩(后拜師楊士喜成為十八代傳人)、張巧玲與蔣立俠教授課程,他們依舊采用琴書老藝人傳統的教學模式。
在開啟琴書師生教學的同時,民間琴書傳承依舊延續師徒的方式,行輩目前已經延續到二十一代,而師生的傳承則以師生論稱,不再涉及到行輩的習俗。
雖然,師徒與師生的傳承在內容與形式上是相同的,但是學習卻產生不同的教學效果,這就是:師傅培養下的徒弟普遍可以唱大書(長篇書目),而教師培養出的學生只能唱小段;而唱小段與唱大書之間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這種鴻溝與學生的天資、學習時間、學習內容、實踐積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一)學生天資的比較
學習琴書需要天資,這種天資基本依賴于學生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如樂感、記憶力、口齒清晰、變通能力),后天很難形成。因此,師徒傳承中,師傅首先要挑選徒弟,會拒絕接收天資不好的求學者。樂感與記憶力是學習琴書的核心能力,特別當大部分學習者都是文盲時,記憶力就上升為學習的核心能力之首。
21世紀前的師生傳承中,生源為文化部門統一招生,如能成為學員,就有了事業單位的鐵飯碗。招生工作中,有時會因為平衡各種關系(平衡各地區招生、平衡各種人際關系等),把一些并不具備學習琴書條件的學員招錄入學,這就一定程度阻礙、限制了琴書傳承隊伍的發展水平。學員本身并不具備學習的主要條件,如口齒不夠清晰,樂感差,所以,教學很難取得理想的教學成果。
(二)學習時間,內容的比較
一般來說,師徒關系傳承中,徒弟從十二、三歲拜師,至少經過五至六年的學習才能出師。而藝校的琴書班的學員經過三年學習即畢業。學習時間的長短意味著學習內容的增減,一般意義上來說,學習一年左右大致可掌握幾個核心曲牌唱腔,也可以拉奏簡短的伴奏,或是掌握擊節樂器的幾種簡單節奏型。學習三年基本可以唱幾個小段;但是若想學會唱大書,則必須積累若干年,這個積累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實踐與創作的過程,必須要在師傅的引領下,依托自身的天資,不斷刻苦學習才能有所成就。唱大書有幾個必要條件:一是掌握對核心曲牌變化創作的手法,做到萬變不離其宗;二是摸索唱大書的竅門,深諳如何去發展故事情節;三是充分把握觀眾的心理,依托一些手法吸引觀眾;四是形成創作新書目的基本技能。具備以上四項,才能基本把握唱大書的技巧,才能在琴書界安身立命,否則,只能成為一位平庸、缺乏創新能力的琴書藝人。
(三)實踐積累的比較
師徒關系中的徒弟一般從學藝初始就陪同師傅到處賣藝,邊學邊實踐,在跑碼頭的過程中,見識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同行同吃同住,增進了與師傅的感情,師傅的言談舉止對徒弟形成潛移默化地影響,徒弟的一舉一動會折射出師傅的影子,因此,逐漸形成師門的風格體系。
師生關系中的學員,失去了傳統意義上的師徒關系的制約,彼此獨立,教學以外接觸的時間減少;再加之學員在學習期間,接觸實踐演出的機會相對較少,所以,學員很難從觀眾的反饋中了解自己的水平、也缺失了與觀眾互動的機會。因為受到舞臺演出時間的制約,1958年后,進入專業院團的琴書藝人多以短篇小段演出,中篇書目少有機會登臺,更難得有演唱大書的機會。因此,琴書學員痛失接觸大書的機會,不了解長篇大書的文學曲本的來龍去脈與操作手法,琴書學員們就一直被局限在十幾分鐘的小段中,切斷了中長篇書目學習機會。
師徒傳承與師生傳承最終差異是,師徒傳承中的徒弟掌握了唱大書的技巧與方法,而師生傳承中的學生只掌握了唱小段的技能,除卻學習者天資的不同,應該是師徒制的學習時間較長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剛剛出師的徒弟往往陪著師傅到處跑碼頭,在實踐中逐漸熟悉技巧,在磨練中逐步掌握中長篇書目的方法,方能逐漸成熟起來。當徒弟有能力演唱中長篇書目時,才敢脫離師傅自己單獨去行藝。這個磨練過程要依靠師傅帶領,引導,而師生關系的學習過程缺失了這個重要環節,而這個環節對于優秀琴書藝人的培養與成長至關重要。由于要降演出的低經濟成本,許多藝人都是一人成班,獨行闖天下,這對藝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個人必須掌握過硬的專業技術能力,否則難挑大梁。
三、師徒與師生傳承差別的主要因素
通過上文,可看出師徒傳承與師生傳承的差別主要有天資、學習內容與時間以及教學實踐三個方面。那如果三個方面都做到同步一致,可以逾越兩種教學的差別,從而達到師徒傳承與師生傳承的一致?
筆者從調研資料剖析結果認為,師徒傳承與師生傳承即使運用方法一致,也難以達到同等效果。
從表面上看,除卻學習時間與實踐的因素,師徒制與師生制從教學方式與內容上來看,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師生制省略了一個拜師的環節,而這個環節在20世紀50、60年代是符合當時社會需要的,即打破一切舊社會的習俗,師徒傳承的負面因素被夸大,師傅的形象被丑化,而徒弟被打造成為弱勢群體,這一定程度削弱了師傅的權威性,師傅與徒弟之間的關系緊張化,之間的信任被弱化。但是伴隨著中華文明幾千年文明走來的師徒傳,承畢竟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其存在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從當下徐州琴書的傳承現狀,可以看出師徒傳承的培養途徑比師生傳承有一定優勢,這種優勢體現在以下三點。
(一)心理的認同
心理認同是師徒與師生傳承中至關重要的一點。除卻血緣關系的師徒關系外,徒弟入師門之后,與師傅乃至其家人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徒弟在學藝的同時,也伴隨師傅行街賣藝,在這樣的環境中,徒弟慢慢與師傅形成了深厚的情感,這種情感是以血緣為關系的家族情感的延伸。在中國這種以家庭、家族為基本構成單位的社會中,這種師徒情感甚至會高于血緣情感,師傅會把徒弟視為家庭的一員。而徒弟也會視師傅為再生父母,這種尊重、敬仰又會不斷拉近師徒之間的距離,特別是師傅名望很高,在一方收徒達到相當數量時,師門的興旺如同家族的興旺,會促成一個門派的或流派的形成,并長久不衰。如20世紀末,江蘇宿遷(俗稱“南徐州”)的琴書“柴門”創建人李義成,在世時收徒多達一百多人,至目前其徒子徒孫仍在蘇魯豫皖一代有相當影響力,雖后分成南門與北門兩派,但是都是師出“柴門”。這種師徒之間的心理認同,拉近了彼此的情感,視彼此為家人,奠定了學習的良好心理環境與氛圍。
(二)責任的擔當
師徒制的關系往往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形成了親情,這種親情使得師徒之間的關系勝似父子,母女,徒弟的成功也是師傅的驕傲,使得師傅的門派發揚光大,會有更多的徒弟慕名而來,光耀師傅的門庭。在這種心理驅使下,師傅會把自己的看家本領不遺余力地教授給徒弟,特別是年長的師傅,會有一種使命感,這種愿望會更加強烈,而徒弟在師傅責任感與使命感的雙重驅使下,成績會更為優秀。從徐州琴書的師生傳承來看,缺失了拜師的環節,就缺少了一個親密聯系的紐帶,特別是有的學員對待老師并不是敬重有加,導致了從師徒傳承關系中成長出來的老師的失落感,使得他們在教學時自然遠離了這種使命感與責任感。
(三)風格的形成
不同的門派呈現出不同的藝術特征與藝術風范,徒弟在隨師學習耳濡目染的過程中,不僅掌握了師傅的技術,而且掌握了師傅的對音樂、對曲本文學的獨特處理方法,更有聰慧的徒弟在此基礎上融會貫通,有所發展,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這些風格從唱腔的腔彎處理、伴奏的音型選擇使用、韻轍的使用習慣等方面表現出來,形成個人的獨特藝術魅力。這種風格上效仿是在長期隨師學習的過程中,受到師傅的影響潛移默化影響而成,也是徒弟在藝術方面成熟的一個標志性特征。
以筆者調查所見,凡在民間有較大影響力的琴書藝人,皆出于師徒傳承,如當紅琴書藝人惠忠剛、王秀梅、丁相宇等,他們錄制了許多音像作品,在蘇魯豫皖一代城鄉有著廣泛的影響。在與這些師徒傳承民間藝人和師生傳承的琴書學員的比較中,筆者逐漸認識到師徒與師生兩種傳承的差異,由此形成尋求二者差異的原因的想法。
在資料匯總與對比的過程中,筆者尋覓到了二者差異的核心問題,這就是心理認同的差別以及由此而導致的一系列教學的效果差異,這種差異在近兩年老琴書藝人招收私人徒弟的過程中得到印證。徐州琴書第十八代傳人魏云彩曾親自參與徐州琴書的師生傳承的三撥教學任務,感覺并沒有培養出令其得意的學生;他退休后于2013年開始招收私人徒弟,僅僅一年的教學時間,就碩果累累,其中一個女徒弟在各個方面都展示出魏云彩老師的教學成果;作為一位徐州琴書的研究者,筆者見證了師徒傳承的優勢。
因此,筆者從徐州琴書表演傳承角度出發,提出徐州琴書的傳承的核心力量要仰仗傳統的師徒方式,而師生這種教學方式可以作為大范圍培養傳承人的補充形式,這兩者相互結合,相互補充是當下培養琴書傳承人的最佳途徑。
基金項目:
本文為2015年度江蘇省課題《試探徐州琴書的師生傳承與師徒傳承》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5SYB-080。
作者簡介:
[1]于雅琳:徐州工程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