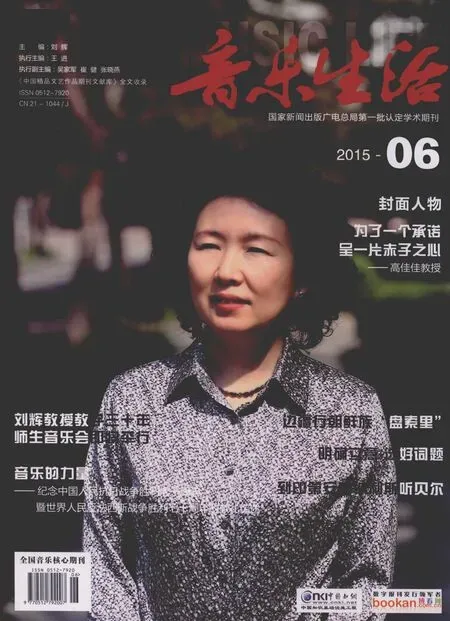中國革命音樂的先驅
——
文/喬書田
中國革命音樂的先驅
——
文/喬書田


1985年7月,剛剛退居二線的呂驥在夫人關立人陪同下再次赴蘭州,對甘肅省六大文化遺址之一的火燒溝出土的陶塤,做進一步考察。在甘肅省音協副主席李曙明協助下,他先后三天到甘肅省博物館,對新出土的與1976年出土的各種陶塤進行吹奏、錄音。他尤其對其中一個發音極難的“雙鴨型”陶塤感興趣。經李曙明再三吹奏,終于找準了它的音階,呂驥用自己隨身攜帶的小錄音機,錄下了它的基本音列。
臨別時,他建議甘肅省文化部門成立一個“中國塤學會”,對塤進行全面、有組織的考察與研究。
9月18日,以呂驥為團長,中國音協副主席瞿維等4人為團員的中國音樂家代表團離京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會員國代表身份出席在德累斯頓舉行的“國際音樂理事會”(簡稱“國際音理會”)①第二十一屆會員國和名譽會員大會。已是國際音理會名譽會員的賀綠汀也出席了大會。
在本屆會議上,呂驥當選為國際音理會的名譽會員。
大會結束時,呂驥應邀率團訪問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和奧地利。在德國,他們先后到波恩和萊比錫參觀了貝多芬的出生地,憑吊了位于圣托馬斯大教堂內的巴赫墓。據說,巴赫的遺骨也是幾經戰亂,幾經尋找,幾經搬遷,最后安葬在圣托馬斯大教堂內的。因巴赫生前為大教堂寫過大量的圣樂,墓地就在大教堂主祭壇的前面,一塊墓碑上鐫刻著巴赫的名字和生卒年。他們還參觀了巴赫紀念館。
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他們游覽了古典浪漫主義前期最著名的鋼琴家、作曲家李斯特的故居街和李斯特紀念館。李斯特10歲離開祖國,到維也納學習鋼琴。16歲定居巴黎。之后又先后在德國的魏瑪和拜羅伊特生活多年。在距拜羅伊特劇院不遠有一座被常青藤圍繞的小樓,是李斯特曾居住過多年的地方。院子里有李斯特的銅像,二樓臥室里懸掛著美婦人達古爾特的肖像。達古爾特原本是一位伯爵夫人,23歲那年愛上了李斯特,與他私奔到瑞士。在瑞士,為他生下了三個孩子,其中兩個夭折,只有一個女兒庫茲瑪活了下來,后嫁給了比李斯特僅小兩歲的作曲家瓦格納。呂驥在拜羅伊特城邊的墓園里,瞻仰了小石亭內的李斯特墓。
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他們參觀了莫扎特和貝多芬的故居。來到了維也納,才知道,莫扎特在維也納住過許多地方。但能讓他們參觀到的只有位于多姆街5號大教堂巷內的故居,有4個房間、兩個小陳列室、一個廚房。莫扎特在這里度過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4年時間。他在這里創作了最著名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
貝多芬在維也納的故居也有20多處,但主要有兩處。一處在維也納北郊的海里根施塔特,按德文翻譯過來的意思是“圣城”。這里毗鄰“維也納森林”,田園風光令人心曠神怡。貝多芬在這里創作了他的第二交響曲等作品。另一處是位于維也納大學斜對面的帕斯克瓦拉提屋。這是一座以帕斯克瓦拉提男爵的名字命名的建筑,落成于1798年。據說,男爵十分崇拜貝多芬,為他提供了五樓的一套住房,并給予他多方面的幫助。貝多芬曾先后多次在這里居住,累計長達8年之久。他在這里創作了著名的第五交響曲(命運)、第六交響曲(田園),鋼琴曲《致愛麗絲》等作品。代表團還到維也納的中央公墓,瞻仰了眾多音樂家的墓地。貝多芬墓與舒伯特墓在前排的中心位置;勃拉姆斯墓與約翰·施特勞斯墓相依相伴……曾妒忌莫扎特的宮廷樂師薩里耶利的墓也在這里,不過,他的墓遠離了令人矚目的中心區,葬在了一個偏僻的角落里,這一點很耐人尋味。處在中心區中央的是莫扎特的衣冠冢。因莫扎特的遺骨已無法找到。它兩邊,一邊是貝多芬墓,一邊是舒伯特墓。
10月末,呂驥率代表團圓滿完成了出訪任務,回到北京。1985年11月,為紀念聶耳逝世五十周年、冼星海逝世四十周年和誕辰八十周年,“聶耳、冼星海學會”在武漢舉行“聶耳、冼星海音樂創作學術討論會”。剛剛回國不久的呂驥與音協主席李煥之、副主席時樂蒙、瞿維,以及聶耳、冼星海的親屬、戰友聶敘倫、錢韻玲、錢遠鐸等,還有來自全國17個省、市音協分會的負責人、14所音樂院校、13個專業音樂研究機構及文藝團體的學者、專家,共70多人出席了討論會。
其間,11月26日上午10時,中國音樂家協會主持的“冼星海骨灰起靈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②。隨后,由嚴良堃和冼星海的女兒冼妮娜護送,乘火車送往廣州。11月27日上午,“聶耳、冼星海音樂創作學術討論會”剛剛結束,護送冼星海骨灰的列車到達武漢,參加討論會的呂驥和全體與會者及湖北省、武漢市的部分音樂工作者,到車站列隊迎靈。隨即,呂驥與音協主席李煥之登上列車,護送骨灰赴廣州。
12月1日,在廣州麓湖公園,“廣東省紀念聶耳、冼星海大會”及“星海園”落成揭幕典禮、“冼星海骨灰遷葬儀式”系列活動相繼舉行。廣東省委副書記謝非、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李煥之分別在紀念大會上講了話。
鄧穎超委托大會獻了花籃。12月2日上午,正式宣布“廣東音樂學院”更名為“星海音樂學院”,并在學院內舉行了“冼星海塑像揭幕儀式”。中顧委常委王首道、文化部副部長周巍峙出席了儀式。呂驥在儀式上講了話。廣東省紀念大會主任委員、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應彬(即楊石),副省長王屏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杜聯堅,以及星海音樂學院院長趙宋光,都在儀式上講了話。
12月4日,冼星海的骨灰安葬儀式在白云山下的麓湖公園內剛剛落成的“星海園”舉行。隨后,《冼星海全集》編輯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編委會議。主編、文化部副部長周巍峙和副主編、中國音協主席李煥之主持了會議,就當前出版《冼星海全集》的重大意義和有利條件,以及編輯這套十卷本巨著的宗旨、方針和要求,進行了認真討論。呂驥作為編委會顧問,出席了會議。
1986年3月25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會議期間,呂驥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接受了《北京晚報》的采訪。他對目前的學校教育問題、特別是美育教育問題,發表了個人意見。4月8日,《北京晚報》發表了他的談話紀要。
5月初,他以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身份,隨人大視察團到福建視察。在福州,他參加了福建省舉辦的“第四屆學校音樂周”活動,觀看了學生們的表演。他興奮地對福建省教育部門的領導同志說,“在學校開展‘音樂周’活動,對青少年進行美育教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這在全國還是一個創舉。”
由于連日奔波于“八閩之地”,南國過于悶熱潮濕的氣候,加上臺風頻發,已經77歲高齡的呂驥,有些不適應,體溫一直高燒不退。大家勸他提前回京休息,但他一直堅持到工作結束,致使病情不斷加重。回到北京時,不得不直接從首都機場送往協和醫院住院治療。
9月中旬,由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河南省委宣傳部、音協河南省分會、沁陽縣委縣政府、沁陽縣文化局等10多家單位聯合舉辦的“紀念我國明代著名的自然科學家、音樂學家朱載堉誕辰450周年紀念會暨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河南鄭州和沁陽縣兩地舉行。呂驥應邀赴鄭州出席了紀念大會,隨后又赴沁陽縣出席了學術研討會。這是我國建國以來召開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有關朱載堉在各個領域、各個學科所取得成就的研討會。全國一百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領域稱贊朱載堉為“自然科學家”、“數學家”、“藝術家”、“音樂家”、“樂學家”、“音樂史學家”、“音樂美學家”、“舞樂思想家”、“著作家”、“教育家”等等,為他總結出了無數個“世界第一”。這大大出乎沁陽縣人民的意料,使沁陽縣人民倍感驕傲和自豪。沁陽縣的“鄭藩樂府”始建于明代,朱載堉曾在這里與父親一起研習音律。1991年沁陽縣改市后,市政府將“鄭藩樂府”辟為“朱載堉紀念館”,并請呂驥題寫了館名,供人們永久參觀。館內設有4個展室,分別展示了朱載堉的家世、生平、學術成就和在國內外的影響等。
1986年12月3日,國家民委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首次學術性的“十二木卡姆專題音樂會”。 《十二木卡姆》是維吾爾族人民一筆寶貴的音樂財富。早在1951年,呂驥擔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后,就十分關注《十二木卡姆》的收集、整理工作。當時,他將學院研究部的萬桐書夫婦派往新疆工作。他們在呂驥的支持、幫助下,用了近十年時間,克服種種困難,歷盡千辛萬苦,錄音、記譜、整理、出版了兩卷本的《十二木卡姆》樂譜。新疆人民曾感慨地說,沒有萬桐書就沒有今天的《十二木卡姆》。
在這次“專題音樂會”上,由新疆藝術研究所和新疆歌舞團聯合演出了《且比亞特木卡姆》③木卡姆,又稱“馬卡姆”、“瑪卡姆”,阿拉伯文的音譯,意思是“地點”、“地位”、“法律”。作為音樂術語,意為成套的民伺古典音樂。《且比亞特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中的第二套木卡姆。。呂驥出席了音樂會,高興地聆聽了新疆藝術家們的精彩演出。出席音樂會的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和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以及屈武、高占祥、李煥之等。
隨著時光的不斷推移,我國的改革開放不斷深入。西方流行音樂和港臺音樂大量涌入我國,國內的一些媒體、音樂組織、中央電視臺等,也大開方便之門,予以廣泛傳播。隨后,“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民歌通俗歌曲大獎賽”等活動相繼活躍起來,使得老一代革命音樂家大為惱火。他們認為外國流行音樂和港臺音樂的涌入,對我國傳統的革命音樂形成了很大的沖擊。為此,呂驥在1987年第四期的《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了《音樂藝術要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文。文章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對近幾年來出現的“新潮派”以及在音樂理論、音樂創作、表演藝術等方面出現的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提出了嚴厲批評。文章指出,“我們的人民今天迫切地要求音樂作品深刻地反映他們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強烈而豐富多彩的熱情,要求情緒昂揚而活潑的音樂鼓舞他們奮發向上,要求遼闊而悠遠的抒情音樂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要求既深沉又富于幻想、色彩絢麗的音樂引導他們對于過去的苦難的回顧和對明天理想和幸福的追求”。文章說,“從藝術發展史宏觀來看,無論從美學角度,還是社會角度,人民都是決定的因素”。不久,《中國音樂學》《人民音樂》等刊物,相繼在遼寧興城組織召開了“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座談會”和“大連會議”。其后,在中國音協主辦的刊物上,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向中國革命音樂傳統及革命音樂的發展歷史提出挑戰。認為從三十年代起,一直到建國以后的17年,音樂藝術始終處在被“異化”的狀態,抑制了個人的創作自由和創作能力的發展。主張在音樂創作活動中恢復“主體體驗”、“主體意識”和“自我表現”。老一代革命音樂家認為,這是對優秀的革命音樂傳統的“否定”和“背叛”。從而,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責任編輯 張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