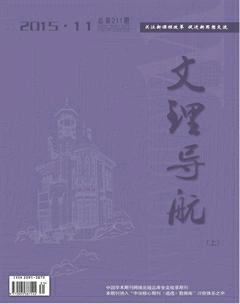語言的力量
胡斌
【摘 要】語言是一個民族和國家形成和凝聚的根本,語言的發展必然會推動社會的發展,同樣社會的發展也會帶來語言的變革。近代西方思想解放也是語言的革命,用不同的語言承載著人文精神的發展和壯大,在社會面臨著困境,人類面對著墮落的情況下,語言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時代爆發了。但丁的俗語和路德的德語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有利于社會的整合,沖破教會的專制,而法語從18世紀以后更是成了民主的重要載體。教學中,在我們關注近代西方思想解放潮流的同時,也要注重語言的力量。
【關鍵詞】語言;西方近代思想解放;解讀
在高中歷史教學中,《西方人文主義的起源與發展》一課就是著重探討這種近代興起于西方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在教材的編寫和教師的講授中往往注重對內容的講述和理解,如意大利文學三杰的主要作品及其主要意旨;馬丁·路德“因信稱義”的思想;啟蒙運動與文藝復興時期人文思想的異同等。其實在教師對思想內容和精神內涵的分析探討中,還有一個隱藏的領域,它往往被忽視,即語言。語言是一個民族和國家形成和凝聚的根本,語言的發展必然會推動社會的發展,同樣社會的發展也會帶來語言的變革。在我們的教學中會關注到中國新文化運動期間用白話文反對文言文而推動思想解放,但在近代西方的思想解放中語言問題卻少有提及。閱讀教材,我們會發現薄伽丘的《十日談》是用意大利方言進行創作的;馬丁·路德將圣經翻譯成德語,在那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人文主義者為什么要進行語言的更新,語言有怎樣的一種力量?本文從語言的角度對近代西方思想的解放的問題進行一些探討。
一、文藝復興,意大利語打破對身份的迷信
作為從中世紀向近代轉型期間的重要詩人——但丁,我們最為熟知的是其代表作《神曲》,率先表達了對教會丑惡現象的憎惡。除了詩人的身份外,但丁還被稱為意大利語之父,在法語中,意大利語被稱為“但丁的語言”。他有一部重要的理論著作——《論俗語》,這部著作為建立和規范統一的意大利民族語言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奠定了但丁在意大利語言上的地位。一個人文主義者為什么會成為意大利語言的奠基人?是偶然嗎?意大利語言與但丁所倡導的思想解放有關系嗎?
在中世紀,拉丁語是西歐、中歐、南歐一部和北歐廣大地區的國際通用語,天主教世界的宗教用語,學術、文化、科學的書面語。一切官方用語,包括文學作品,都是用拉丁文,平民大多是看不懂的。拉丁語作為基督教文化傳播的媒介,作為神學的代表者,向來占據著至高無上的地位,造就了僧侶對文化、思想和教育的壟斷,通過語言的差異,區分高貴和低賤,使用什么樣的語言是一種身份的象征。這種現象長久以來在思想領域培植了一種非此拉丁語莫屬的權威心理,17世紀的英國作家彌爾頓還認為他的《失樂園》倘若用拉丁文寫成,會是一部更偉大的史詩,即使但丁本人創作《論俗語》這篇文章時也是用的拉丁文。
相較于拉丁語,所謂俗語,但丁這樣說:“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語之時從周圍的人們聽慣而且熟習的那種語言,簡而言之,俗語乃是我們不憑任何規律,從模仿乳母而學來的那種語言”。由此可知,俗語就是母語,她是人天生具有的能力,是我們最為熟悉、最易接受的語言,她是普通人思想重要的載體。倡導用“俗語”,其本身就是對中世紀宗教專制壟斷的沖擊。但丁表示官方宮廷用語(拉丁語)是“矯揉造作的”,而俗語簡單易懂,符合自然,反而是“較高貴的語言”。用“俗語”取代拉丁文,是作為一種平民化的表述策略,同時也作為民族群體的思維方式植根于民族的靈魂深處,它能夠表達民間的聲音,表達其精妙細致的思想感情、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語言。把文學的表現權利第一次交還給了人民大眾,這是但丁提倡創造高貴的俗語的進步所在。用民族語言不僅是形式上的突破,更為內容更新、受眾層面的擴大和優秀作品的創作奠定基礎。但丁創作《神曲》時原打算用拉丁文,不過他最終還是放棄了初衷,改用了佛羅倫薩方言。對此薄伽丘《但丁傳》解釋說,“但丁此舉是為他的絕大多數佛羅倫薩的意大利同胞著想。”因此,但丁、薄伽丘以語言為武器,打破身份上的限制,用所謂俗語對抗教會束縛、宣揚新興思想、倡導思想解放,語言也成為了重要的武器。
二、宗教改革,用德語挑戰教會
文藝復興時期的民族語言,是新興資產階級追求對自己身份認同、打破教會束縛的產物,而馬丁·路德則是用德語直接抗衡了教會,打通了一條自由之路。
《圣經》是基督教的圣典,也是教會統治人間的依據,在15世紀以前《圣經》主要是拉丁文寫成,由神職人員代為宣講并傳播給民眾的。語言成為了民眾與“上帝”之間的障礙,羅馬教廷利用對《圣經》解讀的壟斷地位和人們的信仰,麻痹人民,兜售“贖罪券”。教皇通過各國各地的教會對全社會進行精神統治,以神權壓制人權、以神圣禁錮個性、以天主教義反對科學創造、以經院哲學封殺學術自由,企圖以一本圣經定天下,通過控制對圣經的解釋權和閱讀權隨心所欲地篡改教義。路德指出,神職人員任意解釋《圣經》,是出于愚弄人民和統治人們的需要,而不是真正地傳播基督教,他認為每個普通教徒都應該自己閱讀《圣經》,直接跟“上帝”對話。在這樣的背景下,馬丁·路德著手翻譯《新約圣經》,并與1522年以后陸續出版。為了更好體現路德宗教改革的思想,讓《圣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民眾與上帝之間的階梯,實現其“因信稱義”的思想,他在翻譯《圣經》時借鑒前人翻譯的基礎上,更著重大眾化的語言,其宗旨就是用日常生活中生動易懂的語言來代替原來晦澀難懂的書本語言。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應該跟家里的母親、街上的孩童、市集的平民聊聊天,聽聽他們是怎么說話的,然后用他們能懂的文字去翻。”這樣的《圣經》迅速被大眾所掌握,不僅成為他們反對僧俗統治階級的工具、促進了他們反對羅馬教會和反對專制主義的斗爭,而且成為宗教改革的推動力,使德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變化。
另外,路德翻譯圣經也努力加強了德國的民族意識,使德國教會走上民族化的道路,推動了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覺醒,完成了宗教獨立的壯舉。德意志民族在成為一個真正國家之前迎來了一個思想自由交流、擺脫教會束縛的大時代,為之后走向統一奠定基礎。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傳播和德語圣經的影響,歐洲許多國家開始將圣經譯成自己的民族語言,各國語言版的圣經不斷涌現,荷蘭、瑞典、冰島、丹麥等國語言的圣經直接來源于德語圣經。通過德語圣經,人們紛紛擺脫教會的控制,激發了自我意識的成熟,用民族語言的圣經進一步打通了一個自由的社會道路,讓個人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
三、啟蒙運動,法語象征光明、自由
啟蒙運動以法國為中心,隨著它的發展,18世紀成了法語的時代。很多國王都成為法語迷,很多國家上層社會的達官貴人都以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而感到自豪。如普魯士第三代國王腓特烈大帝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親法國王。他對法語如此癡迷,以至于他不斷地重復說,他只學習一種語言,那就是法語。他模仿凡爾賽宮的建筑風格,讓人在德國的東部波茨坦修建了一個新宮邸,取名為“逍遙宮”。他在宮廷、軍隊以及行政機構內都聘請了很多法國人。他只看用法語演出的劇目,并自己學習用法語吟詩作詞,他和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伏爾泰保持長期的通信聯系。在1752年的一天早上,伏爾泰甚至還收到了與腓特烈大帝共進晚餐的邀請。腓特烈大帝通過學習法國哲學思想以獲得輿論的支持,重塑國家威望。
我們每天都在用語言,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語言的力量有多么強大。近代西方思想解放也是語言的革命,用不同的語言承載著人文精神的發展和壯大,但丁說:“我們稱作光輝的語言,只有最高尚的事物才配得上用這種語言來表達。”語言是神奇的,它可以回憶過去,同樣也可以指示未來。但丁的“俗語”和馬丁·路德的德語、伏爾泰的法語雖然語言的形式不同,但他們在各自社會的根本作用是相同的。在社會面臨著困境,人類面對著墮落的情況下,語言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時代爆發了。但丁的俗語和路德的德語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有利于社會的整合,沖破教會的專制,而法語從18世紀以后更是成了民主的重要載體。教學中,在我們關注近代西方思想解放潮流的同時,也要注重語言的力量。
【參考文獻】
[1]章安祺,繆靈珠.《美學譯文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
[2]吳世永.《俗語與白話:全球化中的語言突圍——但丁<論俗語>與中國、印度白話文學觀之比較》.學習與探索,2004年第3期
[3]杜美.德國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4]王明利.《論啟蒙運動與法語的輝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
[5]呂同六編著,錢中文主編.讀意大利[M].泰山出版社,2008年
(作者單位:江蘇南京市第十二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