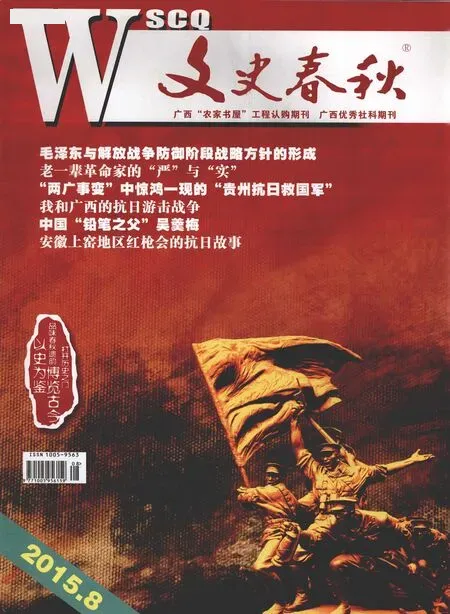老一輩革命家的“嚴”與“實”
●王建柱
老一輩革命家的“嚴”與“實”
●王建柱

無論是在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老一輩革命家們崇嚴尚實的故事一直被口口相傳,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當前,領導干部 “三嚴三實”(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專題教育正在全國范圍內全面開展,本文特輯錄幾位老一輩革命家 “嚴”“實”作風的小故事,以饗讀者。
毛澤東 駐村調查,甘當小學生
1933年,由于李立三和王明的 “左”傾冒險主義者推行的 “左”政策,導致了一些上級機關不知道鄉、村蘇維埃政權的具體工作和實際內容,只知道發布命令和決議,從而阻礙了中央蘇區政府任務與計劃的執行。
正是在此背景下,時任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于當年11月下旬長途跋涉,從江西瑞金來到閩西一個偏遠的小山鄉才溪進行第三次社會調查。此前,他曾于1930年6月、1932年6月兩次深入才溪調查研究。
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情況,毛澤東決定駐村調查。隨行人員擔心他太勞累了,建議說:“開了名單請有關人員來不是一樣嗎?”
“這不行。”毛澤東耐心地說,“我們做調查研究,應該有張良求師的精神。沒有滿腔的熱情,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那是一定做不好調查工作的。”
深入紅軍公田檢查生產、參加勞動、給衰坑改村名……正是憑著 “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毛澤東在調查中幫助群眾解決了一個又一個難題。
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總結了人民群眾的發明創造,寫下 《才溪鄉調查》一文。這篇調查報告解決了革命環境下根據地建設不僅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問題,充分調動了黨內領導干部主動參與到實地調研、深入分析、系統總結經驗和教訓的積極性與熱情。
1934年1月22日,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強調了 “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保證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的工作方針。這一方針正是建立在才溪鄉調查報告的基礎上,并把這些正確的做法上升為政府的決策方針,為處在緊要關頭的黨的建設指明了出路。
劉少奇 讓農民通訊員每年寫幾封信,反映農村情況
1953年7月,正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的劉正山回老家過暑假,離京前,他去中南海看望叔爺爺劉少奇。劉少奇交給他一項任務,回鄉后為他找幾個農民通訊員,請他們每年寫幾封信,反映農村的情況。
王升平是炭子沖的農會主席,當年他親手抓了選拔通訊員這項工作。他常常把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寫信告訴劉少奇。尤其是對1958年 “大躍進”中挨家挨戶收鐵鍋、拆房子的做法想不通,一連給劉少奇寫過幾封信。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王升平一邊給劉少奇寫信,抨擊農村刮 “五風”,一邊自己又加入到了刮 “五風”的行列中。群眾對他意見很大,公社黨委撤銷了他大隊支部書記的職務,要求他向群眾作檢討。
1961年5月,劉少奇在湖南調研時,接見了王升平。
劉少奇批評說:“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農田改成魚池,搞得那么大,費了那么多工,也不養魚。山上本來長滿了樹木,你砍了樹木開茶園,青山成了荒山。搞這些,你跟群眾商量過沒有?”“你到大隊臨時醫院去看看,那些奄奄一息的水腫病人,隊里還有不少因饑餓而死亡的群眾,一想起他們,我心里就難過,一連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你身為大隊支書,難道不應該把自己也擺進去?”劉少奇嚴肅地說:“由于我們的過失,讓群眾遭了罪,不檢討說得過去嗎?檢討了,群眾諒解了,你還可以出來工作,前提是徹底改正錯誤!”
劉少奇接著問他辦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并說:“你不要有顧慮,把你請來,就是要讓你講真心話!”王升平鼓起勇氣說:“報告劉主席,這公共食堂如果再要辦下去,將來會弄得人死路絕,國破家亡!”他列舉了辦公共食堂的種種弊端。
劉少奇說:“既然辦公共食堂不好,中央制定的 《六十條》也發下來了,那你們的食堂為什么還不解散呢?”
王升平解釋道:上級有指示,說這是劉主席的家鄉,解散食堂一定要慎重。
劉少奇聽罷生氣地說:“顧這些虛名干什么,怎么不想想群眾還在餓肚子!”“你還是共產黨員嘛,回去跟群眾商量一下,就說中央的 《六十條》有規定,可以不辦食堂,如果群眾同意,就把食堂散了。你給群眾辦了實事,群眾會諒解你!”
幾天后,食堂停辦了。有的群眾一聽是劉主席支持解散食堂,都說搭幫了劉主席,不然,哪個敢解散食堂啊?劉少奇擺手說:“不是搭幫我,是中央制定了 《六十條》,順應了群眾的要求。”
在家鄉,劉少奇真誠地對鄉親們說:“將近40年沒有回家了,回來后看你們生活很苦,我們工作沒有做好,很對不起你們!”每到一處,劉少奇總是誠懇地向群眾道歉,為前些年工作的失誤主動承擔責任。
董必武 從不以黨和國家的 “元老”自居
1945年6月,聯合國創建大會在美國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并代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在 《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他出國時所穿的那套西裝是在重慶買的,很不合身。在別人的一再勸說下,董老到紐約后,便托 《華僑日報》的同志花25美元買了一套西裝。
董老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國訪問,訪問期間,他精打細算,把節約下來的外匯都上交國家。這三筆錢共計2600多美元。他平時也將醫藥費、郵電費之類的小賬記得清清楚楚。
董老對子女和親戚也是嚴格要求。
1969年的春天,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董老堅決把自己的小兒子董良翮送到了河北晉縣農村去鍛煉。在董良翮下鄉前,董老題詞諄諄囑咐他:“到晉縣農村去,要好好學習毛澤東著作,努力勞動,爭取當個好農民。”
1970年,董良翮入了黨,后擔任村黨支部書記。董老馬上寫信告誡兒子:“一是不要 ‘一得自矜’,二是不要 ‘淺嘗輒止’。”董老去世前對夫人何蓮芝說:“良翮是晉縣的人了,由晉縣組織上去安排,我們不必多操心了。”
董老對侄兒、侄女們要求很嚴格。有一次,侄女從甘肅來信,大意是要董老收她做女兒。這件事事出有因。當年,董老得知兄弟去世后,曾提出幫助弟媳帶一個孩子。可當時弟媳沒同意。她也有自己的考慮:那時董老已是中共高級干部,而她們仍在白區,隨時都有遭受敵人迫害的危險。現在情況完全變了,再要改變這種伯侄關系已無必要。他認為是侄女思想上出了毛病。于是,董必武給侄女寫信說:“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走,靠老老實實地去工作,不是靠父母。如果靠我,我死了怎么辦呀?”
董老就是這樣,從不以黨和國家的元老而自居,不謀私利,不搞特權。他還題寫了“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性習于儉,儉以養廉”作為座右銘自勉。
陳云 決不能把功勞記在自己一個人的賬上
陳云生前把自己的整個生命都融入到黨的事業之中。他從不喜歡拋頭露面,對各種公開活動、場面活動,只要可以不參加,他都不參加不出席。有關宣傳他的材料,只要報到他那里,幾乎都被他拿了下來。
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陳云曾經講過:“假設你在黨的領導下做一點工作,做得不錯,對這個功勞怎樣看法?我說這里有三個因素: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轉一下,第一是個人,第二是黨,第三是老百姓?我看這次序不能顛倒啊。”1982年在編輯 《陳云文稿》時,他特別囑咐,在 《后記》中一定要寫明,他在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期間,所有的重大決策,都是在經過調查研究,經過集體討論并報請黨中央批準的。決不能把功勞記在自己一個人的賬上。“不收禮、不吃請”是陳云立下的一條規矩,身邊工作人員更不得違反。“不迎不送,不請不到”是陳云在去外地視察和休養時,對地方領導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擾他們。“不居功,不自恃”是陳云處人處事的準則。
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堅決要求在待遇和宣傳上不能把自己和毛劉周朱并列。蘇聯政府贈送給新中國五大書記每人一輛驕車,他堅持要把給自己的那輛車退回。中共八大之后,叢書 《紅旗飄飄》要給每個政治局常委都登一個小傳,他卻始終不同意登自己的小傳。但是,當遇到關系黨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時,他從不退縮,挺身而出;遭受到打擊時,他又能遇變不驚,泰然處之。
90歲的陳云去世后,留下的遺物是:三卷 《陳云文選》、少量存款、上百盤評彈磁帶和對子女的教誨。陳云有5個子女,均受過高等教育。他對子女的教育,一行無言之教,二抓問題,并且抓出結果。陳云對子女的教育有兩個原則:一是讀好書;二是做好人。陳云告訴孩子們說:“你們若是在外面表現不好,那就是我的問題。”有一次,他的小兒子陳方為買腳蹼,從生活秘書石長利手中要錢超出預算。陳云知道了這事,叫來陳方,父子的對話開始了:“你從哪兒拿的錢?”“石頭 (石長利)那兒。”“石頭哪來的錢?”“你的工資。”“我的工資誰給的?”“人民給的。”“人民給我的工資,你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兒子,你是我爸爸。”……簡短的對話后,陳云鄭重地說:“記住,節約一分錢也是節約人民的錢,我今后看你的行動。”
彭德懷 在級別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帶個好頭
1930年夏,彭德懷帶領紅五軍轉戰鄂東南,由于戰事頻繁,加上生活艱苦,他的身體日漸消瘦起來。
警衛員看到這種情形很是焦急。有一天,他暗地里讓炊事員下了一碗湯面端到了彭德懷面前。看到面湯里還有幾片豬肝,彭德懷問:“哪里來的?”“我看到你連日熬夜操勞,怕身體拖垮了,特地請炊事員做的。”警衛員回答。
彭德懷聽后,非常嚴肅地說:“誰給你這個權力?我一再強調,紅軍官兵平等,當官的不能搞特殊!”
警衛還想再解釋,彭德懷猛地站起命令道:“不要說了!你快給我送回去!”炊事員連忙過來打圓場:“軍長,面已做熟了,不吃也是浪費,還是吃了吧!下不為例就是了!”
“不能就是絕對不能!這個先例決不能開!否則就不能說服人。我彭德懷鬧革命不是為個人吃好的,如果只為享福,我就呆在國民黨里,享受好吃好喝的了!”說完,他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缸子掉在了地上。
炊事員看到軍長怒氣沖天,頓時不敢吱聲了。過了一會兒,彭德懷才緩緩地說:“同志哥,你將這碗豬肝面送給重傷員吃吧。”轉頭又批評小張:“以后約法三章,誰也不準違犯。”
1955年,身為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到某軍事院校視察工作,他的侄子彭起超恰好也在此學習。匯報會上,彭德懷知道該學院要給侄子授予中尉軍銜時,板著臉對院長說:“起超的軍銜請你們再考慮一下,我的意見是授予他少尉軍銜比較合適。”
院長連忙解釋說:“這是通過群眾評議后黨委審批的,他1945年參加革命,沒有特殊照顧。”
彭德懷說:“根據他的表現和德才情況,我看還是定少尉吧。”
學院采納了彭德懷的意見。為此,侄子老大不高興。彭德懷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在級別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帶個好頭。”
1956年秋天,彭德懷到一個著名的風景區開會。當得知一些漂亮的小洋樓是專給高級干部準備的,而且多數一年到頭都空閑著時,彭德懷半夜起來,圍著那些長年空著的小樓,不停地轉著看了很久,越看臉色越沉重。
離開景區時,他語重心長地對負責人講:“有些人硬要把我們往帝王將相的位置上推,還怕人家不知道,在這兒修了當今帝王將相的庵堂廟宇咧!你們也許是真心實意地尊重我們,但我也要真心實意地告訴你們,我們不是帝王將相!你們這樣搞,人們看到這些長期關閉的房子,會怎么想?不罵娘才怪!”
周恩來 深入群眾,扎根于群眾中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國后,立即到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同時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那時,由于各地黨組織遭到了敵人的嚴重破壞,許多黨員為躲避敵人的追捕,分散到了各處,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周恩來時刻惦念著這些同志的安危,為了保存和聚攏這些被打散的革命力量,他花費了很多心血去尋找。漸漸的,有不少被打散或失去組織關系的同志到上海來找黨中央。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無論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時間親自和這些同志談話,了解他們的實際困難,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在談話中,他從政治形勢、黨的任務、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的關系、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直到具體工作應怎樣展開等,談得十分詳細透徹,使同志們感到了溫暖,受到鼓舞。周恩來還經常叮囑組織部的同志:“干部是革命之本。沒有干部,就沒有革命的事業,更沒有革命的勝利。關心、愛護、教育干部,就是對革命事業的關心愛護,這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
在白色恐怖下,周恩來是國民黨反動派追捕的重要對象,而且認識他的人也比較多,特別是黃埔軍校學生和國民黨上層中的一些人。面對如此復雜艱險的環境,周恩來冷靜機智,不停地變換姓名和地址。中央組織部的秘密機關設在上海靜安寺附近。他有時早晨五六點鐘,晚上是十點以后,甚至半夜一兩點鐘都到那里去,閱讀文件,聽匯報,解決問題。他對上海的街道布局也很了解,出行盡量少走大馬路,多穿小弄堂,很少搭乘電車。他通常裝扮成商人,后來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黨內很多人都習慣叫他 “胡公”。
為保護革命力量,使多數同志能夠適應新的條件下的斗爭,周恩來根據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提出了開展秘密斗爭要 “職業化”和 “社會化”的重要原則,提出深入群眾,扎根于群眾之中。他指出,黨組織要生存,革命力量要發展,就要分散地深入到群眾中去,流落的黨員不到群眾中去是沒有出路的。實踐證明,周恩來這些黨的建設的思想和原則,對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延安整風時,周恩來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評價說:“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
胡耀邦 要靠實事求是吃飯,不要靠摸精神吃飯
1977年12月15日,中央組織部機關門前鞭炮齊鳴。辦公樓西大門上貼出了 “熱烈歡迎胡耀邦同志來中組部任部長”的醒目標語。
到中組部后,胡耀邦就明確提出,今后的工作重點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他在中央組織部任職13個月,平均每天處理的副廳、地委書記以上干部的申訴信就有33封。最多的時候一天處理來信近200封。胡耀邦說,他過去在對人的處理上也犯過錯誤,后來想起這些就感到非常內疚。所以,他到中央組織部后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平反和處理冤假錯案上。
中組部的工作一鋪開,胡耀邦就整天忙得寢不暖席。那年胡耀邦已經64歲,可是為了重建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的組織路線,他以驚人的毅力,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中午,他總是自己拿著飯碗到食堂,和干部職工一起排隊打飯,吃完飯回去便躺在會議室的長沙發上看人民來信。
在中組部一年多的時間里,胡耀邦頂住各方壓力,每天和十幾個人談話,每周閱讀的來信足有一麻袋。他一邊看一邊感嘆,為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鳴不平,為我們國家這么大的悲劇而扼腕嘆息。他說:“凡是一切不實之詞,只要是冤假錯案,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他還說:“我們要靠實事求是吃飯,不要靠摸精神吃飯。一句話,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么人批的、定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