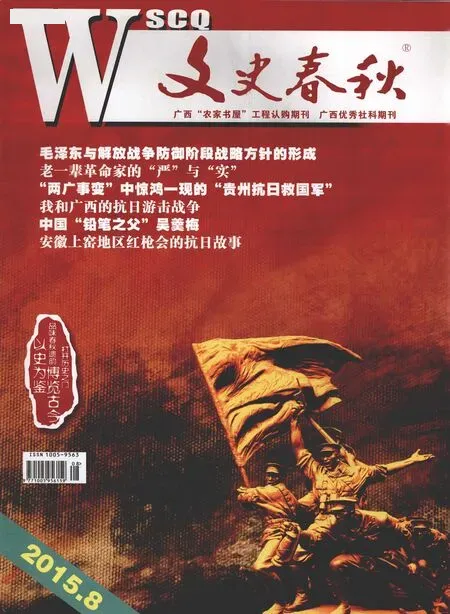賀州韓愈《鳶飛魚躍》摩崖石刻考
●熊開闊
賀州韓愈《鳶飛魚躍》摩崖石刻考
●熊開闊

廣西賀州市昭平縣黃姚古鎮文明閣天馬山上有一韓愈 “退之”款 《鳶飛魚躍》摩崖石刻。韓愈是否曾到過黃姚鎮,已無從稽考,但他的墨跡 《鳶飛魚躍》出現在黃姚鎮,卻是不爭的事實。
筆者通過對黃姚韓愈 《鳶飛魚躍》摩崖石刻以及相關史料的研究,并與陽山縣 (今屬廣東省清遠市,韓愈曾被貶為陽山縣令)幾處 《鳶飛魚躍》墨跡進行對照,認為今存黃姚古鎮文明閣天馬山韓愈 “退之”款 《鳶飛魚躍》摩崖石刻,是清朝道光咸豐年間由廣西柳江縣名士覃少海拓自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陽山斗山書院 《鳶飛魚躍》碑刻的一處拓本摩崖石刻,與現存于陽山韓愈紀念館內清光緒年間陽山縣縣令肖炳坤所臨摹的原碑同為一塊,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鳶 (老鷹)飛魚躍,語出于 《詩經·大雅·旱麓》:“鳶飛戾天,魚躍在淵。”孔穎達疏:“其上則鳶鳥得飛至于天以游翔,其下則魚皆跳躍于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所得,化之明察故也。”后以 “鳶飛魚躍”謂萬物各得其所。
黃姚鎮文明閣 《鳶飛魚躍》摩崖石刻,由 “鳶飛魚躍”四字、落款以及梁端章 (清光緒副貢,黃姚古鎮見龍亭祠門聯作者)楷書題跋等三部分組成。整幅摩崖石刻寬148厘米,高45厘米,為右讀橫書,四字陰刻行草,字體遒勁莊重,外顯生動之形,內含剛勁之神,刻工十分精妙。“鳶飛”二字猶如雄鷹振翅欲飛;“魚躍”二字如淵中之魚,逆水而躍,其破水上串的美,令人震撼。落款為 “退之”二字,豎寫草書,二字結合,像一條被阻擋去路的蚯蚓,蜿蜒曲屈,不能前行只能 “退之”,或許這正是這位大文豪被貶為陽山縣縣令時心境的真實寫照。彼時的韓愈,多么希望自己能夠像一只矯健的蒼鷹,自由自在翱翔天際,像魚兒一樣在清淵嬉戲,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如鳶在天,如魚得水。或許,韓愈雖貶謫嶺南蠻荒之地,每天以蚯蚓為餌,垂釣溪流,悟性極高的大文豪通過對釣魚所用的魚餌蚯蚓細致入微地觀察,悟出了 “蚯蚓退之”,用在自己的書法落款上,有“退避三舍,以退為進,是為退之”之意。
對于韓愈的書法造詣,宋代朱文長如是評價:“退之雖不學書,而天骨勁健,自有高處,非眾人所及也。”在賀州這塊 《鳶飛魚躍》摩崖石刻中,“天骨勁健”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韓愈 (768—824),字退之,世稱韓昌黎,唐代著名詩人、文學家。唐德宗貞元十八年 (公元802年),韓愈晉升為監察御史,在任不過兩個月,因遭權臣讒害,被貶為連州陽山縣縣令。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公元805年)夏秋之間,韓愈離開陽山,任江陵法曹參軍。韓愈三年任職陽山縣令,甚有政聲。
據1397年刊印的 《陽山縣志》記載,韓愈墨跡 《鳶飛魚躍》原刻在廣東省陽山縣《韓公釣磯》前。《韓公釣磯》位于該縣城東塔溪之右 (今陽山中學內)。據記載,韓愈被貶陽山縣令時,常在此以蚯蚓為餌釣魚,至明代,此處建有韓公釣臺。由于時間久遠,此前的韓愈 《鳶飛魚躍》題刻已被毀。到了清乾隆四十七年 (公元1782年),邑司訓何健得韓愈手跡于陽山士人家,重摹勒石 (碑刻),置斗山書院中堂壁,健有跋,后移至韓文公祠側,今已不存。
在廣東陽山,現存韓愈 《鳶飛魚躍》石刻有三件,其一為清陽山縣縣令潘元音于乾隆五十七年 (公元1792年)刻于陽山縣陽城鎮北約1千米的賢令山打字巖,為一處摩崖石刻。另外兩個為碑刻,均為清光緒年間陽山縣縣令肖炳坤所摹刻,一通為陰刻,一通為線刻,并附有詩及詩序,原石刻存韓公釣魚臺韓山書院廳壁,今存陽山韓愈紀念館內。
在黃姚鎮文明閣天馬山 “退之”款的 《鳶飛魚躍》摩崖石刻的左側,有清光緒年間副貢梁端章題寫的后跋。茲錄跋如下,以資考證:
此韓公宰陽山時書也神奇遒勁古意盎然覃君少海見而寶之用搨以歸人爭摹仿紙貴一時第未經刻石恐剝蝕于風霜戌午春同人莫君臧辰義甫覃君少海古君洽齋善齋小池光庭郭君齊之蒙君民礎勞君仲云李生嚴谷達民吾弟平甫紫階等列觴于此酒酣談妙異想天開俯仰上下隨在悟化機之洋溢因而發思古之幽,刻昌黎之遺墨青山無恙大筆常新懸諸終古而不磨矣
后學梁端章敬跋
從 《陽山縣志》和該摩崖石刻梁端章題跋,不難看出,原刻在 《韓公釣磯》前的《鳶飛魚躍》石刻,至遲到明代,就連同 《韓公釣磯》都已被毀。到清乾隆四十七年 (公元1782年),當時的陽山縣邑司訓 (明清時期在州、府、縣設置訓導,為縣學教諭)何健得到韓愈 《鳶飛魚躍》手跡后,摹刻在陽山縣斗山書院中堂壁上。名士覃少海——新桂系之第八十四軍軍長覃連芳 (1894—1958)中將之曾祖父,“見而寶之,用搨 (搨同拓)以歸”的應當就是何健置于斗山書院中堂壁上的 《鳶飛魚躍》碑刻。梁端章題的后跋里的 “戌午”,應為誤刻,實為 “戊午”(天干地支紀年無 “戌午”年)。在文明閣上山的路旁的 《重修文明閣記》碑刻有云:“夫世間無不朽之物,惟修復循環,可以維持于不敝,戊午春,風日清美,余與莫臧臣、覃少海、李嚴谷、李陪芝、莫義甫、蒙民楚等因小西湖、鳶飛魚躍之刻,殤會于此。”落款為:光緒十七年,辛卯副貢梁端章撰,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吉旦立。可見,梁端章后跋石刻中的“戌午春”當為誤刻,而非梁氏誤寫。查自清乾隆四十七年 (公元1792年)至清光緒十七年 (公元1891年)年間,只有兩個戊午年,其一為清嘉慶三年 (公元1798年),其二為清咸豐八年 (公元1858年)。從該碑刻的后跋所記的 “戊午春”以及覃少海在世年代推測,“戊午春”,只能是清咸豐八年,即公元1858年春天,而此時距離乾隆四十七年 (公元1782年)何健得到韓愈手跡,重摹勒石(碑刻),置斗山書院中堂壁,只有76年。
同時,通過與何健后跋款 《鳶飛魚躍》板墨書匾進行對照,發現從字體和結構上看,黃姚 《鳶飛魚躍》摩崖石刻與墨書匾極為相似,筆者認為:兩幅書法作品當出自同一母本,只是一為勒石,一為臨摹在木板上而已。而黃姚 《鳶飛魚躍》摩崖石刻與陽山縣賢令山打字巖 《鳶飛魚躍》摩崖石刻又有所區別,尤其是兩幅石刻的 “魚”字,黃姚石刻的“魚”字更加剛勁有力,棱角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