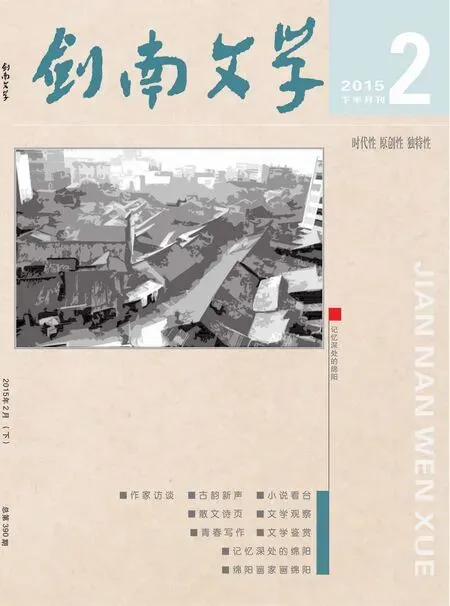自由與專一——簡談《詩經》中的愛情觀
■李 博
《詩經》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無論其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都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愛情詩,既有對戀愛自由的追求,又有對感情專一的贊頌,開啟了中國愛情文學的先河。在對這自由與專一的愛情觀的分析中,我們或許可以發掘其潛在影響與價值。
要談《詩經》中的愛情觀,首先我們要確定愛情詩的數目。學界大致認為在《詩經》中反映愛情的詩作約有百余首,占詩歌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純粹”的愛情詩為52首,多為描寫男女間的愛慕、約會等內容,而其余多以家庭婚姻為主題,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著愛情內容。以下將從自由的愛情觀、專一的愛情觀以及愛情觀的影響與價值等三個方面來進行闡述。
一、自由的愛情觀
《詩經》中自由的愛情觀出現,是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的。當時社會人口較少,各個諸侯國出于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通過鼓勵生育來增加勞動人口,因此對中下層男女之間自由戀愛交往不予限制。《周禮·地官·媒氏》中說:“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由此在《國風》中出現了大量歌頌自由戀愛的詩作。
在《詩經》中,青年男女無論是在城市中偶遇,還是相約在一起出游,他們的情感選擇是自由無束的。如《鄭風·野有蔓草》就描述了一對男女在田野間一見鐘情的愛情故事。“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主人公在露珠剔透的田蔓中行走,突然邂逅一位清婉的女子,兩人一見鐘情,一生共好。自由的田間環境,美好的戀愛理想,成就了這個愛情故事。這也是自由的環境下男女自由戀愛最為直接的反映。當然,自由戀愛不僅僅是你情我愿、一見鐘情。自由的愛情觀還表現在《鄭風·褰裳》中女主人公戀愛受挫時所表現出的獨立的人格:“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你如果不思念我,難道就沒有其他人嗎?言外之意就在于我有相愛的自由,也有放棄的自由。愛情有聚有散,這種敢于放棄的自由是難能可貴的。這些詩作從正面描寫了當時戀愛自由的狀況,是《詩經》中自由戀愛最直接的反映。當然,也有少數表現戀愛不自由的詩作,如《鄘風·柏舟》中女子對母親干涉自己自由戀愛的控訴:“母也天只,不諒人也!”母親、蒼天,你們為什么不體諒我的心情!這種反映戀愛不自由的詩作雖然不多,但更能表現出當時青年男女對戀愛自由的渴求。文學作品往往是一個時代最為真實的反映。與后世如《孔雀東南飛》等通過悲苦的故事表現對自由愛情的追求相比,《詩經》中的愛情詩作對自由戀愛進行了大量積極正面的描寫。男女間相聚的快樂、一見鐘情的喜悅,是當時較為自由的社會氛圍以及“禮教”未及的直接反映。
二、專一的愛情觀
《詩經》中的愛情詩除了對自由愛情的歌頌,還有對專一愛情的渴求。《詩經》第一篇《關雎》,雖然被歷史上許多儒學家認為是表現正妃之德的詩作,但根據人正常的情感心理上來看,我認為它就是一首表現 “男子思女”的愛情詩作。從“寤寐求之”到“輾轉反側”,男子對女子的思念以及專一形象地展現在我們眼前。而那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更是令多少青年男女為之感動,由此為專一的愛情奮斗終生。它實際上出自《鄴風·擊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個隨軍遠征的男子當年對妻子的誓言。主人公在外出征,思念自己的妻子,回想起當年的誓言:無論生死聚散,我都會伴你終老。這種對愛情的生死不棄可以說是專一的愛情觀最為忠實的反映。
對愛情專一的追求在一些家庭婚姻詩中也有所表現,多反映在“棄婦詩”中。在此可以對在高中學習過的《衛風·氓》進行簡要分析。《氓》描述了女主人公由訂婚、結婚到被男子遺棄的故事。從男子“氓”的“來即我謀”到“以我賄遷”,女子在這段時間里是對美好愛情的期待。但結婚后 “三歲食貧”、“士貳其行”,她得到的是辛苦的生活和男子不忠的行為,“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最終女子的“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使她與這段感情的徹底決裂。《氓》通過對一個棄婦的描寫,譴責了男子用情不專的行為,從反面表現出女子對愛情專一的渴望。
然而,愛情是存在于男女之間的,那么對愛情忠貞專一的愿望當然也為男子所看重。《鄭風·出其東門》就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出其東門,有女如云。雖則如云,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鄭國東門外就是當時溱、洧之濱,是當時青年男女出游之處,在《鄭風·溱洧》中對此有所描述。男主人公在東門外看到成群的女子,但他都不為所動,因為“匪我思存”。他思念的是那位素衣女子。這充分表現出男子對心上人淳樸的專一之情。
自由與專一是《詩經》中愛情觀最主要的兩方面。它們在表面上看似矛盾卻又是愛情中必不可少的。正如徐儒宗先生所言:“脫離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愛情去強調婚姻上的專一,勢必陷入“從一而終”的貞節觀念;違背互相忠貞這一愛情道德而侈談戀愛自由,勢必流于泛愛和庸俗的性解放”。愛情要以自由戀愛為基礎,以用情專一、白頭偕老為目的。而《詩經》中的大部分愛情詩就是描述的這種愛情,因而一些詩句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在今天還散發著不朽的光芒,指引著人們對愛情的追求。
三、愛情觀的影響與價值
《詩經》中以自由和專一為核心的愛情觀對后世的影響首要在于詩歌創作上。《詩經》作為古代文人的必讀書目,文人們言必稱“詩”,其愛情觀自然影響著后世的愛情詩創作。無論是漢樂府《上邪》中“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與劉蘭芝的愛情悲劇,還是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李香君對侯方域經年不變的感情,都可以看到《詩經》中自由和專一的愛情觀。
文學作品是一個時代的反映。《詩經》中自由與專一的愛情觀特別是自由的愛情觀對研究西周至春秋的社會歷史有著很重要的推導價值。可以從中對當時自由寬松的社會環境、自由交往的社會習俗以及“禮教”的態勢進行某些挖掘。
非如朱熹在其《詩經集傳》里“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的評價,《詩經》里的愛情詩表現出的自由專一的愛情觀恰恰是男女之間正常戀愛婚姻關系的體現。特別是專一的愛情觀區別于當時上層社會的“三妻四妾”的一夫多妻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反映。
對于當今社會而言,《詩經》中自由的愛情觀可能已經普及。但古人那種淳樸的專一之情,就如《東門之外》那位男子一心想念自己樸素的心上人的感情,希望可以對當今青年男女功利化的婚姻與愛情觀產生某種凈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