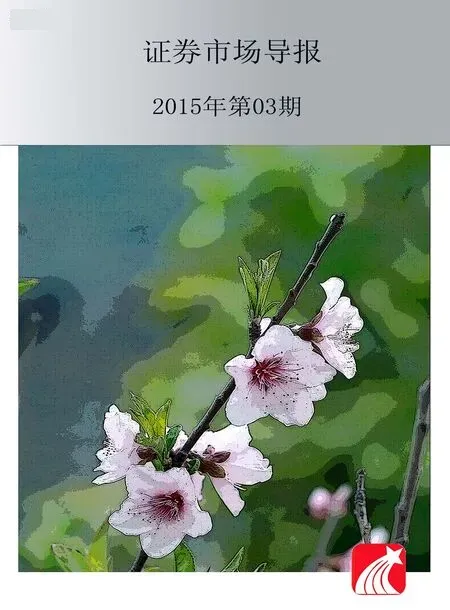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實施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來自中國A股市場的經驗證據
張清瓊
(安徽大學商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引言
為了規范注冊會計師的執業行為,提高執業質量,我國財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發布了新的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體系,并要求自2007年1月1日起在所有會計師事務所施行。該準則體系最大的亮點是全面貫徹風險導向審計的基本原則。然而,風險導向審計自誕生以來就飽受爭議,尤其是本世紀初國外爆發的一系列審計失敗案件,將風險導向審計推向了風口浪尖。我國自新審計準則實施以來,也出現了一些觸目驚心的審計失敗案例。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運用能否在審計效率和審計質量之間實現動態的平衡,以及我國新審計準則的實施會對審計質量產生的影響理應成為研究重點。
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實施后,在審計效率提高(韓曉梅、郭威,2011)[6]的同時審計質量有何變化?是出現審計效率和審計質量的雙重提高(Eilifsen,Knechel and Wallage,2001)還是會由于對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運用不當而導致審計質量下降?基于我國當前的審計環境,本文從審計師所采用的審計理念與方法的角度實證研究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對審計質量的影響,以期為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實施對審計質量的影響提供經驗證據。
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是對傳統風險導向審計的一種改進,它更加強調對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和外部風險進行評估。國內關于風險導向審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06年前后,且多從理論分析的角度闡述審計風險模型的缺陷(陳志強,2005;王會金、劉瑜,2006)[7][8]、風險導向審計的理論缺陷與現實困境(秦榮生,2005)[9]等。張圣利(2011)以審計意見做為審計質量的替代指標,研究了新審計準則實施后我國審計質量的變化,結果發現新審計準則的實施使相同的盈余管理幅度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概率增大,從而作者認為新審計準則的實施提高了審計質量[10]。與張圣利的研究角度不同,本文以盈余質量來衡量審計質量的高低,這是因為非標審計意見的出具受到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而盈余質量的高低直接受到審計師的獨立性以及審計師所采用的審計技術和方法的影響,因而更能體現審計師的審計質量。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提高審計質量的積極影響
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是為應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日益復雜的組織結構和交易事項以及不斷增長的法律訴訟風險所開發出來的一種審計方法,是對傳統風險導向審計的改進。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注重對企業經營風險的關注和評估。一般認為,審計質量愈高,審計風險就愈低,審計風險只有控制在允許的范圍內,審計質量才合格。并且,有效地對審計風險進行評估與控制進而又為提供高水平的審計服務提供保證,如此就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11]。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從審計風險的角度對審計質量加以關注,且以風險為導向對審計質量進行控制。在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下,審計風險存在的高低與被審計單位財務報表錯誤和舞弊的程度相關,審計質量與審計風險的高低也相關。對于會計師事務所而言,如果審計師能夠有效地將審計風險控制在合理的水平,這也就意味著審計工作質量得到基本保證;相反,如果審計質量不高,也會導致潛在或現實的審計風險。
在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下,審計師對被審計單位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由此確定一個合理的、可接受的審計風險水平。會計師事務所或注冊會計師愿意承擔的風險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審計質量的高低,其愿意承擔的審計風險水平越低,對審計質量的要求也就會越高。可見,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方法的實施過程,實際上就是審計風險控制過程,也是提高審計質量、達到最終審計目的的一個質量控制過程[12]。雖然不同的審計模式都以提供最高審計服務質量為最終目的,即為被審計單位的財務報表信息的可信性提供合理保證,但是,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是以風險理念為基礎、以審計證據為驅動,強調全面風險評估的一種審計程序與方法[1]。
較之于以往的審計模式,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提高審計質量:一是審計程序重心前移,以風險評估而不以審計測試為重心。這種重心的前移能有效發現被審計單位的高風險領域,防止審計過量或審計不足。現代企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環境,企業外部的市場風險、技術風險、監管風險等都會對企業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通過對被審計單位經營風險進行評估,在重大風險領域投入更多審計成本,可以從總體上控制審計風險,提高審計效率。二是強調從宏觀層面上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以充分識別和評估會計報表重大錯報的風險,這不僅緊扣審計工作的核心,而且與審計目標責任定位緊密相連,有利于注冊會計師履行審計責任,實現審計目標。諸多審計失敗案件,一個重要原因是注冊會計師對被審計單位所處的行業環境、經營狀況、發展前景以及被審計單位的治理層和管理層的品德、能力等了解不夠,從而導致審計不到位出現審計失敗。三是改進審計業務流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審計路線,可增強審計程序的實施效果。
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糾正了人們對風險導向審計在認識和實踐上的偏差,有利于注冊會計師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質量。在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的指導下,只要注冊會計師能夠全過程、多方位評估風險水平,嚴格遵守審計準則,保持應有的職業懷疑,就應該而且能夠發現客戶報表的所有重大錯報,從而能夠提供更高質量的審計服務。
二、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提高審計質量的不利影響
然而,許多理論界與實務界人士對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是否能夠有效應用并提高審計質量表示出懷疑和擔憂。部分研究者甚至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審計風險模式由制度導向審計模式發展成為風險導向審計模式,這種審計模式的嬗變可能使審計由一門高尚職業淪為一種唯利是圖的生意[13],風險導向審計的運用并不意味著審計質量的提高。
首先,在理論上,現代風險導向審計重點強調企業的經營風險,在方法上又主要關注財務報表重大錯報風險,而被審計單位財務報表重大錯報風險并不完全由經營風險決定,這勢必會導致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理論與方法體系嚴重脫節,難以有效地指導實踐,審計質量也就無法顯著提高[10]。在我國,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理論體系和實務操作尚不夠成熟和完善,審計師對如何有效評估審計風險、實施審計程序以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尚不明確,實施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反而容易增加注冊會計師的過失。
其次,審計質量不高,甚至審計失敗發生的原因也并非純粹是因為審計師所采用的審計技術方法所導致的,它還與審計環境中相關利益制度的缺陷密不可分。風險導向審計的核心是風險評估,且重點強調了審計師在執業過程中的職業判斷,那么影響評估結果的關鍵因素就是審計主體的風險偏好。而相關利益制度的缺陷是導致審計主體對風險非理性偏好的誘因,這使得審計人員在社會責任和執業利益上無法統一,從而會影響風險導向審計的有效實施[14]。
再次,審計師可能面對的未來法律訴訟風險與審計質量也密不可分。風險導向審計產生于美國高法律訴訟風險環境下,在高法律風險的外部環境中,審計人員常常會被“卷入不愉快的責任訴訟糾紛之中”[2]。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中,獨立審計可預見的法律風險高、違規成本大,其理性選擇應是努力提高審計質量,以盡可能降低法律風險[15]。如果一個國家法律對審計風險責任的要求極低或執法效率低下,那么,即使審計結論極不可靠也未必會導致實際的審計風險[16]。我國審計職業界所面臨的法律風險很低,且對會計師事務所及注冊會計師的違法行為以行政處罰居多,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審計師認為審計風險可以接受,也可能在審計質量相對較低情況下出具標準意見的審計報告。
最后,即使外部法律風險較低,若存在一個相對有效的審計需求市場,市場也能通過自我有效的制度安排激發高質量的審計[17]。盡管2005年我國實行了會計師事務所的脫鉤改制,但目前的審計市場仍主要受政府管制,事務所的政治關聯嚴重影響著審計服務質量。由此可見,即便實施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本身可以促進審計質量的提高,但由于我國市場的各項制度安排不僅不會激發高質量的審計,而且還會存在“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18]。
根據以上制度背景及理論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競爭性假設:
H1a: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施行提高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
H1b: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施行降低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
樣本選擇與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本文以2003~2010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初選研究樣本,然后,從初選樣本中剔除了以下公司:(1)金融類上市公司,原因是金融類上市公司的生產方式與其他行業公司存在顯著不同;(2)主要變量數據缺失的公司。最終確定11082個樣本數據。樣本分布如表1。本文財務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會計師事務所信息來自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2003~2010年公布的《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前百家信息》。為了控制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性變量進行了Winsorize處理。
二、模型設計及變量定義
1.審計質量定義
被審計過的財務報表中可操控應計的大小一方面反映了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獨立性對審計師的要求。因此,經審計的財務報表中可操控應計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出審計質量的高低。國內外大量研究采用盈余管理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19][20]。已有研究發現,截面Jones模型估計出的可操控性應計數能夠有效地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3]。同時,Kothari發現加入業績控制指標的Modified Jones Model可以較好地計算公司的可操控性應計數。因此,本文采用Kothari(2005)的方法計算可操控性應計數,并對可控性應計取絕對值(|DA|)來衡量審計質量。Kothari的模型如下:


表1 樣本分布
其中,TAijt為j行業i公司第t年的總應計,它等于公司當年凈利潤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ΔREVijt為當年營業收入相當于上一年度的變動額;ΔARijt為當年應收賬款相當于上一年度的變動額;PPEijt是本年固定資產凈額;ROAijt是總資產收益率,等于公司當年凈利潤與當年總資產之比。另外,以公司上年末總資產對模型中所有變量進行標準化。
可操控性應計(DA)的計算過程是:首先,分行業分年度對模型(1)進行OLS回歸取得回歸參數,同時,仍然保留截距項以消除異方差的影響;然后將參數代入模型(2)中計算得出非可操控性應計數(NDA);最后將計算出的非可操控性應計數代入模型(3)估計出DA。
2.研究模型
已有研究表明,資產規模(LnAsset)、資產負債率(Lev)、收入增長率(Growth)、現金流量(Cfo)、上市年限(Age)、盈余管理行為(EM)等會對公司的可操控應計額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4]。因此,本文從企業層面上對這些因素進行控制,參照chen et al.(2011),建立回歸模型(4)反映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施行對審計質量的作用。模型中的具體變量定義如表2。

表2 變量定義

表3 風險導向審計施行前后|DA|的變化

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單變量檢驗
本文首先對現代風向導向審計施行前后|DA|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做了單變量檢驗,分析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的施行是否提高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后,在全樣本中,可控性應計絕對值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從0.078、0.052上升到0.1200、0.058,且在1%水平上顯著;在“國內十大”(排名在“四大”之后的國內十大會計師事務所,下同)和“非TOP”(除四大和國內十大之外的其他所,下同)中,可控性應計絕對值的均值和中位數也均顯著上升;但是在“四大”中,可控性應計絕對值的均值和中位數無顯著變化。可控性應計絕對值的提高說明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之后被審計單位的盈余質量明顯變差,即審計質量有所下降。但是,這種現象在“國內十大”和“非TOP所”中顯著,而在“四大”中不顯著。
二、變量相關性分析
表4報告了變量間的相關系數。|DA|與Switch顯著正相關,說明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之后,經審計報表的可操控性應計利潤水平提高,審計質量降低。另外,|DA|與Age、Cfo、Growth、Lev顯著正相關,說明上市年數越長、銷售增長越快的公司,越有利用可操控性應計利潤進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DA|與LnAsset、EM則顯著負相關。同時,變量間的相關系數最大的僅為0.271,說明變量之間并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4 相關系數
三、多元回歸分析
在回歸分析中,各變量間的VIF均不大于5,因此,可以認為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從模型總體看,盡管模型的調整R方相對較低,但整體顯著性水平較高,各回歸模型P (R2)均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性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回歸模型在整體上是合理的。由于事務所規模、聲譽、行業專業化等因素會對審計質量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本文首先對全樣本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然后再分別對“四大”、“國內十大”和“非TOP所”進行回歸分析。
表5為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對審計質量影響的多元回歸結果。從表中可看出,在全樣本中,Switch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在我國施行之后,整體事務所的審計質量明顯下降。同時,在“國內十大”和“非TOP所”樣本中,Switch的回歸系數也顯著為正,但是在“四大”所樣本中,回歸系數雖然為正,但不顯著。這說明現代風向導向審計施行后,“國內十大”及“非TOP所”審計質量顯著降低,而四大審計質量無顯著變化。

表5 多元回歸結果(2003~2010年)

表6 多元回歸結果
本文認為這種結果出現的原因可能是:風險導向審計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由“四大”開發出來,在2007年財政部要求國內所使用風險導向審計之前“四大”就已將其廣泛用于客戶的審計實務中,因此,在2007年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前后“四大”的審計質量并無顯著變化。而“國內十大”及“非TOP所”審計質量顯著降低,這可能是因為目前我國正處于政治、經濟轉型期,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2007年施行風險導向的審計準則后,注冊會計師掌握風險導向審計的理念和方法的時滯;再加上本土事務所自身對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未能有效運用等因素的影響,因而導致了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后本土事務所審計質量的整體性下降。
四、進一步分析
由于財政部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要求所有會計師事務所自2007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現代風險導向審計,因此我們選取2006年為基準,分別比較2007年及以后各年度的盈余管理相對于2006年的變化情況(由于篇幅有限,此處只列出主要變量的回歸結果)。表6為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后的每個年份與2006年的多元回歸結果。從表6中可看出,無論是“國內十大”還是“非TOP所”,Switch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表明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之后,其審計質量明顯下降。但對于“四大”所,審計質量則無顯著變化。將2006年的盈余管理數據替換成2005年的以后,僅在四大樣本中,Switch的回歸系數符號有所變化,但總體不顯著,其余結果與表6一致。回歸分析的結果進一步驗證了本文的研究結論。
為了驗證結論的穩健性,我們還以異常性營運資本(AWAC)來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5][21](Carrey and Simnett,2006;蔡春、鮮文鐸,2007)。該替代變量的計算公式為AWACt=WCt-WCt×(St/St-1),其中AWAC為異常性營運資本,WC=(流動資產-現金和短期投資)-(流動負債-短期借款),S為主營業務收入。我們同樣選取2003~2010年的數據作為樣本,將樣本數據代入回歸方程(1),得到樣本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從表7我們可以看到,在實施現代風險導向審計以后,不區分大小所的全樣本下,事務所客戶的異常性營運資本整體上出現了上升,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具體來看,“四大”的客戶其異常性營運資本雖有所變化,但并不顯著;而“國內十大”和“非TOP所”的異常性營運資本均顯著上升,且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這一結論和此前的檢驗一致,說明我們的結論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表7 多元回歸結果(2003~2010年)
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的分析研究發現: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后,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在整體上有所下降;進一步研究發現,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施行后,“國內十大”及“非TOP所”的審計質量有顯著降低,而“四大”審計質量并無顯著變化。本文認為這種現象的存在可能與我國的相關監督機制不完善、監管體系不健全、法律風險不高以及事務所自身并未迅速掌握風險導向審計的理念和方法,并未能有效運用現代風險導向審計等因素有關。
從理論上來看,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代表著審計模式的最新發展方向,比以往審計模式具有更大的優越性,能夠降低審計風險、縮小審計期望差距。但是,從目前實際情況來看,由于外部監管不利、法律訴訟風險不高、審計師對風險導向審計的運用還處于起步階段等原因,面對既定的審計風險,審計質量難以得到提升。因此,我們建議會計師事務所應當加強對現代風險導向審計運用的研究,注重提升審計師的綜合素質,通過職業培訓提高審計師的專業技能,提高運用風險導向審計的能力。審計市場監管者應當完善監管機制,鼓勵事務所之間進行同業互查等手段來提高審計服務質量和水平。此外,在風險導向審計運用的過程中,經濟環境和會計準則處于不斷的變化當中,可能會由于遺漏變量對本文的研究結論造成一定的影響,如何減弱上述影響將是本文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