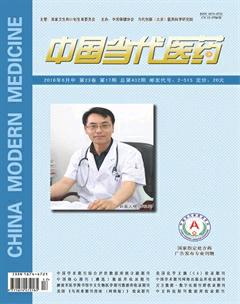“下學而上達”的歷程轉變
李永暉
【摘 要】 《大學》和《中庸》都為儒家在“下學而上達”的道路上提供了思路和指導,兩者所共同強調的地方在于都把政治理想的實現建立在經過道德規范后的家庭倫理及社會秩序能夠井然有序和個人道德水平能夠不斷提升并能夠推己及人的基礎之上。區別在于《大學》的著眼點在人,從個人的“修身”出發,最終達到“明明德”的境界;《中庸》則更多地關注人力所不能及的“天”,認為人后天的成就“因其材而篤焉”。《大學》止步于道德,《中庸》則更進一步,從道德上升到了形而上的本體的高度。
【關鍵詞】誠;大學;中庸;儒家
《大學》中,“誠”主要是作為一個動詞以“誠其意”的面目出現[1],而在《中庸》當中“誠”字又有所不同,主要是表達一種“誠”的狀態[2]。這個看似細微的差別,實質上體現了《大學》《中庸》這兩篇文章本身在思想上的一些差異。
《大學》《中庸》均源出《禮記》(《中庸》為第31篇,《大學》第42篇),因北宋時期二程的推崇,這兩篇文章開始和《論語》、《孟子》并列,作為儒家學說的基礎讀本,南宋時,經朱熹注釋整理將四本書共同編入《四書章句集注》,該書后成為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唯一官方注釋。[3]
一
《大學》《中庸》所共同強調的地方在于兩者都把政治理想的實現建立在經過道德規范后的家庭倫理及社會秩序能夠井然有序和個人道德水平能夠不斷提升并能夠推己及人的基礎之上,與此同時,實現政治理想亦非其最終追求。正如《論語·憲問篇》中所說的“下學而上達”這句話所表達的那樣,實施具體事務(甚至像治理國家這樣的大事也一并包括在內)的目的是為了對個人德性的提升有所增益。“外王內圣”作為對儒家終極理想人格的描述,“外王”在更多的時候是“內圣”的必然結果而非先決條件,這與蘇格拉底對“哲學王”的期待是一致的。孔子本人也從未具有王的身份,但這并不妨礙后世儒家將其尊為“圣人”,成為儒家的精神領袖,并被冠上“素王”的稱號。
在這樣一個共同的前提之下,《大學》和《中庸》所表達的思想,或者說為“下學而上達”的這個過程所提供的思路又有所不同。《大學》強調的是一種循序漸進式的道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4]”的思想貫穿了政治思想、家庭倫理、個人修養的各個方面。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5]”則強調了這種路線的施行在身份上并不會因為天子、庶民的差別而有任何差異。假如以自身作為一個起點,從向外的一面來說,這條道路從“修身”開始:“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6]”而向內的一面到“格物”結束:“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7]”通過這種循序漸進的邏輯關系,《大學》使治國和修身這樣兩個本來不在一個層面上的事情共同進入了一個封閉的循環的通路,并在“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之間建立了聯系。從而使儒家思想中將政治理想的實現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這一構想成為可能。
二
“誠”在《大學》中表示表里如一、坦誠而不自欺,這是儒家要求“君子慎獨”的緣由所在,“君子慎獨”則能“誠于中,形于外[8]”。這種內外的高度一致性是儒家道德規范的基礎要求,也是實現道德規范后的基本表現。而在《中庸》當中,“誠”則主要用來表達一種狀態,與另一種狀態“明”相對。盡管兩篇文章中的思想都將內外兩條道路的起點放在了個體自身上面,但是相比《大學》中要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內在標準,《中庸》強調的“至誠如神”卻走向了另一個目的地。簡單地說,《大學》中的“誠”與“不誠”是一個態度問題,而《中庸》中的“誠”卻被推向極致,并開始成為形而上的、具有先驗性的本體的代表:“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9]”《中庸》中關于“誠者”和“誠之者”的表述不僅是在天道、人道上有區別。而且在人與人之間也做了區分:“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0]”這三者中“生而安行”者無疑是符合“誠者,天之道”的,“學知利行”與“困知勉行”都屬于“誠之者”,兩者的區別是在“誠之”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從“利行”、“勉行”的角度來看,在“誠之者”中,即使兩者都是“擇善而固執之者”,先天賦予的“誠”的程度多少也對后天的“行”有著巨大的影響。
如此一來,《中庸》和《大學》開始出現了極大的不同:《大學》強調“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在修身的要求上并不因為其對象身份的改變而改變。而同樣是修身,在《中庸》中就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與“困知勉行”的區別。“生知安行”者,即“誠者”可以“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生來就是圣人。而唯有“至誠”,才可以“盡性”、可以“前知”、可以“化育天地”,達到與形而上的本體合一的境界。雖然《中庸》中也說“及其知之一也”和“及其成功一也”,但問題是對于“人之道”來說,有可能達到“至誠”的境界嗎?連孔子自己也只是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近乎與達到自然是不相等的。不過暫且不論從“人之道”達到“天之道”的可能性是多少,《中庸》為儒家所確立的發展方向就是如此,可以說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也是中國傳統中產生對“天人合一”這一追求的來源之一。
三
其實《大學》《中庸》的不同在兩篇文章開篇第一句中就有所顯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11]”“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12]”《大學》中明明德的重點在“明”,是從人自身發揮理性和智慧的能力這一角度開始,而《中庸》中的“教”卻旨在說明人類智慧的傳遞來源是基于“天命”賦予的“性”而來的。《大學》認可人具有理解認識的能力,《中庸》則認為這種認識能力因“天命”賦予給人的不同而產生差別。“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13]” 人后天所能取得的成就受先天的“材”限制,也受先天的“材”決定,這種先驗的宿命論式的論斷與《中庸》中“誠則明”的思想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大學》的著眼點在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八條目的落腳點無一不在人的身上,人可以從修身開始,通過對自身的不斷提升達到“明明德”的程度;《中庸》則著眼于天,更看重“天命”對人的作用。人所能取得的成就既以先天的“材”為基礎,其成就的大小也受到先天的“材”的限制。和《大學》相比,《中庸》更多的把眼光放到了人力所不能及的“天”上面。
與此同時,在“下學”的道路上,盡管《大學》和《中庸》都強調當個體處在社會的不同等級秩序和倫理關系之間時,行為上應具有差別,但其強調的終點卻有所不同。《大學》中說:“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與外在世界的相處和倫理關系上,《大學》停在了“仁、敬、孝、慈、信”這樣的具體的道德標準上。《中庸》中亦從倫理關系的角度提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者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14]”。但是《中庸》中的倫理并沒有止步于一般意義的道德上,而是上升到了本體的境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15]”甚至從個人擴大到國家的層面時,倫理道德的最終結果也上升到了本體的高度。《中庸》在表達治理國家的理念中,就治國之道,對處在不同倫理關系中的群體分門別類的做了說明:“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16]”但是和《大學》相比,《中庸》在“下學而上達”的道路上顯然是更進了一步,無論在對外在的倫理關系中體現的是哪一種道德,接下來這些道德都要回歸到自身的德性上,其最終的歸宿都是從自身的德性上升到了作為本體的“一”: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17]”從而完成了“上達”的過程。
四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18]”從“誠”和“明”的關系上來說,《大學》中的“明明德”只達到了“明”的境界,而“明”的狀態是后天完成而非先天擁有的。《中庸》則對比“明”更高的“誠”進行了說明。《中庸》中說:“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其中的“明乎善”是要在“誠乎身”之前達到并完成的一個狀態。也就是說,如果人后天要達到“誠”的境地,必須先達成“明”的狀態;反而言之,假如先天已經具備了“誠”,“明”不過是一個隨之而來的結果。《中庸》所說的“誠則明矣;明則誠矣。[19]”并不意味著“誠”和“明”是兩個完全相等的狀態,而是說具備“誠”自然而然就能具備“明”,“誠”是高于“明”的,即使當“明”達到極致以后也能達到“誠”的境界。誠者,因“誠”而“明”,是“天之道”,而自“明”至“誠”的是實行“人之道”的誠之者。對于人來說,除非是天命賦予可以“生知安行”的圣人,就只能走自“明”至“誠”的道路。從這個角度來說,四書中把《大學》放在《中庸》之前,也是有著循序漸進的含義在其中。在儒、道、佛三教合流的趨勢和時代背景下,儒家的學者特地把《中庸》從《禮記》中挑出來,也有對儒家學說中相對缺乏的關于形而上的本體論的部分進行強調和補充的目的在。
對于“生知安行”以外的人來說,“至誠”是一個“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狀態,那么在“學知利行”和“困知勉行”的群體中,“誠”和“明”的關系又是如何呢?事實上,無論是“生知安行”、“學知利行”還是“困知勉行”,當我們假設“行”的前提是“知”的時候,“知”作為人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的高低自然要受到先天“誠”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誠則明”的描述是比較準確的。但是如果以人類的每一次客觀實踐本身都會提高人對客體和外在世界的認識水平這一事實為前提,強調“行”對“知”的作用,“明則誠”就更有道理,因為人確實可以通過“行”來使“知”的能力不斷深化。這樣一來,“誠”和“明”的關系問題實質上可以通過“知”和“行”來進行說明。從“知行合一”的角度來說,在“知”和“行”之間并沒有哪一方能作為絕對的先決條件而存在。“知”和“行”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把這種相互作用放到“誠”和“明”上,也是可以得到解釋的。“誠”作為先天條件制約著“明”的能力,后天環境中的人通過不斷的“明”這一過程也可以使 “誠”的程度得到提升。通過這樣的歷程,最終使“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成為了一個相互作用中的循環回路,而不僅僅是對“誠”和“明”的先后次序進行表述。
參考文獻:
[1] 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M]. 北京:中華書局, 2011.
[2] 劉子健. 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2.
[3] 柏拉圖. 理想國[M].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6.
[4] 王陽明. 傳習錄[M].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5] 陳來. 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M]. 北京:三聯書店, 2009.
[6] 陳銳. 中西文化的振蕩與循環[M].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2000.
[7] 孫希旦. 禮記集解[M]. 北京:中華書局, 1989.
注釋:
[1]《大學》中“誠”字一共出現了8次,其中4處為使役動詞,3處為表示狀態的形容詞,1處名詞。(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準,下同。)
[2] 《中庸》中“誠”字出現25次,其中12處為表示狀態的形容詞,7處名詞,6處動詞。
[3]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28頁。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4頁。
[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5頁。
[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5頁。
[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5頁。
[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8頁。
[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32頁。
[1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30頁。
[1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4頁。
[1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19頁。
[1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27頁。
[1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30頁。
[1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30頁。
[1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31頁。
[1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32頁。
[1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33頁。
[1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第一版,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