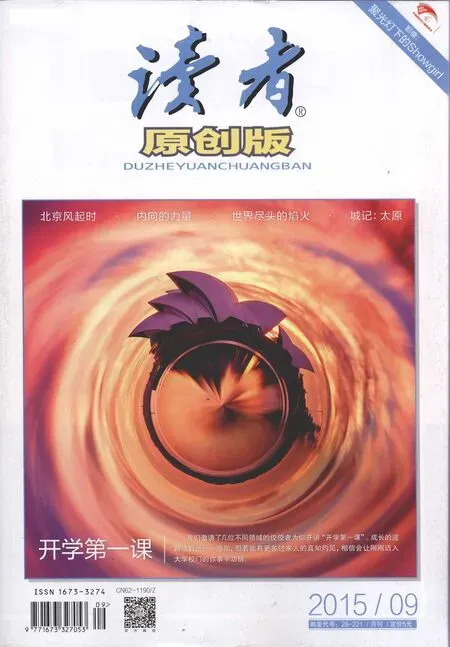枇杷
文_這 么
枇杷
文_這 么

小區里有一棵枇杷樹。它聰明,長得高,高得過分,有兩層樓那么高,筆直地長上去,在接近樹頂的地方,才開始結枇杷。
入了夏,小枇杷一簇一簇的,在那么高的地方,一萬片綠葉也遮擋不住,都招搖地黃了起來。枇杷的黃是明黃,比警示燈、救生衣的黃稍微淡一點兒、柔一點兒、潤一點兒,但也讓路過的鳥和人無法漠視。
陸續地,枇杷樹下多出了許多不該出現的東西:竹竿、木棍、磚頭、舊衣架、立起來的破沙發……小區里的人一撥兒一撥兒在樹底下仰著頭,來了又去,樹上的枇杷巋然不動。便宜了鳥,蹲在樹冠上,一邊吃一邊浪費,嘴里還不干不凈地吵架,把枇杷啄得稀爛掉到地上,看得人越發惱火。
沒法子,這棵枇杷樹,離地兩米的這段樹干都沒有枝杈,難爬。旁邊還圍著一窩毛竹,竹子一下雨就抽高一截,竹葉擠擠挨挨的,戳得人生疼。
這窩毛竹,很明顯,和這棵枇杷樹是老鄰居,是發小來著。
然而世上無難事,不怕賊偷,只怕賊惦記。君子好吃,何患無成?在觀望了幾天后,我們還是決定去試一試。
因為胖子是個藝術家,看重身份,所以爬上爬下的事都是我來。我先爬到沙發上,然后揮起竹竿,竹竿前頭綁了根棍子,左打右打,就是打不著,離最矮的那一簇都還差得遠呢。
正考慮改換戰術,胖子在底下一聲喊,撒丫子跑了。干嗎呢?“好多的花腳黑蚊子!”我在家門口追上胖子,他驚魂未定,把夏威夷短褲下的兩條粗腿伸出來給我看。肉眼可見的暗紅色大包,一個一個在那細皮嫩肉上凸現了。“再也不上你這賊婆娘的當了!”
此役的結果是胖子呼痛呼癢了足足一個禮拜,穿著牛仔褲和長襯衫的我,也沒逃脫蚊子們的利嘴,并且因為是過敏體質,到現在還在抹藥膏。
“有違公德的事,果然不能干哪。”
“誰能想得到,那棵詭詐的枇杷樹居然跟毒蚊子做了好朋友呢?”
其實,今年我們買了好多三潭枇杷吃。三潭枇杷產自歙縣,新安江上有漳潭、綿潭和瀹潭,下臨深水,上倚群山,都產好枇杷,小時候倒是年年吃得到。那時我爸常去歙縣出差,到了枇杷成熟的季節,當地的朋友就送枇杷,用編織得粗枝大葉的竹簍裝滿了,簍口用紅塑料繩一扎,左手一只,右手一只,在長途汽車站大呼小叫,拉拉扯扯,扭作一團。終于,車子發動了,送行的一方扔手榴彈似的,把竹簍奮力投進車窗,被送的一方慌忙抱住,又是抱怨,又是致謝,又是到鄰座膝蓋上撿滾掉的保溫杯,然后再回身,跟窗外齜著牙笑的人揮手道別。
這些枇杷,沒疤沒蟲眼,個頭差不多,都有土雞蛋那么大,皮是低調的赭黃色,輕輕一撕就脫落,露出肥厚的蜜色果肉。個個熟透,甜得厚道。
所以我一直以為,枇杷就是這樣好吃的一種水果。
其實并不是。
今年網購的三潭枇杷,價格昂貴,墊了冰袋快遞過來,卻讓人失望—個頭太小,甜度不夠,又爛了不少,但是比起超市里那些奇酸無比的枇杷,還是好得多。
我們拎著一袋枇杷,走到小區門口,到傳達室取快遞。傳達室老頭說:“嚯,你們買的這是什么雞蛋,這么小?”我們趕緊請他嘗,他推辭半天,嘗了一個,說:“還怪甜的,這個叫啥?枇杷?真的沒吃過。”
“老師傅,你是哪里人?”
“我是阜陽的!”
也難怪,枇杷大體上只種在長江以南,冬天開花,初春結果,耐不得寒冷。熟了落地又爛得快,不好運輸,老北方人沒吃過、沒見過的多。
枇杷樹四季常綠,葉子確實有些像琵琶。自然,此枇杷非彼琵琶,“若是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果子秀麗好看,吃之外,兼做清供,入畫。
枇杷好像親水,在湖中島、江中洲上長得好。去年5月底,在太湖東山走走吃吃,干掉了十來斤白沙枇杷。白沙枇杷和三潭的不同,個兒小,圓,皮色嫩黃近白,水分足,吃起來是水靈鮮嫩的清甜。
“東山枇杷,西山楊梅。”東山的枇杷有名,在島上吃,也還便宜。
不過最好吃的白沙枇杷,也是目前為止我吃過最好吃的枇杷,是在蘇州山塘街菜市買到的。一個瘦瘦的男人,蹲在早市的角落里,身邊放著一竹簍的黃果子。二十元一斤,不還價。一還價,他臉上就浮起傲慢的笑來:“正宗白沙枇杷,多買點兒吧,你們吃了還會來的。”
因為還要逛市場,只稱了五斤。午飯后回到賓館,嘗一個,大驚,再嘗一個,面面相覷,跳起來就往山塘街跑,可哪里還能找得到。本來下午回家,改了主意,一路把車開到太湖東山去了。然而,在東山也沒吃到那樣好的枇杷。
想吃真正的好果子,一看品種,二看水土,三看時節,最后,當然還要吃的人有機緣。
所以,吃應季水果是一件有喜氣的事情,吃罷又要等下一年了,一年一年就這么過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