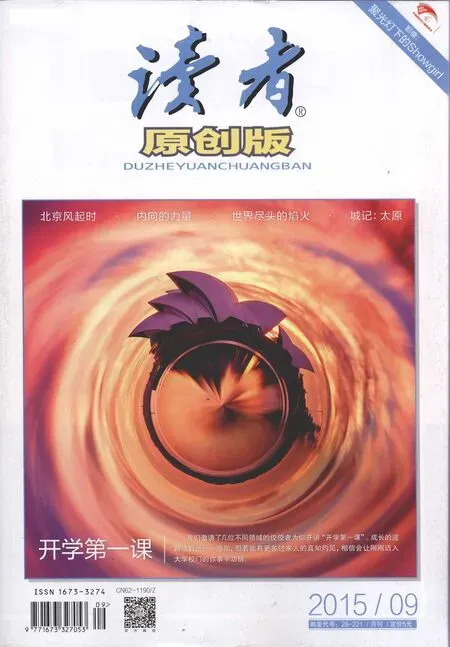世界盡頭的焰火
文_桑 雨
世界盡頭的焰火
文_桑 雨

昨晚睡前手機突然震動,跳出Koo的短信:“我真高興你已經回美國了,現在我每天都像活在地獄。”Koo因為工作關系已經在約翰內斯堡生活了4年,而此刻距我離開南非整整兩周。
據CNN4月17日報道,自南非沿海城市德班開始的暴亂已經蔓延到了首都約翰內斯堡,造成6人死亡,其中4人為這場暴亂的目標—外國人,2人為南非公民。事件的起因是,南非人數最多的民族祖魯族的領袖祖魯王公開發表言論,表示“外國人玷污了南非的街道”,于是,祖魯族以及其他南非居民開始武裝游行,攻擊過往車輛和行人,燒毀店鋪,入侵居民住宅。盡管當地警察已經采取了各種防御和戒嚴措施,但事件仍然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主流新聞媒體給出的事件起因則大相徑庭:南非當地的失業率已經高達25%,國內經濟發展存在許多問題,而作為一個多民族混雜的移民國家,南非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有許多難以名狀的微妙之處。
事件的爆發對我來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為志愿者工作在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生活了一個月的我,對這個國家獨特的氣質深深著迷,甚至考慮在未來能夠長期生活在開普敦—一個依山傍海、有音樂和美食的人間天堂。然而,同事們被搶劫,進入當地人聚居區時被不友好地圍觀,以及每當夜幕降臨時都提心吊膽,即便5分鐘的路程也不敢獨自出行的經歷,卻令我感到失望和困惑。
黑與白
談起歷史上最反人類的政策,種族隔離毫無疑問是其中之一。這項違反人類最基本信念的政策,在南非被公開執行了46年之久。在種族隔離最激烈的年代,一旦被劃為黑人,即意味著只能在限定的區域內活動,外出必須攜帶“通行證”,在公共場合隨時會被警察要求出示“通行證”,如果無法出示,便會面臨牢獄之災。
在約翰內斯堡的種族隔離博物館中,廢棄的裝甲車和被子彈擊穿的頭盔作為歷史的證物靜靜地躺在展臺和櫥窗里,一張張黑白照片平靜地敘述著那段充滿血與淚的歷史。在開普敦,兩張標記著“白人專用”和“有色人種專用”的長椅毫無愧意地佇立在市政廳門口,時刻提醒人們,歷史就像影子一樣,即使無法觸碰,你也無法否認它的存在,而且它注定會緊緊跟隨。
在1960年至1963年期間,350萬非白人的南非人被迫離開家園,進入政府劃給他們的聚居區,其中就有約翰內斯堡附近規模最大的黑人聚居區索韋托。
如今的索韋托,仍是約翰內斯堡附近最貧窮和混亂的區域之一。雖然政府進行了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比如修建被當地人戲稱為“火柴盒”的小房子,比如鋪設水管和電路,但更多的是明顯帶有DIY性質的由卷閘門、塑料板和形狀各異的木板搭建起來的臨時避難所。這里的居民包括種族隔離時期被強制遷徙過來的南非居民,從非洲其他國家經由合法或非法途徑進入南非避難的難民,以及無法承受像約翰內斯堡這樣的大城市越來越高的房價和物價而被迫進入聚居區的人。
在這些聚居區,外來者尤其白人是不被歡迎的,所以我們志愿者進入聚居區的學校工作時永遠都是集體行動,而且我們被禁止在天黑后進入聚居區。
然而在南非首都約翰內斯堡,一切又是另一番景象:在特定的購物區或繁華地帶,隨處可見西裝革履的生意人以及裝飾典雅的咖啡館和西餐廳。當我在羅斯班克地鐵站附近的一家餐館坐下時,服務生熱情且專業,餐館的菜品以及價格都令我有種身在紐約西村街角某家咖啡館的錯覺。唯一的區別是,大多數西裝革履、在有機超市購物、在餐館吃新鮮水果拼盤的是白人,而大多數在超市柜臺收銀、在餐館做服務生以及在路邊游蕩、看起來無所事事的是黑人。
Koo在一家韓國企業負責非洲市場的推廣工作,她非常沮喪地向我訴說了對這個國家的了解:南非的個人所得稅相對于當地的收入水平和物價而言奇高無比,納稅人所能夠得到的基礎服務卻少得可憐。沒有完善的醫療保險,更沒有其他福利和保障措施,甚至連人身和財產安全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自己來保障。難怪南非各個城市的街頭都充斥著“武裝保護”的廣告,當你遭遇搶劫或暴力襲擊時,最可靠的往往不是警察,而是這些私人的武裝保安公司。
而我作為一個亞裔女性,時刻能感受到路人投來的好奇目光。當我獨自行走在約翰內斯堡游客較少的街區時,好奇和恐懼都會越來越多,尤其在所有人都反復告訴我約翰內斯堡是一座對待游客多么不友善的城市,尤其是在Koo駕車送我去車站的途中,因為在等紅燈時無視了一個黑人青年的乞討,被對方從半開的車窗澆下的一瓶可樂淋得狼狽無比之后,我也默默地對這個國家起了戒心。與此同時,我又為此感到羞愧無比,原來成為一個僅僅根據種族和膚色就試圖判斷他人本質的種族主義者是如此容易。
事到如今,這場暴亂的進程告訴我們,這個國家的內部沖突已經不僅僅是因為或深或淺的膚色而遭到不公平待遇,因為大多數來自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津巴布韋、盧旺達等地的居民同樣受到了嚴重的沖擊。這已經不是一場反對任何種族的暴亂,而是一場反對國際化進程,以及為自身處在不利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尋找替罪羊的暴動。
開普敦的氣質
2013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是一部名為“尋找小糖人”的電影,講述了落魄的美國歌手羅德里格斯在美國發行了兩張無人問津的唱片后,放棄了歌唱事業,成為一名裝修工人。機緣巧合,他的唱片由一個前去看望男友的美國姑娘帶去了南非,并一發不可收地紅遍了大街小巷。在種族隔離時代,許多南非白人對這項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卻因為政府的高壓統治而保持沉默,在受到羅德里格斯專輯的啟發后,他們意識到原來可以用音樂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可以用藝術的形式進行反抗。許多受到羅德里格斯影響的南非樂隊以及他本人都成為那個年代的南非人成長的記憶,同時,他們也是引導年輕人開始反抗的標桿。
這樣一位傳奇的歌手,對自己在南非的影響力卻毫不知情,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直到幾個南非的音樂人開始尋找羅德里格斯。他被找到后,在南非開了數場演唱會,場場爆滿。當他站上舞臺時,觀眾們無論年老還是年輕,都會尖叫和流淚,并不是因為他們見到了偶像,而是因為他代表著一個墜落時代的夢想,他的歌曲見證了這個國家最黑暗也是最光明的一段歷史。
羅德里格斯在美國的默默無聞與在南非的影響力恰好印證了我對南非這個國家最大的感受:南非有自己非常特殊的氣質,而作為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與南非相對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開普敦似乎仍舊任性地游離于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之外,保持著自己野孩子的本性。
我在開普敦最常聽到的一個英文單詞就是chill,它似乎是對所有問題的完美回答:你在干什么?Chill。你現在怎么樣?Chill。我們接下來干什么?Chill。似乎很難找到完美的中文翻譯去解釋這個單詞,通常來說,這個詞表達了開普敦居民對生活的一種散漫和隨性的態度:每天工作到下午5點,就可以拿上沖浪板,驅車5分鐘到海邊,或約上兩三好友去酒吧對著夕陽小酌,或提著吉他和架子鼓,約上樂隊成員排練。
我工作的機構在開普敦周邊的聚居區建立了幾所學校,包括一所專門招收身體或智力有缺陷的學生的小學,同時組織了許多課外活動,包括沖浪、游泳,僅僅是為了讓在聚居區長大的孩子能夠受到更好的教育,在放學后有事可做,而不再游蕩在街頭巷尾,成為暴力組織或黑幫的受害者,更不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一同工作的志愿者大多數來自歐洲,其中大部分來自丹麥、挪威、瑞典等國,而大多數志愿者都是剛剛高中畢業來旅行的年輕人。
盡管在我工作的兩周時間里,一個丹麥女孩和同伴遭遇搶劫,劫匪用螺絲刀捅傷了她的后背,使得她不得不住院治療;另一個年僅19歲的德國姑娘在與好友旅行時,為了避讓迎面而來的車輛而將車開下了懸崖,再也沒有回來……但仍舊有許多人選擇留下來,不論時間長短,都帶來了一些小小的改變。
也許正是這種回歸生活原本樣子的態度,給開普敦帶來了獨特的氣質:我們不再追求華服豪車,不再按照人的收入來判斷他們是否值得尊重,不再疲于奔波,開始為看得見的改變而努力。當然,如果某一天,開普敦的氣質無法改變一撥兒又一撥兒心懷遠大發展目標的“外國人”,無法讓他們意識到強加于他人的繁榮即是剝削時,開普敦也許會成為下一個約翰內斯堡。
或許這世界盡頭的焰火,也將要熄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