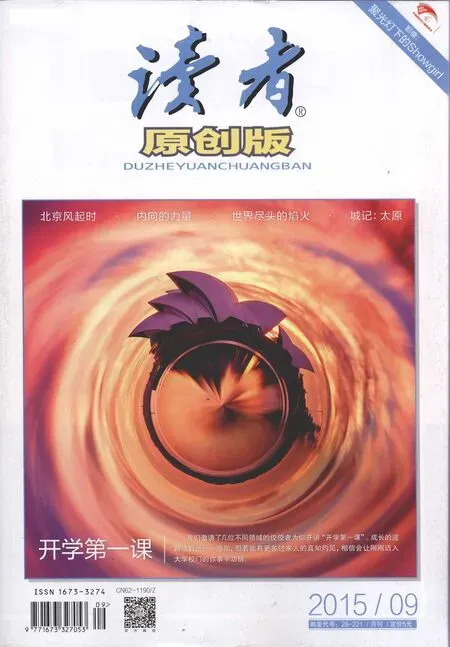平衡在心,浮游天地—專訪大冰
文_特約撰稿 魏小帥
平衡在心,浮游天地—專訪大冰
文_特約撰稿 魏小帥
專訪
與其同行的編輯還在環顧四周,尋找約定的地方,大冰已經埋頭快步走向了咖啡廳,黑色的棒球帽遮住半張臉,辮子蓬松地從帽子后面支棱出來。“我們抓緊時間,工作要緊。”大冰邊說邊往沙發上坐,順手拒絕了服務生遞上來的酒水單。
他剛從排練場出來,在北京的晚高峰時段穿城而過,些微遲到,心急火燎。
這是8月初,離北京展覽館“大冰和他的朋友們”音樂會還有最后兩天,排練進入最緊張的階段。“音樂人”是大冰的身份之一,確切地說是民謠歌手。此外,他還有一系列身份:二流主持人、資深背包客、不敬業的酒吧掌柜、漫畫作者、手鼓藝人、HangDrum(一種打擊樂器)演奏者、業余皮匠、業余詩人、大齡“文青”、大學導師、“西藏控”、第三代“拉漂”、資深麗江“混混”、重癥失眠患者、禪宗臨濟弟子。
“這么多身份,那你該怎么做自我介紹呢?”面對這樣的疑問,大冰不假思索,又有點兒樂:“我就說,我叫大冰。”
平行世界中的多元生活
在眾多報道中,大冰被描繪成了這樣一種形象:藝術科班出身,以主持成名,后來背包旅行,嘗試各種生活,出書、唱歌、開酒吧、當匠人,悠然自得,最終成了“‘90后’最想成為的人”。
大冰出生于煙臺,成長于萊陽,求學于濟南,就讀于山東藝術學院,專業是風景油畫。18歲時,他背著畫箱和背包滿世界晃蕩,夢想著能有一雙A貨耐克鞋和帶支架的油畫箱,夢想著能畫出最好的作品來。但是還沒畢業,他就進入了山東衛視,從美工開始,逐漸成長為主持人。
主持人是大冰最早為人所熟知的身份,他主持的綜藝節目《陽光快車道》大獲成功,他也被稱為山東衛視的金牌主持人。“大冰哥哥”成為一代人的童年記憶,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陪伴不少人走過童年的大冰,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大男孩。
直到大冰以作家和民謠歌手的身份出現,人們才驚覺,這個鬼馬、陽光的大男孩,經歷著遠比電視屏幕上更豐富的人生。
從大一開始,大冰背包旅行,一邊行走,一邊賣唱。簽約山東衛視后,幾乎所有不用坐班的時間,他都在旅行。他打手鼓,在邊陲小鎮給銀匠當學徒,跟著皮匠師傅學快要失傳的手藝。他和朋友陸續在拉薩、麗江開了幾家酒吧,包括“浮游吧”在內的酒吧都倒閉了,只有“大冰的小屋”勉強維持。大冰說自己是個不太合格的酒吧掌柜,但并不妨礙各路有傳奇經歷的人在此聚集。
所有的職業和經歷都幾乎同步進行,他一字一頓地將這種生活狀態總結為“平行世界的多元生活”。
“多元選擇是一項基本權利,這就是一個我在主張權利的過程。”他語速略快,說話和文字風格完全不是一回事。
規劃、分割與網格
他常在自己的身份前加上“二流”兩個字,他認為“一流”無法達到,通過這種方式來闡明生而為人的局限性。他不追求單一領域的極限,卻主張在生活的廣度上追求極限。當被問及想完成的事情是否太多時,他說:“我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出成績了。我沒有什么不滿足,想做的事情就一步一步往前做吧。”
事實上,大冰的游刃有余有賴于精密的規劃和驚人的執行力。所有看似率性而為的舉動,實則循著一條隱形的、精心設計的線路在穩步推進。“這一切都在我的規劃中,現在的我就是自己當年想成為的人。”
隨著大冰人氣劇增,網民對其多有爭議,褒貶不一。他很少花費時間與網民爭辯,因為“沒有必要”。唯一的憤怒來自讀者對他所寫故事真實性的質疑,他專門撰文痛斥。
“誰質疑,誰舉證。我在很多地方都說過了,就賭一根手指。如果查明這個人不存在,書里的故事沒有發生過,我切一根手指給你。”大冰一邊說,一邊用右手沿著左手食指做了一個切割的動作,“但是如果查不出來,你切一根手指給我—我是江湖氣很重的一個人。”有時被尖銳的問題逼到死角,大冰就如此回應對方。
有傲氣,有戾氣,有江湖氣,有才氣—大冰的朋友給了他這樣的評價。這些特質剛好成為大冰保護每一種生活的獨立性的手段。他近乎嚴苛地區分自己的每種職業,使其變成一個個獨立的網格,不讓每種生活之間發生交集。最廣為人知的一個細節是,他用做主持人的工資還房貸,即使酒吧面臨倒閉,也只依靠唱歌賣酒的錢來維持。
對于大冰而言,每種身份都是獨立的,不是寄生關系,他需要做的只是在不同的身份之間自由切換。



既朝九晚五又浪跡天涯
大冰最近在做“百城百校”系列演講。不少向往遠方的年輕人向他表達了想去流浪的夢想,大冰卻極為反對。
“一門心思地浪跡天涯與一門心思地朝九晚五沒有任何區別,而且,說走就走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浪跡天涯沒有錯,朝九晚五也沒有錯,他無法認同的是一生只做一次單向選擇。大冰用桌腿打比方,認為圍繞一個重心的生活是不穩定的,人應該用好幾條“桌腿”來支撐起整個生活。
大冰將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那些神奇的朋友稱為“族人”。他們并非異類,都是“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跡天涯”的人。如何做到既朝九晚五又浪跡天涯?他把身邊的例子都寫進了書里。
“一門心思流浪的人,進不了我們的圈子。出世和入世之間要找到一個平衡點,工作和生活之間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旅行沒有那么‘高大上’,旅行和生活之間也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朝任何一個方向走向極端,都不是他所愿。

記錄世界的善意
2015年5月底,大冰和朋友發起了音樂會眾籌,一個月內獲得了140%的資金支持。依靠這筆錢,他們得以請火塘酒吧的歌手在北京的舞臺上表演。人們說,這是一場江湖游俠的聚會,一場浮世散人的彈唱會。這群人正是大冰筆下“最幸福的人”。
從2013年起,大冰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書,第一本書便是《他們最幸福》,書中記錄的都是他所看到的、經歷過的故事。
他寫路平,一個逃離了簽約公司的流浪歌手;他寫自己“異父異母”的妹妹雜草敏,在自己行走江湖時,始終溫暖陪伴;他寫一個不用手機的女孩,從酒吧出來散心,一路走去了珠穆朗瑪峰;他寫小越陽,一個有著音樂夢想卻過早離世的孩子,大冰聯合民謠音樂人為他錄制專輯……
大冰用指尖敲著桌上的新書:“我想說的都在這里。”
《乖,摸摸頭》位列三大電商圖書榜單第一名,《阿彌陀佛么么噠》也在預售期受到熱捧。單部作品銷量突破百萬冊,他的走紅出人意料,走紅的原因卻并不令人意外—他一直在記錄這個世界的善意。
“善良是一種天性,善意是一種選擇。選擇善意,即選擇了天性,選擇了光明。”他引用《三慧經》里的經文解釋善意,“善意如電,來即明,去便復冥”。他書中的故事如閃電,也許短暫,但足以照亮人心。
“文以載道,這要求我將自己所感受到的陽光的東西表達出來。”文藝是表達的手段,而表達則是人的權利。
“權利”是大冰在接受采訪時說得最多的一個詞。他關于“權利”的闡釋,順溜得好似背熟的繞口令,而他每次說的時候,帽檐底下都露出一雙亮亮的眸子,長久注視著你,讓人覺得,這雙眼睛和這個詞語,都不容輕視。
我有很多人生選項
《讀者·原創版》:你平時怎么介紹自己?
大冰:在不同的場合,說不同的身份。比如在當下,我們在出版行業,我會說我是個作者;如果是在酒吧行業,我會說我是個掌柜;如果是在傳媒領域,我會說我是個主持人。
《讀者·原創版》:如果一個人需要在短時間內了解你,你希望他通過什么樣的途徑?
大冰:在泛泛的人際交往中,直接告訴對方我叫什么名字就好了,我也不希望別人在短時間內了解我,這種了解沒有意義。社交分很多不同的層面,還是直接一些比較好。
《讀者·原創版》:你害怕被別人貼標簽嗎?
大冰:我反對的不是標簽,而是單一的標簽。用一個標簽來界定一個人,肯定是不科學的。
《讀者·原創版》:在剛進主持界時,有沒有想到十多年后會是今天這樣的狀態?
大冰:想到了,本來也沒有打算在這個行業干一輩子。我干的所有職業都沒有打算干一輩子。你說一個人在七八歲的時候,他能立下遠大的志向嗎?我覺得那是扯淡,肯定是在我們成年并有了一定的社會經驗之后,做出了最初的規劃。嘗試的過程是實踐的過程,是漫長的觀察世界的過程。到最后你可以把它總結出來,任何一個理論都是通過實踐得出的。
《讀者·原創版》:如果按照“一張桌子需要有多條桌腿來支撐”的比喻,你最開始形成的一條“桌腿”是什么?
大冰:我沒有想過先把一件事情做完了再做另外一件事情,都是同時慢慢地開始。唯一例外的是作者的身份,這個身份是我用來總結前面那一系列身份的。之前,干傳媒的同時我也在畫畫,同時也在玩音樂,還在做生意、開酒吧、旅行。不能說哪個是第一個,它們是不應該被時間概念局限的。
《讀者·原創版》: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有沒有遇到過來自家庭的阻礙?
大冰:從來沒有。比起大多數人,我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時間長太多了。我每年至少有兩三個季度和父母住在一起,我會帶著父母出去旅行,很多人做不到吧?但是大家總愿意把我這種非常規化的生活理解為拋家舍業,認為是帶有原罪的,是與父母脫離的。我爸媽都是大學老師,他們用很正常的方法來教育我。但是也許這種“正常”,在那個年代剛好是不正常的。
《讀者·原創版》:很多人會困惑于“選擇了一條路,就不能選擇另外一條路”,你怎么看?
大冰:為什么要困惑呢?這種思維是我們的父輩秉承的。我們的父輩沒有錯,只是因為他們經歷的時代不同。我們身處的時代,不一定“要做社會的螺絲釘”“干一行愛一行”,這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沒有說一輩子只做一件事兒嘛。
《讀者·原創版》:一個人要如何選擇自己的生活?
大冰:有人適合單一的生活,我從來沒有指責過單一的生活就一定是錯的,我只是說單一的生活不適合我。但我們有權利去主張多元選擇,高度文明的社會永遠是多套價值觀并行的。我們有權利主張生命的多樣性。
《讀者·原創版》:在多種身份之間游刃有余,你有什么技巧嗎?
大冰:這跟技巧沒太大關系,就是“想不想”的問題,想做一定能做。有的人覺得難,是因為沒有勇氣,邁不出第一步,那就是不想,至少是沒有那么想。我從來沒有辭過職,我在體制內,之前的電視臺是一個事業單位,一樣是朝九晚五,就看你要多少而已。我覺得當好主持人就行,不需要去負責一個部門,那我自然可以擁有很多時間。臺長肯定要比部門負責人更忙,我沒有想過要去當臺長,這不就可以了嗎?就是個想要多少的問題。
《讀者·原創版》:設想一個極端的場景:你被困住,無法動彈,無法言語,你會怎么樣?
大冰:不會怎么樣,因為我的人生選項已經足夠多。大部分人一輩子只干一件事兒,或者只在一種生活模式下,最起碼我還有這么多的選項,我相信終歸有一個選項可以拯救我。這個“保險”我已經“買”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一點兒都不擔心這個問題,就像我完全不擔心我的經濟狀況一樣。
《讀者·原創版》:相信你在生活里也見到過很多烏七八糟的事情,為什么不把這些東西呈現在書里?
大冰:把值得記錄的東西記錄下來,這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