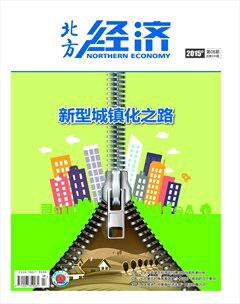“十三五”時期內蒙古推進城鎮化發展的戰略思考
杭栓柱 朱曉俊 趙秀清 張 捷
當前,內蒙古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處于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時期,也處于城鎮化深入推進的關鍵時期。中央城鎮化會議、《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對我國城鎮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府也對推進新型城鎮化提出了總體要求。“十三五”時期,內蒙古必須按照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創新理念,轉變方式,全面提升城鎮化的質量。
一、充分認識城鎮化的地位
(一)城鎮化是內蒙古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一是城鎮化是擴大消費和投資需求的最大潛力。在城鎮化過程中,城鎮人口持續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將刺激農牧業和城鎮投資需求:如道路、給排水、電力通訊、交通等基礎設施,工業消費品以及房地產需求。我國經驗表明,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可帶動城鎮固定資產投資50萬元。預計2020年內蒙古城市化率將達65%左右,城鎮人口大約為1657.5萬人,還需要追加約9588億元左右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時,如果按照城鎮人口統計的400萬農牧民工及隨遷家屬未能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墾區和林區的150萬人口中的1/2轉變為城鎮人口,每人按照平均10萬元的公共服務費用計算,還需支付2750億元。這樣,內蒙古城鎮化建設資金需求總量大約在12338億元左右,平均每年需要1762.6多億元,相當于2013年內蒙古財政收入的66.3%。

二是城鎮化是服務業加快發展的重要動力。大量分散居住的農牧民轉移、集聚到城鎮后,擺脫了以往家庭式自我服務的生活模式,加上城鎮生活質量和生活需求多樣化高于農村牧區,對文教衛生、商貿流通、旅游休閑、娛樂健身、住宿餐飲、交通運輸、市政服務、社區服務等生活性服務業產生了龐大的需求。城鎮發展要素的配置,社會分工的細化,不同產業的銜接,也對金融保險、現代物流、廣告設計、商務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產生較大的需求。
(二)推動內蒙古東西部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
進入新世紀以來,內蒙古呼包鄂地區依托資源、區位優勢,實現了率先發展,成為全區經濟增長的領頭羊。相比之下,由于市場、體制等多方面因素,蒙東地區整體發展水平相對滯后。2012年,蒙東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僅相當于全區平均水平的71.7%,財政實力和城鄉居民收入也顯著低于全區平均水平。”十三五”時期,蒙東地區面臨著繼續加快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牧業現代化的歷史性任務。其中,通過城鎮的發展,可以迅速提高經濟實力,增強輻射和支援能力,帶動區域整體發展;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為民生改善提供基礎條件。因此,通過推動城鎮化加快發展,帶動蒙東地區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是自治區區域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
(三)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途徑
城鎮化的過程是農牧業實現現代化、大部分農牧民實現非農化和市民化、城市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農村牧區推廣、城市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農村牧區普及、城鄉差別逐步縮小直至基本消失的過程。內蒙古作為傳統的農牧業基地,農村牧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交通、衛生、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遠遠落后于城市。這些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統籌城鄉經濟發展,通過推進城鎮化進程,為新農村新牧區建設創造積極條件。一方面,規模經營是農牧業現代化的主要特征。近幾年來,我區在加快推進城鎮化的同時,不斷引導農牧民加快土地草牧場承包經營權流轉,使土地草牧場向專業大戶、家庭農牧場、農牧民專業合作社和農牧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流轉。這不僅提高了土地、草牧場的規模經營和集約化程度,實現了生產成本降低、農牧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農牧民收入增加,也加速了農牧業的資金積累,有力推動了縣域農牧業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城鎮人口的集聚可以為農畜產品創造穩定的市場需求,為農牧業規模化、產業化經營開拓了巨大空間,有利于形成布局區域化、生產專業化、管理企業化、服務社會化的農牧業現代化格局。
二、內蒙古城鎮化要遵循城鎮化發展的客觀規律
我們認為,特別是要注意把握城鎮化發展的三個國際規律。
(一)城鎮化進程的階段性規律
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城鎮化進程一般要經歷起步期、加速期、成熟期三個階段,總體呈現出類似“S”形的發展曲線。起步期的城鎮化率一般小于30%,主要特點是城鎮數量少,城鎮人口用地和經濟規模小,城鎮職能單一,對區域的輻射帶動能力有限,城鎮化速度慢,國際上一般把其作為城鎮化發展的起步期。加速期的城鎮化率在30%-70%之間,主要特點是城鎮數量迅速增加,城鎮人口用地和經濟規模急劇膨脹,城鎮職能拓寬,對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明顯增強,城鎮化速度較快。成熟期的城鎮化率一般大于70%,主要特點是新的城鎮增加緩慢,城鎮人口郊區化和分散化,城鎮化速度放慢。
2013年內蒙古城鎮化率為58.7%,與城鎮化發展成熟期70%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總體上內蒙古仍處于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但是,綜合考慮其他因素,內蒙古城鎮化已經進入加速階段的后半期,城鎮化推進速度將會呈現由遞增轉變為遞減趨勢,將從以前過度追求量的增長向質的提高轉變,更加注重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的農牧民工市民化問題(即人口城鎮化),將會影響城鎮化的速度。
(二)城鎮化的差異性規律
內蒙古地域廣闊,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和基礎有很大差距。經過過去十余年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差異性更加明顯,這導致了城鎮化水平在各地的差異。一是區域之間的差異。全區12個盟市,超過自治區城鎮化率平均水平的有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烏海市、鄂爾多斯市、阿拉善盟、呼倫貝爾市、錫林郭勒盟。其中,城鎮化率最高的是烏海市,達到94.59%;最低的是通遼市,城鎮化率為44.28%。二是全區主要城市集中分布于中西部,東部地區人口相對分散,沒有孕育出具有較強輻射能力的中心城市。突出表現在東部地區有13個城市,其中包括赤峰市1個特大城市,通遼市等5個中等城市,7個小城市。這些分布在6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10萬平方公里有2座城市、38.7個鎮,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市(包括地級市和縣級市)平均規模為22.73萬人,比自治區城市的平均規模少19.15萬人,比全國少37.34萬人。這種地廣人稀、城市密度和規模小的特征,導致城市規模偏小,集聚產業和承載人口的能力不高。三是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差異。以呼倫貝爾市為例,2013年該市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了69.73%,超過自治區平均水平11個百分點,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但是,境內林區、墾區的約60萬人口戶籍為城鎮戶口,但生活區遠離城鎮,基礎設施、生活條件遠未達到城鎮的水平。剔除這部分人口,實際的城鎮化率僅為43%左右。
(三)產城互動性規律
城鎮化與工業化共同構成現代化的雙翼,工業化是城鎮化的推動力,城鎮化反作用于工業化,兩者相輔相成,需要保持協調發展。從內蒙古的實際看,突出的矛盾在于產業發展與城鎮化的健康推進不匹配,支撐城鎮發展的產業體系滯后,使進入城鎮的人口缺乏就業和增收的途徑。我區城鎮規模逐漸擴大,但由于經濟結構中60%以上是資源型經濟,資本、技術代替勞動力現象十分突出,導致對就業帶動能力較弱。同時,我區資源型經濟布局分散,難以形成集聚效應。工業園區大量建設,但園區布局不合理,產業分工不明確,與資源優勢不符合,與城鎮體系不匹配,與公共基礎設施不對接。一些工業園區布局遠離城市,與生產生活服務不配套,勞動者存在著成家難、就醫難、子女就學難、業余生活枯燥等問題,導致很多園區出現了人才和生產工人難以留住。城市集聚產業和承載人口的能力不高,導致目前城市的土地利用率和產出效益都比較低。我區地級城市每萬人用地35.04平方公里,是全國地級城市平均水平的2.2倍;每平方公里產出2941.81萬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64.6%;地級城市市轄區占全區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為47.4%,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4.6個百分點。
三、推進新型城鎮化應著眼于實現三個轉變
(一)城鎮化由重物向重人轉變
要從過去停在地上、注重外觀的重物輕人的高代價、粗放型的傳統城鎮化轉向以人為本、城鄉一體、綠色低碳、集約型城鎮化。也就是說,內蒙古要樹立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發展理念,從促進人的發展角度推動城鎮化,變傳統城鎮化的市民、農牧民工的雙軌運行為一體化的單軌運行。重點是將進城農牧民徹底轉變為市民,核心是通過綜合配套改革,促使農村牧區權益可以方便有效公平地轉化為城市權益,取消城市市民與農牧民工在社會權益和公共服務中的雙軌制,逐步將有條件的農牧民工及家屬轉移到城市中,實現農牧民工徹底市民化,推動城市人口一元化。
(二)城鎮建設由擴空間為主向提功能為主轉變
目前內蒙古人均城鎮建設用地(建設用地面積除以市區人口計算得出)已經達到127平方米,高于全國67.7平方米的平均水平59.3平方米,也高于發達國家人均82.4平方米和發展中國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盡管國家給內蒙古人均用地指標放寬到150平方米,尚有一定的增加空間,但未來城鎮建設的主要方向應以提升城鎮功能為主轉變。同時要看到,許多城市在確定綜合承載能力時較少考慮農牧民工需求,大多數地區城市規劃和建設還沒有充分考慮到農牧民工市民化帶來的城市公共服務需求增長城市空間結構變動等因素,進一步激化了基礎設施的需求和供給矛盾。必須看到,在呼和浩特市等大城市,交通擁堵已經成為突出的“城市病”。
(三)經濟社會發展由城鄉分割向城鄉一體轉變
按照現有城鎮化發展速度,到2020年內蒙古城鎮化率達到65%的水平,仍有近900萬人口在農村牧區生產和生活,他們理應分享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城鎮化是解決“三農三牧”問題的重要途徑,但不能簡單依賴城鎮化來完全解決“三農三牧”問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同步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要求從我區城鄉分割的現實出發,堅持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方針,加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力度,以促進城鄉要素資源平等有序流動為重點,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推動城鄉要素資源平等交換和有序流動,注重城市公共服務向農村牧區覆蓋城市文明向農村擴散,讓城鎮化的進程成為促進農牧業增效農牧民增收農村繁榮的過程,使農村牧區也享受到工業和城市的文明,加快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