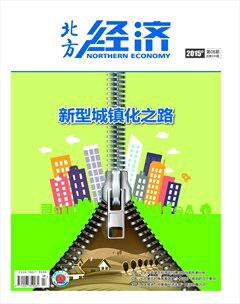我區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的著力點
張永軍
2014年9月11日,習近平主席在杜尚別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舉行元首會晤時,提出三國發展戰略高度契合,中方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獲得俄方和蒙方積極響應,可以把絲綢之路經濟帶同俄羅斯跨歐亞大鐵路、蒙古國草原之路倡議進行對接,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這為“發揮內蒙古聯通俄蒙的區位優勢,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和“建成向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和充滿活力的沿邊開放經濟帶”指明了方向,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并加以妥善落實。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指出,發揮內蒙古聯通俄蒙的區位優勢,完善黑龍江對俄鐵路通道和區域鐵路網,以及黑龍江、吉林、遼寧與俄遠東地區陸海聯運合作,推進構建北京-莫斯科歐亞高速運輸走廊,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我區與俄羅斯、蒙古國陸路相連,邊境線總長4261公里,占全國陸地邊境線長的19.4%,現已開放口岸16個,共有19個邊境旗市(15個旗,4個市),57個邊境鄉鎮(蘇木)。2014年,我區口岸進出境貨運量7085.7萬噸,是2010年的1.35倍,其中對俄口岸進出境貨運量3038.7萬噸,對蒙進出境貨運量4047萬噸。滿洲里和二連浩特分別是我國最大的陸路口岸和我國對蒙古國的最大口岸,分別承擔中俄陸路運輸的65%和中蒙貨物運輸95%的任務。2014年,滿洲里口岸進出境貨運量3010.6萬噸,占全區進出境貨運總量的42.5%,“蘇滿歐”、“鄂滿歐”、“湘滿歐”、“渝滿俄”等經滿洲里口岸各類過境班列460列,在向北開放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問題的提出
(一)突出戰略對接是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的重要前提
充分了解和掌握中蒙俄發展戰略的基礎上,找準基礎設施節點和合作領域的對接,才能更好地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
2009年俄羅斯出臺《2025年前遠東和貝加爾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作為俄羅斯實施“遠東開發戰略”綱領性文件,將提振經濟、調整結構、改善民生、加強對外合作列為首要任務。2016-2020年主要目標是興建大規模能源項目,增加過境客運和貨運量,建立核心運輸網絡,提高產品出口份額。2021-2025年主要目標是發展創新型經濟,完成大型能源和交通項目建設等。2012年普京總統指出“全面走向亞太地區是俄羅斯未來成功及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發展的重要保證”,并制定了《西伯利亞和遠東發展法》(草案)。2013年普京總統發表國情咨文時指出,發展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是俄羅斯21世紀的優先方向。2015年俄政府確定農業、加工業、化工、機械制造和住房建設為財政撥款優先發展領域。同時,俄羅斯實施“跨歐亞鐵路”計劃,跨歐亞西伯利亞大鐵路9288公里,跨越8個時區,是貫通西伯利亞的交通動脈,打通俄羅斯的遠東通道,沿途經莫斯科、車里雅賓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伊爾庫次克、赤塔、海蘭泡和哈巴羅夫斯克,最后抵達海參崴。主要包括貝阿鐵路和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現代化改造,預計2020年這兩條鐵路的運輸能力將達到每年5000萬噸。

2009 年10 月中俄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聯邦遠東及東西伯利亞地區合作規劃綱要(2009—2018 年)》提出,發展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干線將使布里亞特共和國、雅庫特共和國、赤塔州(外貝加爾邊疆區)、阿穆爾州及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現有礦產地接近現有的交通運輸線路,特別是接近通向西伯利亞大鐵路乃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納霍德卡、蘇維埃港、瓦尼諾等海港及與中國、朝鮮和蒙古接壤的邊境口岸的門戶。計劃延長涅留恩格里-雅庫茨克鐵路,建設“東西”交通運輸走廊,發揮俄遠東港口優勢,縮短貨物運輸時間,這就需要擴大和新建中俄口岸,提高濱海邊疆區鐵路的通過能力。
基于身處歐亞之間的地理優勢,2014年蒙古國準備實施“草原之路”計劃,通過運輸貿易振興蒙古國經濟。計劃從阿爾坦布拉格開始,向烏蘭巴托延伸,最后連接扎門烏德。主要由5個項目組成,總投資約500億美元,具體包括連接中俄的997公里高速公路,1100公里電氣線路,擴展跨蒙古鐵路,天然氣管道和石油管道。同時,蒙古國鐵路規劃第一階段是建設連接南部戈壁地區戰略大礦的橫向鐵路,即從達蘭扎德嘎德(南戈壁省省會),經塔旺陶勒蓋煤礦、查干蘇布拉格銅礦、宗巴音至東戈壁省,與連接我國和俄羅斯的縱向鐵路相接,再經蘇赫巴托爾省最終到達喬巴山(東方省省會),全長1100多公里,該條鐵路修通后,可直接通往俄羅斯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為蒙古國的第二個出海口,之前主要從中國天津港進出貨物。全部計劃完成后,基本上可以形成連接蒙古國各地的鐵路運輸網。
因此,對于中俄而言,我國華北和東北是俄方合作的重點地區,與俄毗鄰的內蒙古和東北三省是合作的前沿地區。這就需要我們加強經滿洲里和二連浩特鐵路與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聯通性,才能更好地發揮大通道作用;對于中蒙而言,需要加強與蒙方南部鐵路網節點的聯通,尤其是加強與重點礦區、省會城市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才能更好地拓寬合作領域。
(二)突出通道建設是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的關鍵點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而“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突出發揮好我區成熟口岸優勢,借助與蒙古國、俄羅斯的通道優勢,拓展與歐洲腹地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重點抓好:一是以滿洲里為節點,發揮滿洲里-赤塔鐵路線優勢,外延至伊爾庫茨克、莫斯科至歐洲腹地,內延至大連港、秦皇島港及東北經濟區,或者內延至天津港及京津冀經濟區;二是以二連浩特為節點,發揮二連浩特-烏蘭巴托-烏蘭烏德鐵路線優勢,外延至蒙古國、俄羅斯至歐洲腹地,通過集二線內延至京津冀經濟區;三是以呼和浩特為節點,發揮京包-包蘭-蘭新、臨河-策克、策克-哈密鐵路優勢,對外向西經新疆聯通哈薩克斯坦及中亞五國。同時,發揮呼和浩特國際航空口岸優勢,開設和增加與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伯力)、伊爾庫茨克、雅庫茨克和蒙古國烏蘭巴托等航線,形成國際航空網絡;四是以策克、甘其毛都等口岸為節點,加強與蒙古國擬建戈壁地區鐵路線、鐵路網橫線及東部區鐵路線、西部區鐵路線連接,與烏蘭巴托鐵路聯通,形成與重點礦區的重要通道;五是以黑山頭、室韋等口岸為節點,加強與俄羅斯東部地區的溝通與聯系,形成與重點礦區的重要通道;六是以珠恩嘎達布其口岸為節點,加強與蒙古國蘇赫巴托省的溝通聯系,形成內聯錫赤朝錦協同發展經濟帶的重要通道。
因此,通過上述通道建設,能夠更好地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加強與俄蒙通道平臺建設,在開展與俄蒙全方位合作的基礎上,加強與歐洲和亞洲市場的聯系,拓寬合作領域和范圍。
(三)突出“五通”建設是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的重要內容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這是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的關鍵,需要我們在兼顧中蒙俄共同需求、兼顧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贏、兼顧長期發展和近期計劃、兼顧經濟往來和人文交流、兼顧機制創新和模式創新的基礎上,重點抓好:一是圍繞跨境鐵路、公路、信息、電網、皮帶、管道,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二是圍繞能源、生態、農牧業、文化旅游等領域,推進產業合作;三是圍繞推進投資貿易便利化,促進貿易暢通;四是圍繞深化人文交流和深化醫療衛生合作,密切民心相通;五是圍繞提高跨境金融服務能力,簡化跨境貿易和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流程,推進資金融通。
因此,在正確處理好“五通”建設關系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
(四)突出口岸建設和管理是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的重要環節
從未來口岸發展趨勢看,需要把握好“三個轉變”。口岸正在從單一的開放通道向資源配置中心轉變,口岸在全球資源流通配置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口岸服務功能和范圍得到較大的拓展;口岸布局正從自然布局向根據經濟服務區域布局轉變,腹地經濟已經成為口岸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支撐;口岸功能從簡單的通道向現代化的口岸體系轉變,既服務于國內外用戶,又促進所在地口岸經濟發展。
從口岸適應未來跨境合作要求看,需要把握好“五個適應”。需要適應通關管理高效化,通過推動內陸同沿海沿邊通關協作,實現口岸管理相關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形成既符合國情又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管理體制機制;需要適應投資貿易便利化,加速要素跨境的流通,為國際貿易交易創造一個協調的、透明的、可預見的環境;需要適應人員往來便利化,才能更好地加強國與國、民與民之間進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宗教等人文交流和合作,實現民心相通;需要適應產業合作協同化,隨著產業合作領域的拓展,需要不同的合作模式和過境方式;需要適應跨境基礎設施網絡化,中蒙俄均積極尋求參與地區物流網絡,進一步深化合作。
因此,這就需要我們提高口岸管理和服務水平。首先要明確口岸功能定位,實現由注重數量向注重質量轉變,區分專業口岸和綜合口岸,避免同質同構競爭;其次理順口岸腹地互動關系,積極發展“泛口岸經濟”;再次提高口岸運行效率,加快推進“三互”建設。
二、主要建議
(一)樹立“兩個大局”思想
稟承“親、誠、惠、容”理念,妥善處理好與俄羅斯和蒙古國的關系,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建立安寧的周邊環境;堅持將心比心,以誠相待,營造良好的互信氛圍;堅持講情重義、先義后利,建立良好的利益共享機制;堅持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建立區域共同發展機制。
(二)合理有序推進合作項目建設和儲備
開展跨境合作項目涉及不同國家,具有一定的復雜性,需要依托已有基礎,分層分類,先重后輕,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確保項目有序接替,支撐有力。依托現有基礎即充分利用現有通道、口岸設施資源,避免大量新建和新增投資;分層分類,就是要明確國家、自治區、盟市、旗縣市的分工,確定不同類型地區的重點任務;先重后輕,就是對關系全局的干線通道、基礎網絡、互聯互通關鍵環節等重大項目優先部署;先易后難,主要是對國家間關系相對穩定、合作意愿強烈、容易達成共識的項目優先考慮;對那些盡管有合作意愿但達成共識難、前景不明朗的項目,要緩期開展,嚴格控制風險。
(三)加強智庫間交流合作
缺乏對俄蒙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政策、法律、投資環境等情況的全面了解,是目前推進中蒙俄合作的“瓶頸”。建議設立專門的針對俄羅斯、蒙古國的研究機構,加強與俄羅斯和蒙古國智庫間的合作交流,針對三國關心的領域和內容共同開展合作研究,做好政策和項目對接,服務于三國政府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