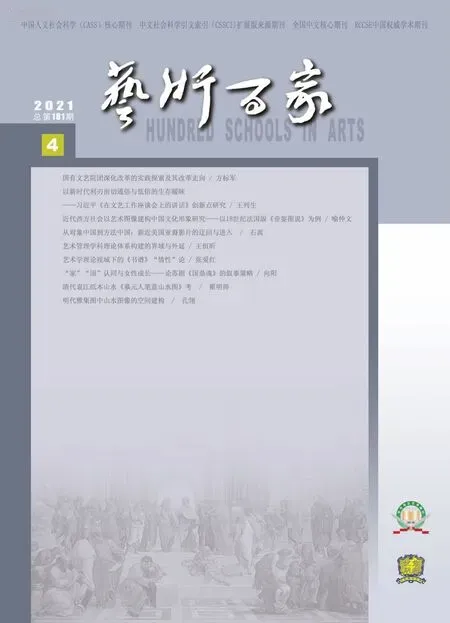日本動漫的未來想象與“物哀”美學
劉超
摘要:日本動漫繼承和發展了以“物哀”為特征的日本傳統關學理念,并將其滲透在自身對于未來世界的想象性表現當中。這一審美意識正構成了日本動漫未來想象的美學基礎:一方面,“死”的環節通過對末日浩劫的幻想被進一步放大,另一方面,“生”的過程則由于機械人、人機合體等高科技“他者性”元素的引入而得以擴展。二者的交替重合將“物哀”“充滿矛盾的愉悅感”發揚到了極致。這不但成為日本動漫最為獨特的文化標記之一,也影響了好萊塢電影乃至全球流行文化的未來敘事模式。
關鍵詞:日本動漫;傳統關學理念;未來想象;人機合體;物哀;審美文化
中圖分類號:J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104(2015)04-0235-02
為了考察日本動漫的審美特性,我們不但要在其與西方電影傳統之間進行區分,還要超越日本電影研究的樊籬,盡管日本動漫是在日本電影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本文主要對之前學者在分析小津安二郎或是黑澤明真人電影時所引入的諸如靜態畫面、陰影、負空間的運用之類的范疇便不再贅述,而著眼于大友克洋的《光明戰士》、渡邊信一郎的《星際牛仔》、士郎正宗的《攻殼機動隊》、庵野秀明的《新世紀福音戰士》等經典動漫作品對于未來人類浩劫的描繪上,并將其與源于日本動漫理念的沃卓斯基的《黑客帝國》及其動畫版以及同樣由沃卓斯基兄弟出品卻由小池健、前田真宏、森本晃司、川尻善昭等日本動畫師所執導的電影短片進行對比,從而力求突顯日本動漫的美學特征。從本質上來說,《黑客帝國》是日本動漫“美國化”之后的產物,所以能夠更好地體現出兩種文化之間的微妙差異,也能夠更好地說明日本動漫的文化意義和藝術追求。而在比較的過程當中,我們有必要對下列問題進行解答:是什么使得日本動漫中的未來世界顯得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這一表現方式反映了怎樣的美學理念,其背后又蘊含著怎樣的文化信息?這一切又與其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語境下的對應物存在著何種具體的差異呢?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有助于揭示日本動漫作為村上隆所謂“末日之后社會”(post-apocalyptic society)的精神表征是如何塑造出一個有別于美國電影中殘破、混亂、危機四伏的劫后景象的未來世界的。
在《從黑澤明到(哈爾濱的移動城堡):體驗當代日本動畫》一書中,內皮爾談到了日本近代化以來的歷史巨變和所頻繁遭遇的各類自然災害對其當代社會思潮的影響。在內皮爾看來,作為日本傳統意識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無常”觀念及與其相對應的“物哀”的審美理念在當代日本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這不但賦予了當代日本文化以一種“末日之后”的身份屬性,還推動了動漫藝術的發展與繁榮。對于絕大多數動漫作品而言,敘事的張力并非來源于“面臨世界毀滅”所產生的焦慮,而與“展現世界毀滅的方式和原因以及克服手段”有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內皮爾相信,在日本動漫中,情節的變化往往要通過外在事物的毀滅來進行推動,變化和毀滅就是同義詞,都擁有某種啟示錄式的意味。換句話說,對于建立在“物哀”美學之上的日本動漫而言,毀滅是敘事的常態,問題在于在不斷毀滅的過程之中要如何展現生的意志,這也是日本動漫的癥結之所在。正因為此,才會有如此眾多的動漫作品熱衷于刻畫未來的景象,從而以一種想象性的方式傳達對于現實世界的反思和超越。
作為“末日之后”意識的縮影。這種想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便是對機械身體和人工生命的展現上。無論是富野由悠季《機動戰士高達》中的機甲裝備、滝沢敏文《七武士》中將自己改造為力量型生物機械的菊千代、《新世紀福音戰士》中的EVA全機體、《星際牛仔》中史派克的智能眼球,還是《攻殼機動隊》里的機械戰士,都以將生物器官與人造機器相結合作為共同特征,而這也是日本動漫未來想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雖然這些動漫作品對于生物機械化的描繪大多只能歸入科幻的范疇,但卻反映了現實的希望,體現了某種“本體論”層面上的認識,將對生物技術的推崇發揚到了極致。正是在這一極致之中,動漫的制作者和觀眾獲得了超越當下存在的快感及意義。哈拉維對此總結道:“描寫半機械人的作品是為了展現生存的力量,這種生存并非基于原初的純粹,而是要利用工具來對抗這個將其標示為他者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動漫作品中的機甲或半機械人大多仍舊保持了人類的外形,其所隱喻的并非機械對人性的異化和反噬,而是生命意識的彰顯與延伸。這一運用技術的“幻景”來延續生命的手段不禁讓人聯想到巴贊所提出的“木乃伊情結”(mummy complex),即運用“存真”的影像來描摹人類活動、與時間相抗衡的審美現象。在巴贊眼中,“對生命的再現與對生命的保存其實是一回事”。在這個意義上,上述動漫形象的類人化(anthropomorphic)傾向同樣出于生命象征的需要。正如勞拉·穆爾維所指出的那樣,“比例、空間及故事都是類人化的。在這里,好奇與窺視的愿望同對相似性、可識別性的迷戀相互混雜:人類的面孔、人類的身體、人類形體與周邊環境的關系,人在世界中清晰可見。”
除了半機械人之外,文明的浩劫構成了日本動漫中未來想象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七武士》《新世紀福音戰士》《星際牛仔》以及《光明戰士》都以過去的災難性事件作為敘事背景。內皮爾也注意到了日本動漫這種對于未來浩劫的表現偏好,并將其與日本近代以來所經歷的歷次天災人禍尤其是東京大轟炸和廣島原子彈襲擊聯系在一起。實際上,這種偏好也普遍存在于美國電影當中。從1976的《大地震》到1996年的《龍卷風》,再到熱映全球的《后天》和《2012》,文明浩劫的主題在好萊塢災難片里一再上演,由此還產生了一系列描繪未來人類末日之后景象的科幻電影。這些后啟示錄式的電影與同類型日本動漫在主題處理方面最大的區別之處在于展現浩劫之后人類生存狀態的不同方式。為了進一步對這一問題進行說明,我們有必要將目光轉向由沃卓斯基兄弟共同執導的科幻電影的經典之作《黑客帝國》。該片深受日本實驗性動畫片《玲音》和押井守版的《攻殼機動隊》的影響,是在迎合美國觀眾審美趣味的基礎上對上述作品所進行的改寫和重新創造,這種改寫更加突顯了日本動漫未來想象的獨特性。
在《黑客帝國》系列中,盡管虛擬世界展現的是20世紀后半葉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場景,但在電腦程序之外的現實世界卻因為人類和機器人的戰爭而被摧毀,這構成了影片與其日本對應物之間最大的差異。一方面,機器并非像日本動漫所表現的那樣成為人的生命的擴展和延伸,而是化作某種可怕的異化力量,時刻與人處在緊張對立的關系之中,一直在試圖操縱、奴役和毀滅全人類。另一方面,人類自身構成了這一切災難的根源:沒有人類對于機器人的殘酷壓迫,就不會產生隨后機器人的大規模反抗和與人類的最終決裂;如果在戰爭中人類沒有為了終止機器人的能源供應而遮蔽太陽,也不會帶來人類文明的最終毀滅。人類的殘暴與墮落在《黑客帝國》的動畫版中占據了更為重要的地位,被以編年史的方式呈現出來,使得這一對人性的批判顯得更加尖銳。
相反,《光明戰士》對文明浩劫的回顧只有一開始的幾個鏡頭,緊接著便采用多層次的畫面、明亮的色彩以及輕快的配樂表現了擁擠的街道、鱗次櫛比的建筑和熙來攘往的人群。畫面不斷來回切換,在屏幕范圍內營造出豐富的景深,從而全方位地勾畫出一幅生機盎然的景象。很明顯,《光明戰士》所試圖表現的是人類社會對災難的超越和克服,充分肯定了人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如果說以《黑客帝國》為代表的好萊塢電影熱衷于涉足啟示錄題材并對人性之惡進行揭露與批判反映了美國社會的群體性焦慮,是一種對其自身社會問題的隱喻和放大,旨在警醒世人、引發深刻反思的話,那么日本動漫則通過一次又一次地展現文明的毀滅及其重生,既傳遞了強烈的主體意識,又消解了災難的破壞性內涵,將其轉化為特定的審美對象,使由現實威脅所帶來的恐懼、憂郁、絕望等負面情感在觀看過程中獲得集中宣泄。
日本中古文學經典《徒然草》一開頭便這樣寫道:“倘若無常野的露水和鳥部山的云煙都永不消散,世上的人,既不會老,也不會死,則縱然有大千世界,又哪里有生的情趣可言呢?世上的萬物,原本是變動不居、生死相續的,也唯有如此,才妙不可言。”這或許正是對“物哀”美學的最好詮釋:頻仍的變故與生死的循環構成了現實世界的本真和人類社會的常態,正因為此,毀滅或“消散”不過是由死到生自然轉換的必經之路,不但不應當畏懼,反倒值得欣賞、玩味,基于這樣的世界觀,人世的災難化作了情趣的載體,而對其進行審美觀照進而領悟其中之“妙”則成了主體擺脫現實束縛、獲致生命達觀的可能途徑。
(責任編輯:帥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