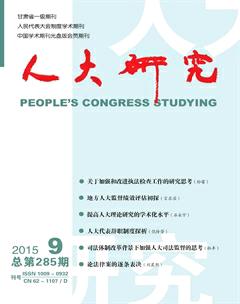人大代表退出機制需要規范運作
王占紅
目前,人大代表退出機制創新實踐在多地不斷推進,有地方甚至在嘗試“責令代表辭職”。筆者經系統翻閱學習相關法律規定,結合自己對相關法理精神的理解,認為“責辭”的主體、條件、程序等關鍵要素,既沒有必要的法律依據,也沒有充足的法理支撐,當謹慎為之。
人大代表作為一種國家職務,是選民或選舉單位通過特定程序選舉出來組成國家權力機關行使國家權力的“法定受托人”,其產生有著嚴格的法定條件和法定程序,其退出自然也必須有充分的法律依據或充足的法理支撐,來不得半點“任性”。應當看到,無論是從體制層面細究,還是從法理角度考量,對人大代表履職優次或職務進退有話語權和終端裁判權的主體,只有選民或選舉單位。也就是說,建立人大代表退出機制,應當把住基本“底線”,對代表職務退出條件和退出程序的設計,在法律和法理上都要能站得住腳。
現行體制框架下,人大代表的退出主要有暫時停止執行代表職務、代表資格終止和罷免、辭職等形式。前兩種退出形式的具體情形和操作程序,以及許可采取限制代表人身自由強制措施的條件和程序,代表法都有具體規定。罷免和辭職的程序法律有規定,但具體條件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根據法律精神和法理原則,代表的罷免應當是“無條件的”,而辭職應當出于“自愿”。
在現行條件下,推行人大代表退出機制,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依法疏通“硬出口”。地方黨委要積極支持有關方面依法定條件程序及時啟動暫時停止執行代表職務、代表資格終止和代表職務罷免程序。另一方面要積極疏通“軟出口”。各級人大常委會應著力探索代表自主退出機制,對因身體等各種原因不能履行代表職責或因工作變動不方便履行代表職責的代表,可由本級人大常委會代表工作部門或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建議人大代表本人提出申請,按法定程序辭去人大代表職務。
(作者單位:甘肅省人大常委會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