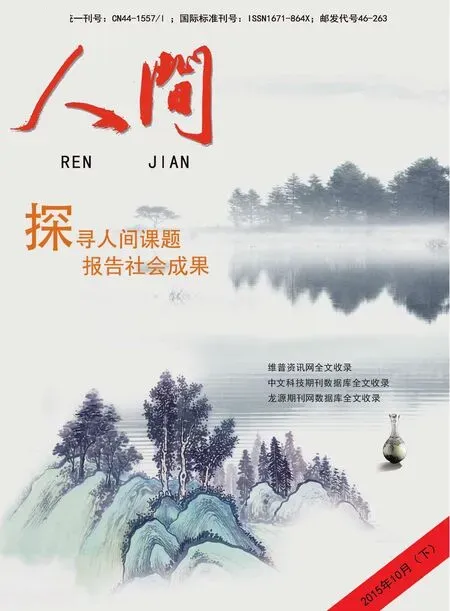如何以藝術行事
——對奧斯汀“如何以言行事”理論的借鑒
顏藝澄
(四川美術學院,重慶 400000)
如何以藝術行事
——對奧斯汀“如何以言行事”理論的借鑒
顏藝澄
(四川美術學院,重慶 400000)
邏輯經驗主義者,也是我們常說的維也納學派這一批學者對于語句的劃分,最為重要的是把語句區分為分析語句和綜合語句。如“五是一個數”,“王老五未婚”等等則是分析語句;“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則是綜合語句無疑。但是,分析語句不需要經驗的確證或驗證,所以我們判斷他們的真假,只是需要看本身這個語句的邏輯關系,是矛盾式抑或是重言式;綜合語句也同樣需要去判定他們的真假,邏輯經驗主義對于語句的檢驗,所設的意義標準都是真假。判定綜合語句的真假,需要經驗的檢驗,如“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無論真假,我們就需要歸納、驗證。如果“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是假,也就是說天鵝的顏色還有別的顏色,不全是白色一種天鵝。分析語句只是需要邏輯地推導,便可判定真假;綜合語句則需要經驗的驗證。
邏輯經驗主義者;奧斯汀;藝術
“現代經驗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是:一個句子作出認識上有意義的斷定,因而可以說它是真的或假的,當且僅當,或者(1)它是分析的或矛盾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說它有邏輯的意義,或者(2)它是能夠,至少潛在地能夠用經驗證據來檢驗的——在這種情況人們說它有經驗的意義”。1
之所以有檢驗、確證,也就是說語言或者綜合語句肯定是得對于世界、事件是描述的層面,我們才能對之進行檢驗、確證。恰恰是早期維特根斯坦,想要構造出理想的人工語言,語言的圖像論,也就是說,確定了語言的描述性質。而在邏輯經驗主義者這里判定語句的意義的標準只有一條,只有真假。邏輯經驗主義的目的、口號是去除形而上學。所以,在邏輯經驗主義者看來,詩歌是沒有真假可言的。
但是,語言除了有它的描述的性質,我們可以經驗求證其真假,同樣語言也還有其他的性質,如情感就不是真假的標準所能限定。所以奧斯汀對語句作了另外的區分。但是首先他也對語言只是描述的理論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即是并不認同語句僅僅只是描述的,要把問句、命令句等句子同陳述區別開來,也絕非易事······因為我們到底如何確定哪個是問句或命令句,哪個是陳述呢?他們各自的界限與定義又如何呢”?2
這就是奧斯汀對于語句的在區分的背景,但是奧斯汀并沒有反駁說語言的“描述”或“陳述”的性質就沒有了,而是要注意到語句除了其“陳述”或“描述”的性質之外,還有其他。所以奧斯汀對語句作了另外的區分:施行式與記述式。
施行式語句的例子是這些:
例一:“我愿意”【I do】(娶這個女人做我的妻子)——在婚禮過程中如是說。
例二:“我把這艘船命名為伊麗莎白女王號”——在輪船命名儀式上如是說。
這些語句就不是具有記述式語句,因為它們都不是去描述一個事件。如例子一就是對某一件行為的表態。例子二則是一個船長或命名人命名權力的實施的過程, 語句的劃分就不僅僅只是記述式的了,還有施行式一類。這樣的施行式語句因為恰恰說出了奧斯汀所說的“如何以言行事”,施行式語句其本身就是行為。而行為就涉及到了倫理、情感、法律等等,就不是像早期經驗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語句更多只是記述式的。對于像奧斯汀剛才所說的對像問句、命令句的區分就很顯然了,這些問句、命令句都是施行式語句。
在藝術史上,我們所看到的很多藝術作品都是寫實主義。在柏拉圖那里,藝術家是再現出現實生活中的椅子,而現實生活中的椅子則是再現出椅子這個概念。所以,古希臘的哲學對于藝術所定下來的基調,幾乎是影響了西方藝術幾千年。文藝復興中的藝術家的理想就是再現模仿論,雖然再現可以是再現出了一座金山,一個神話的故事。他們都是模仿,只不過對于藝術家來說,再現出了現實、歷史情境下的人物、事件,我們都可以將這些作品稱作為寫實主義的作品。 所以,在我們固定的對于藝術作品的感受上,我們是以作品中的形象“像”與“不像”來判定的,就好像經驗主義者中以“真假”來判定綜合語句的。經驗主義者將語句限定在記述的層次;同樣將藝術作品的判定只是限定在“像”與“不像”,也同樣只是將藝術、藝術作品局限于本體論的層面。
表現
如果說一件藝術作品要去表現一個對象,很有可能藝術作品的目的就不是去再現一件事物,那這個時候面對如此的藝術作品,通過經驗的驗證,我們說藝術作品像或者不像某個對象,就不是表現這個概念的應有之義。雖然一件藝術作品可以既是去表現某個對象,也可以是再現某個對象。如德拉克羅瓦的《自由引導人民》就是表現的作品,雖然它再現了某個事件,再現出來自由女神這個形象,在參照模特的情況之下。浪漫主義所具有的激情型,恰恰與當時學院派的寫實主義對立。學院派的寫實主義就是去再現一個對象,它是奧斯汀所說的記述式語句。所以寫實主義的原則是素描,再現事物,更多在于像與不像,根本沒有涉及到行為。而表現這一概念的定義則明顯偏向于施行式語句。無論是德拉克羅瓦的《自由引導人民》,還是藉里柯的《梅杜莎之伐》都是這樣,并不是再現事件,而是對于一個事件的表態,而且也是歷史的過程中之一環。“我愿意”是在結婚儀式過程中,是結婚這個行為的一部分,語句就是行為。浪漫主義的這兩位藝術家的藝術作品同樣也是歷史過程中一環,藝術作品有行為的因素。藝術作品不再僅僅只是記述式語句,像鏡子一樣去再現對象。表現與再現,按照奧斯汀對于語句區分來看,前者就是施行式語句,后者就是記述式語句。
分析哲學領域對于語句的界定、區分,奧斯汀完全走出邏輯經驗主義者的藩籬。我們藝術史也是大致上是這樣的脈絡。前期我們看待藝術作品僅僅停留于像與不像的層面。語言是一面鏡子,藝術也是一面鏡子。當藝術史的進程在發展,現代藝術史上出現了表現主義等等這樣的流派,以至后來有了達達。杜尚展出了《泉》這樣的作品。那這樣的作品如何去分析呢。以杜尚的《泉》為例,我們肯定不是說杜尚去再現了小便池,杜尚根本就是對現成的物品的借用,杜尚將小便池命名為《泉》,就已經說明杜尚根本就不是去再現。如果說杜尚的《泉》就是施行式語句,本身就是行為。那我們怎么去區分定義杜尚的這件作品中的行為。奧斯汀對于施行式語句有著更為細致的劃分,對于藝術作品的劃分、定義興許要更為精致才行。
當藝術不再是記述式的時候,奧斯汀對于語句的劃分,施之于藝術之時,我們同樣也可以歸類出藝術作品那些是施行式的。藝術除了記述、模仿之外,還能做什么呢?如果藝術本身就是行為,事件過程中一部分的話,藝術就是行事。那我們需要就不是關于美的理論,而是政治的理論。“例如,許多施行式是契約式的(“我愿意”)或宣告式的(“我宣戰”)話語3。藝術也可能是這樣。
注釋:
1.洪謙主編《邏輯經驗主義》上卷、商務藝術館1982年第一版、第102頁。
2.奧斯汀著 楊玉成、趙京超譯《如何以言行事》商務印書館 2013年 北京 第5頁。
3.奧斯汀著 楊玉成、趙京超譯《如何以言行事》商務印書館 2013年 北京 第10頁。
H315
:A
:1671-864X(2015)10-0038-01
顏藝澄(1987-)男 ,蘇州人 ,漢族, 學術碩士,單位: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方向:當代繪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