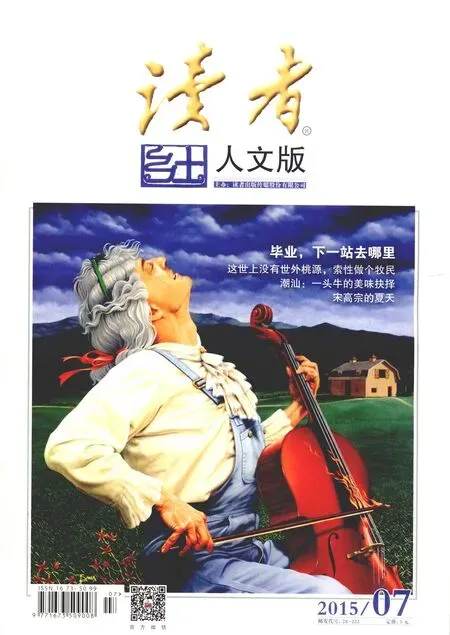你聽,食物的分貝
文/陳曉卿
你聽,食物的分貝
文/陳曉卿

兒子養了一只愛睡覺的加菲貓。貓很安靜,連吃飯都是,含一粒貓糧,慢悠悠地吃下去,沒任何表情,所以我總覺得它病了。“這是優雅好不好?”兒子認為我不懂,“這是美國人培育出的品種,很容易融入人類社會。”
連寵物都懂得優雅,可我是一個懼怕餐桌禮儀的人。每當餐盤里出現了誘人的食物,我總是忍不住想撲將上去,但環視四周,全是“杰克李”—節制、克制、理智的人。強忍著沖動,改成一口一口賊兮兮地吃,這時候,心中總不免嘮叨一句:“唉,‘不及林間自在啼啊’!”
作為社會性動物,人越來越遠離自己的自然屬性。想起有一年,參觀BBC的動物攝影棚,聲音制作線正在為野生動物擬音。錄音師介紹說:“一般來說,大型兇猛動物,撕咬食物的聲音很大,囂張且伴隨歡快呻吟和低頻口腔共鳴。從食物鏈上看,處在頂端的,后期擬音時要故意夸張一些;而處于末端的,我們會故意壓低它們吃東西的動靜,以便于觀眾理解動物特性。”
聽到這兒我樂了,人是萬物之靈,處于食物鏈最頂端,但人類進餐為什么卻要盡量低調呢?
幾乎所有的食物享用過程都伴隨著聲響。人類的齒間可以通過感受的細微差異,區分脆、韌、酥、沙、綿、糯等口感或牙感。即便脆,又分蔬果類汁水豐盈的鮮脆、油脂烹炸食物的香脆、焗烤谷物類的焦脆、烘焙類點心的酥脆、炒制干果的生脆、漬制脫水腌菜的柔脆……天哪,多到不勝枚舉。
脆,大都與食物纖維脫水有關。有些蔬菜,比如青菜頭,直接吃澀口,但不知從何時起,人們嘗試用腌漬的方式處理它,菜頭不僅鮮美可口,而且還多了一種脆韌。可以想象,我們的祖輩當年得到這種美妙口感時有多么驚喜。最好的涪陵榨菜,一定是先風干脫水的(不像有些工業榨菜,直接用鹽脫水),這和巴蜀講究些的人家做泡菜是一個道理。
我的家鄉有一種叫“苔干”的脫水蔬菜,據說有千年歷史,和榨菜一樣脆,但不用鹽腌,而是直接晾曬。吃之前,放在溫水中浸泡,菜迅速原地滿血復活,老家人管它叫“貢菜”,也有叫“響菜”的,可見動靜之大。
中國菜肴里更是不缺少與脆相關的美食,松鼠鱖魚、三鮮鍋巴、宮保雞丁,還有著名的爆雙脆,烹飪方法無論是炸、爆、煎、烤、焗,每一種都能獲得不同脆的口感,同時無不伴隨著強烈的誘人聲音。美食家們不得不挖空心思,尋找一些詞匯與之匹配,普通一點兒的說“外焦里嫩”,文藝一點兒的形容“裂帛”“嚶嚀”……我很幸運,因為我做影視,可以直接把聲音記錄下來。
但電視里的食物聲響顯然是經過處理的,比如《舌尖上的中國》里的油爆河蝦、炸豬排、蒿子粑粑,在入口時,都被聲音工作站模擬成“耳鼓接收的聲音”。因為我們咀嚼和吞咽美味的聲音感受,是由口腔直接傳導到耳鼓,而不是通過空氣振動傳遞到耳膜的。這就是“看(聽)別人吃東西,永遠沒有自己吃東西美味”的原因。在節目里我們模仿的,恰恰是個人進食的感受。
當年我拍另外一部野生動物的紀錄片,請了一位新西蘭的大腕兒指導,叫邁克爾,在講聲音的時候,他透露了這個秘訣,這和BBC的聲音制作理念類似。他打趣說:“模擬耳鼓的聲音是在現場看球,否則只相當于看轉播。”邁克爾的說法,讓我想起童年的一件糗事。
老家有一種點心—芙蓉果,類似江米條,但更大,芯兒蜂窩一樣綿密,外面通體油炸,而且掛著糖霜。和鄰居家的老三玩兒,她吃著這種果子,一點兒分享的意思都沒有。我只好提醒她:“這東西,脆不脆?”老三把最后一塊放進自己的嘴巴,一邊嚼一邊說:“很脆呢,不信你聽?”
(白寧靜摘自《南都周刊》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