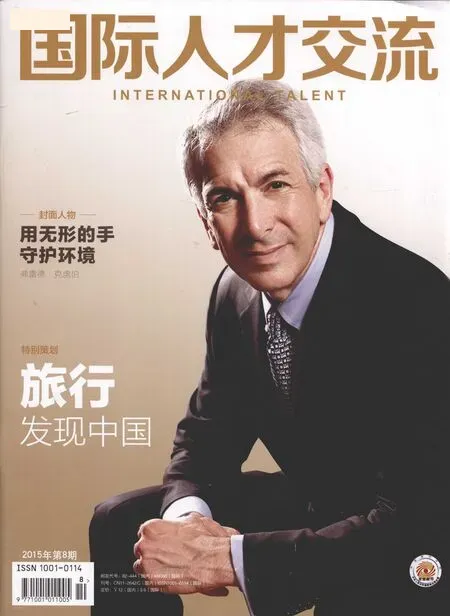一位華裔學生在中國的助教經歷
文/韓琳
一位華裔學生在中國的助教經歷
文/韓琳

課堂上,美方師生與中方教師一起練習中國畫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雖然我父母都是二十幾歲才從北京移民到加州,我自己也長得像個典型的中國年輕人,但我總認為自己是一個美國人,這在我住的硅谷并不算稀奇。我上的是以亞裔學生為主的美國學校,交了像我一樣的第二代亞裔朋友,在家我和父母講中文,加上每星期上中文課。我以為這就是地道的美國生活。
但近兩年來我在中國的經歷讓我覺得事情遠遠不是這么簡單。
在上高一和高二前的暑假,我參加了America China Exchange(ACE)夏令營。ACE是江蘇省和加州舊金山灣區中學的學生和老師交流的項目,但參與的學生和老師并不局限于學校。
每年暑假,會有15名美國師生到中國,教中國老師和三至五年級學生英語。另一方面,美國老師和學生也向中國老師學中文,到當地人家中做客,參與文化交流活動。
我在江蘇省江陰市峭岐實驗小學當助教。在為期3周的夏令營中,我們美方老師和助教舉辦了從讀書到手工制作的英語課。而10位美方助教中,只有兩位是華裔美國人,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位是我的室友。
幾年前第一次聽說ACE我就很好奇。雖然我去過北京好幾次,卻從來沒有交到除親戚之外的朋友,所以我盼望和中國小孩交朋友。我在家人包圍下的北京體會到的中國,與我在峭岐所經歷體會到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國的學校,交換生從來都沒有受到過這么隆重的迎接,這種歡迎方式是給那些名人和政客的
夏令營見聞
夏令營的第一天早晨,我們很早就起來了,又困又興奮地登上了去學校的汽車,期待見到要和我們交流的學生。在前往學校的路上,我們離開入住的江陰市區,進入了峭岐小鎮。在清晨的陽光下,勞動的農民點綴在我們路過的稻田里。在離江陰市僅半小時車程的峭岐鎮,高樓變成了陳舊的房屋和商店。這和美國那充滿了星巴克、連鎖超市以及新技術的世界截然不同,然而這樣的現實使我對中國的認識變得更加清晰了。
走進學校時,看到了非常熱鬧的一幕:很多父母帶著孩子,3個人擠在一輛電動車上去學校。夏令營開始的第一天,我們都特地選擇穿著紅色衣服,以為這是入鄉隨俗之舉,學生們排成兩隊在學校門口迎接我們。當我們走過時,他們一邊舉起手里的花一邊說:“歡迎!歡迎!”在美國的學校,交換生從來都沒有受到過這么隆重的迎接,這種歡迎方式是給那些名人和政客的。
我們團隊的基本任務是教中國學生英文詞匯和發音,并培養他們對英語的學習興趣。在我看來,ACE不單單是與中國助教和學生進行交流,而且是進一步交換想法并和他們建立長久的友誼。
我們在峭岐實驗小學的教室里,第一個任務是搬課桌。我們把原來整齊而獨立排列的課桌并在一起,7張課桌一組。這樣,學生在課堂上就不僅僅是與老師交流,彼此之間也能面對面地互動:對中國學生來說,這本身就是一件新鮮事。
3個星期過得很快。學生從8到10歲不等,每個年級的學生無論是個性、學習勁頭還是英文水平,都有著差異。學生們跟著“The Hokey Pokey”(一首經典的英文兒歌)的節奏邊唱邊跳、聽我們助教朗讀Dr. Seuss在1957年的經典作品《戴帽子的貓》、和我們玩“我說你做”的游戲。從這些活動中,學生們學會了身體部位和家用物品方面的詞匯,以及如何用英文表達指令。
我所遇見的文化差異
在課堂上,我注意到了中美文化的一些差異。比如老師和學生的關系,中美之間就有很大的不同。就我的觀察,中國學生對老師更尊敬,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都是恭敬地遵從老師的指導。這可能跟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系,中國的傳統注重權威的高低順序,比如小孩得尊敬父母,學生得尊敬老師等等。而在美國的學校,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系沒有那么嚴肅,更有點像朋友的關系。學生在課堂上和老師開玩笑,老師也可以和學生開玩笑,而且我們在補習時間和課后,會跟老師聊聊天。例如有一次在學校里,我的老師告訴我們,他的未婚妻問他是更喜歡她還是學生,老師說他更喜歡我們學生。我們立刻歡呼起來,同時一個學生開玩笑說:“看樣子有人的婚禮要取消了。”
另一方面,在課堂上,峭岐小學的學生通常比美國學生更加謹慎。舉例來說,我們在課上教英文時,學生們不敢試著念出一個沒有學過的單詞的發音。在閱讀練習時,我讓小組學生們大聲地念出來,直到他們因為生字停頓下來。我就領著他們練習每個音節的發音,即使是在念對了每個音節的情況下,他們還是不敢試著完整地念出整個詞。根據我的經驗,在美國,老師會鼓勵學生大膽說出自己的推測。老師對錯誤答案和對正確答案的重視程度是差不多的,因為這證明學生在嘗試著了解和運用所獲得的知識。而在峭岐的課堂上,當學生不知道正確答案的時候,不管我怎么勸說,他們往往都不肯猜。根據我的觀察,也許這是因為中國老師通常會向學生提供所有正確的答案和知識。學生基本上只用吸收和掌握這些知識,而不需要自己去得出結論。因此,峭岐小學的學生開始時很不適應西方的教育方式。
由于我們把大約30個學生的一個班分成幾個7人左右的小組,一段時間后,學生們變得更有意愿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并且對自己能力和信心也增強了。另外,學生們也更愿意說英文了,并試著在平時也用英文交流。這時我才發現他們平常在課堂上學的都是英式英語。一次課堂上,學生問我她是否可以去上廁所,她英文說的是“WC”。我當時沒聽懂她要干什么,幸好我身邊的另一位助教聽懂了。

英語閱讀課上,交換生與學生們在一起
中國人?美國人?
因為我的中文還算流利,并且長著中國人的面孔,所以學生們對我格外熱情。我們常常在課間和課后聊天,彼此之間變得越來越熟。我們一起開中英文結合的雙語玩笑。一個五年級的學生最有趣:他伸著4個勾著的手指,宣布是“彎的four”(wonderful)。我還學了些漢語的俚語。我對“超”這個詞一見如故,從飲食(“超好吃”)到觀光(“超好玩”),用得不亦樂乎。通過練習,我的中文語句變得更流利了。每一天下課時,學生們都像我一樣,舍不得離開。女生會擁抱和親一下我們的臉蛋,而男生都在門前排隊,為和我們熱情地擊掌。
直到后來我才發現,他們一直把我看成是和他們一樣的中國人。因此他們疑惑不解我為什么總是把自己說成是“美國人”。
“姐姐,”一個小女生課前忽然問道,“如果你是美國人,為什么頭發不是金黃色的?”我笑了,然后才意識到這是一個嚴肅的提問。我立即說明了我的中國血統,但是學生還是不懂。
“你就是中國人呀!”她回答。
我在江陰居住時,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吃完晚飯,我的華裔美國室友和我叫了個出租車。坐在車里,我們自動換成用英文聊天,然而司機覺得特別奇怪。當司機問到我們是哪里人,我們回答是美國人。
“美國人?”他半信半疑,并從后視鏡掃了我們一眼,“怎么會呢?”
這時我已經在峭岐小學經歷過好多相同的問題,所以我再一次解釋:雖然我的父母在中國出生,但是因為我在美國出生,所以我就是美國人了。我以為他會理解,畢竟他不是小孩,應該能明白這件事。
然而他不容置疑地說:“不可能。沒這種事!”他似乎無法把我們看成美國人。
經歷了這兩個暑假,我才開始琢磨:我到底算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顯然,我是兩者兼有,然而現在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并不那么重要了。我已經不能簡單地用種族或文化以及國籍來定義。除了這些以外,我還是一個小作家、一個小畫家、一個校隊的跑步運動員;我是一個高中生、一個女兒和一個姐姐。是的,我喜歡吃中餐也愛西餐,跟我父母說中文,跟我朋友說英文,喜歡讀《射雕英雄傳》和《哈利·波特》。在某種程度上說,Irene Han(我的英文名字)和韓琳代表了我的兩個身份,而在你眼中我是誰,其實只由你的觀念決定。
天津
外國專家參加中國傳統文化體驗活動

文化體驗活動現場
近日,30余名外國專家及外國留學生參加了由天津市外專局和天津市國際人才交流協會舉辦的“天津市外國專家中國傳統文化體驗活動”。此項活動在樂琪英語培訓學校第七培訓中心舉行,并得到了樂琪英語的大力支持。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的38名外國專家以及部分非洲和東南亞留學生踴躍參加本次活動。活動中,外國專家親身體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學習如何包粽子,并品嘗了體驗成果。活動在有獎知識問答、游戲、猜謎的歡樂氣氛中結束。外國專家紛紛表示,非常喜歡參加此類中國文化體驗活動。(天津市外國專家局供稿)
嶗山
“田園計劃”引來德國工程師

德國工程師西蒙(左二)與志愿者們純手工打造一臺風力發電機
在嶗山的一個村子里,一對80后年輕夫妻唐冠華和邢振創建了一個名為“自給自足實驗室”的天然模擬生活區,他們自己發電、自己凈化污水……他們希望達到的理想狀態是:在山間自力更生。他們把這種生活方式起名為“家園計劃”。
近日,德國工程師西蒙主動找上門。作為唐冠華“田園計劃”的一個實驗項目,西蒙帶領招募來的志愿者用木頭、鐵管等材料純手工打造一臺風力發電機。
“我學士學位是環境資源管理,碩士學位是可再生能源科技,對這種環保生活特別感興趣。”專程從北京趕來青島的德國工程師西蒙說,自己獲得碩士學位后在北京的中德政府合作項目可再生能源部門工作,從網上了解到唐冠華的“家園計劃”后,主動聯系到了唐冠華。“我的一個好友是專門研究自制風力發電機的,還專門寫了一本教程,我和他一起做過風力發電機,所以這次我來領頭帶著這些志愿者一起做。”西蒙說,他的朋友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風力發電機手工制作專家,他的風力發電機自制計劃具有實際操作性。(青島市外國專家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