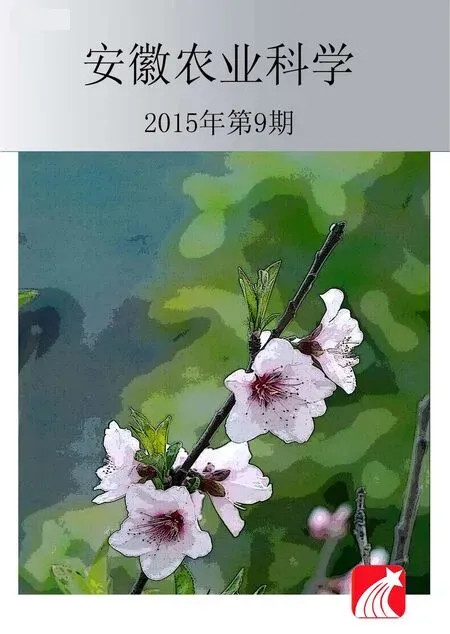民間法與農村社會糾紛解決
趙小浪, 張曉萍
(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黑龍江哈爾濱 150040)
?
民間法與農村社會糾紛解決
趙小浪, 張曉萍*
(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黑龍江哈爾濱 150040)
農村社會糾紛與民間法有著“天然親和”。正是在法官對大小前提的建構過程中,為民間法適用農村社會糾紛打開了通道,而從提升法治認同感和維持農村社會秩序的角度,民間法的司法適用,也有著重要的法制意義。特別是在農村社會婦女土地權益問題、彩禮問題、相鄰關系問題等具體糾紛中,民間法的重要作用越發凸顯。
民間法;農村社會糾紛;司法適用
1 農村社會糾紛與民間法概述
“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土社會的特征之一是鄉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代的傳下去,不太有變動。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1]。”這是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教授所傳達的理念。時至今日,我國農村社會還是一個“熟人社會”。熟人之間相處更多以情感為要素,更為看重“關系”,他們堅信情感因素會降低交易的成本。其交往中的側重點以精神利益為重,物質利益從屬于前者。在熟人交往之間,會盡量避免因物質利益而傷“和氣”,這就是農村社會糾紛中的重要特點:物質利益從屬于精神利益,利益原則低于情感原則[2]。法治是一種實踐的事業,農村社會糾紛這種“熟人化”的特性,需要相應的規范作出回應。
按照功利主義道德的基本觀點,法律規范在本質上是利益的規范表達,商業化和市場化所帶來的大量的陌生人之間的大規模流動,是它所建立的根基。法律規范的運行機制——就是通過分配權利和義務,調整人們利益上的平衡而維系市場主體交往的秩序和功利時代的道德(功利型道德)[3]。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促進陌生人社會中法律規范繁榮的重要原因。因此,陌生人關系越復雜,法律規范的作用就越突出。在市場經濟中,陌生人之間交往的重要紐帶,就是契約。陌生人訂立契約的核心追求,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特別是物質利益的最大化。基于以上原因,使得在農村社會糾紛解決中,國家法的介入顯得很難為情。
與此相反的是,民間法的調整機制總會照顧到熟人情感的需要。民間法調整機制的核心在于以熟人之間情感的維系為解決糾紛的基本前提或先導。顯然,農村社會的糾紛與這樣的調整規則,有著天然的“親和”。總而言之,對于農村社會的熟人糾紛而言,以利益關系為核心的國家法,不易被接受。而以情感關系為核心的民間法,反而更為容易被糾紛雙方所選擇。
2 民間法適用農村社會糾紛的法理和實踐基礎
2.1 民間法適用的法理基礎民間法與司法實踐的鏈接,十分廣博,難以全面闡述。故筆者擬以“民間法與法律方法之間的關系”[4]這一角度出發,在分析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對大小前提的建構的基礎上,探討民間法在農村社會糾紛中的司法適用。
一般認為,法官在進行司法審判的時候,將所需適用的法律列為大前提,庭審過程中查明的案件事實列為小前提,司法判決就是法官根據大小前提間的邏輯推理所獲得的。但法律條文繁多,各個條文間還可能存在著眾多競合關系,案件事實更是繁紛復雜,大小前提都不會自動擺放在法官面前。司法審判需要法官建構大小前提,而正是這個過程,為民間法進入司法實踐打開了通道。
2.1.1民間法通過法律解釋進入司法實踐。一般而言,在法律解釋方向上,有兩種代表性觀點,即主觀論和客觀輪。前者以探究立法者心理意圖為方向,后者則以分析法律的現實意義為落腳點;前者強調法律的解釋應注重立法者的意志,后者則認為法律解釋時應以法律在客觀現實中的固有實效為依據[5]。但在一定意義上而言,“法律解釋的最終目標是:探索古老的法律在今日的社會現實條件下的標準意義,而不是完全忽視某一點。[6]”以法律解釋的具體方法為例,如刑法上的“猥褻”、“淫穢”、“暴力”等語詞,在對其進行文義解釋的時候,則須時常參照語言習慣及相應的習慣法則。
2.1.2民間法作為經驗法則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民間法可以成為法官構建大前提的基礎,但如何構建小前提,對司法實踐來講也是極為重要的命題。司法中所認定的事實,是通過分析證據所證明的案件事實,亦即合乎程序法和證據法的事實。但證據只能證明庭審中的程序事實,但是在真正涉及案件實體問題時,證據則無能為力[7]。
但民間法基于其自身具有的經驗法則,完全可以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一定程度上,民間法會在人們的思維中形成定勢,并在其效力范圍內決定著人們的行為習慣。正如學者指出:“在一定區域內,習俗會嚴格約束著群體的行為,如果有人不依習俗行事,他將會被視為異類,會被其他成員孤立。如此,生活于習俗中的成員會不自覺的在這種內在的信念和外部壓力的雙重作用下,嚴格按照習俗行事。也正因為如此,通過認知習俗,也就可以在認定案件事實時,用以證明當事人在案件事實中的所作行為的可能性,幫助法官準確的認定案件事實,建構司法判決中的小前提。[8]”
2.2 民間法適用農村社會糾紛的實踐基礎
2.2.1適用民間法有利于提升農村社會的法治認同感。法治的普遍認同,就是指公眾因法律能夠順應其價值期待而認可法律,對制定法的普遍認同[9]。在法治認同較高的社會,人們遵守法律不是因為畏懼,而是已經形成了對法律的信賴。但就目前而言,我國農民對法律規范的認同程度偏低。農村地區多數農民只有在其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同法律打交道[10]。而提升農民對法治的認同,關鍵在于利益的感召。即相對人可以在法律規范中找到其熟悉的存在,法律對于其本身不再是冷冰冰的存在,不再是統治他們的武器。這就要求從“本土資源”中挖掘立法的養料。
2.2.2適用民間法有利于維持農村社會秩序。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習慣和慣例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有時候這種作用是超越法治的。因為在上千年的過程中,農村社會已經形成了一種自覺維持其自身運行的慣性。而現在一直在呼吁的法治,在立法文本中,除了大量的法律移植,剩下的其實更是對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習慣的認可。所以,就農村社會秩序這一角度而言,樸素的民間法有著法治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處理農村社會糾紛問題時,完全不應也不能忽視民間法維持農村社會秩序的功用。
3 民間法適用農村社會糾紛的具體體現
3.1 婦女土地權益問題我國《土地承包法》對婦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專門的規定,在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時,不得歧視婦女。但是,就目前現實情況而言,鄉土性濃厚的農村社會中,婦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并沒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對此種問題再進行更深一步的考量,其根本不在于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上立法的缺陷,而是由于農村當地重男輕女及其他自然、歷史文化遺留下來的民間習慣法在這一問題上與國家法的對抗,使得具體的規范難以執行。因此,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從執法上入手,而前已論述,欲在我國農村地區提升法律的執行力,就需要提升農民的“法治認同”感。所以,將民間法規范納入整個司法活動中,或許成為司法部門應該認真考量的因素。不是依靠人的理性空泛的制定出一套理想中的法治藍圖,而是應該充分認知和理解農村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民間法,理解此種規范存在的現實意義,將其有益部分吸納入法治軌道中。
3.2 民間彩禮糾紛問題我國《婚姻法》對于婚約和彩禮并無明確規定,但是在我國得農村地區卻廣泛存在著訂立婚約并給付彩禮的習慣。隨著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婚約給付彩禮數額更是急劇增大,隨之而來的農地彩禮糾紛案件的標的額逐年膨脹。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解釋”的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二)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適用前款第(二)、(三)項的規定,應當以雙方離婚為條件。”這項司法解釋為各地法官審理彩禮糾紛案件時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但這只是一項較為原則的規定,對于具體案件來講,彩禮是否應當返還及應返還多少,法律并無具體規定。這既賦予法官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又給法官造成了很大的困擾。特別是婚約關系的地方特色極其鮮明,這也給實踐中“指導性案例”的運用也造成了困擾,同案同判基本不太可能。因此,各地法官在面臨此類糾紛時,民間法的適用自然成為了首選因素,特別是我國《婚姻法》規定,離婚案件必須調解,法官在調解的過程中,在不違反強行法的基礎上,民間法在化解“熟人”矛盾的作用上,優勢鮮明[11]。
3.3 相鄰關系糾紛問題面對繁紛復雜的現實中的相鄰關系矛盾,特別是在廣大農村社會,相鄰權爭議雙方基本是發生在“熟人”之間。以“利益關系”為調整手段的法律,面臨此種問題,常常“成本高昂”。《物權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處理相鄰關系……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的,可以按照當地習慣。”這就為民間法在相鄰關系適用的問題上打開了通道,民間法成為了處理相鄰關系爭議的重要依據。我國民間本就有“遠親不如近鄰”的習慣,將民間法適用在相鄰關系的爭議問題上,更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相鄰權本就是從民間習慣中產生的,農村社會糾紛的“熟人化”特征在農村相鄰關系爭議上體現的更為明顯。此時,農民對民間法的認同就更為強烈,而這也就要求法官“認真對待民間法”。
[1] 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85:17.
[2] 謝輝.論民間法與糾紛解決[J].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1(6):40.
[3] 汪潤生.西方功利主義倫理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17.
[4] 謝輝.初論民間規范對法律方法的可能貢獻[J].現代法學,2006(5):28-37.
[5] 張曉萍.在司法中民間法與法律方法的勾連[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6):67.
[6] 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出版社,2003.
[7] 鄭永流.法律判斷大小前提的建構及其方法[J].法學研究,2006(4):51.
[8] 韋志明,張斌峰.法律推理之大小前提的建構及習俗的作用[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67.
[9] 李春明,王金祥.以“法治認同”替代“法律信仰”[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6):109-115.
[10] 劉立明.民間法與農村社會的法治啟蒙[J].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110-113.
[11] 張曉萍.在司法中民間法與法律方法的勾連[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6):70.
The Theory of Folk Law and Rural Society Dispute Resolution
ZHAO Xiao-lang, ZHANG Xiao-ping*
(Institute of Grammar,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There is a natural affinity between dispute of village society and folk law. It is becau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emises by the judge that makes the folk law a possible way to solve the dispute of the villag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law and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order, the adaption of the folk law have a great sense in law. And the folk law is making more and more contributions, especially in some specific disputes like women's right to land, neighbours' relationship, betrothal gifts, and so on.
Folk law; The rural social disputes; Judicial application
2014年度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法治視野下的“社會規范失靈”問題研究》(14B004)。
趙小浪(1993- ),男,陜西安康人,本科,專業:法學理論,民商法。*通訊作者,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2015-02-06
S-9
A
0517-6611(2015)09-36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