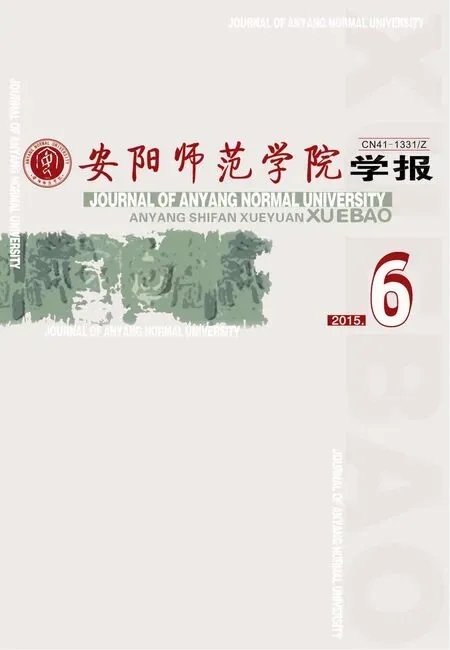中國新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形象
李興陽,朱 華
(1.湖北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2.湖北師范學院 美術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中國新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形象
李興陽1,朱 華2
(1.湖北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2.湖北師范學院 美術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中國形象是晚清以來中國新文藝現代性建構的重要內容。晚清至民國初期,以報章小說為主的中國文藝所塑造的中國形象可概括為“過去之國”、“未來之國”和“新生之國”三大類型;“五四”至1949年,中國各類新文藝所塑造的中國形象可以概括為“病態中國”、“青春中國”、“革命中國”、“都市中國”、“鄉土中國”和“戰時中國”等六個類型;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各類新文藝所塑造的中國形象可以概括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文革中國”、“改革開放之中國”、“現代中國”、“世俗中國”和“東方化中國”等六個類型。中國新文藝在不同歷史時期塑造出的中國形象,具有不同的國家形態與時代精神,這是近百年來中國國家形象歷史演變的現實投射與新文藝家們主觀想象的藝術之果。
中國新文藝;民族國家想象;中國形象
中國形象是晚清以來中國新文藝現代性建構的重要內容。這里所謂的中國新文藝,是指晚清至今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報章小說、戲劇、詩歌、散文、舞蹈、音樂、電影、電視、繪畫、雕塑、攝影、書法和建筑藝術,等等。中國自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在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炮與鴉片毒品的夾攻下走向衰亡開始,歷經近代、現代和當代的百年滄桑巨變,由一個傳統的王朝國家逐漸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中國的國家形象在百年歷史演變的每個階段都有新的變化,都呈現出不同的形象特征。與之相應的,中國新文藝在不同歷史時期塑造出具有不同國家形態與時代精神的中國形象,即如有論者所說:“中國形象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作家和詩人們總是從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國。”[1]
一、清末民初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形象
晚清至民國初期,是中國由封建王朝國家被迫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歷史大變革與過渡時期。在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里[2],晚清至民初的小說與報紙“為‘重現’民族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提供了技術上的手段”[3]。以報章小說為主的中國新文藝及傳媒所塑造的中國形象,可概括為三大類型:
其一,“過去之國”[4],指正漸趨衰亡的晚清王朝。鴉片戰爭之后,曾經的“中華帝國”陷入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無論是整體的綜合國力還是國家的客觀形象,都一落千丈。劉鶚的《老殘游記》把貪污腐敗、苛政如虎的晚清王朝喻為航行在太平洋上即將沉沒的“危船”;曾樸的《孽海花》也把昏庸無能、積貧積弱的晚清王朝喻為“陸沉奴隸國”和“陸沉奴樂島”;陳天華《獅子吼》把朝廷昏庸國人渾噩備受外敵欺凌賠款割地的晚清中國比作“混沌國”,這“混沌國”曾經轟轟烈烈做過,輝煌過,后來為自古流傳下來的忠君邪說所害,衰敗了,被蠶食國、鯨吞國、狐媚國蠶食分割,竟至滅國;又比作“睡獅”:“原來此山有一只大獅,睡了多年,因此虎狼橫行。”即將逝去的王朝在這里留下了殘破的舊影。
其二,“未來之國”[4](P9),是晚清新知識分子想象中的理想中國,亦即以西方民族國家為參照所構想的新型國家,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將其稱之為“新中國”。吳趼人的《新石頭記》、陸士諤的《新中國》、蔡元培的《新年夢》、陳天華的《獅子吼》(未完成)等小說也都圍繞“新中國”而展開對未來中國的想象與形塑。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梁啟超設想的是未來的“西歷兩千零六十二年”中國建立起了君主立憲制國家,已發展成為世界強國,于是各國都來參加在上海舉辦的世博會,“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偌大一個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好一幅國家富強、科技昌明、學術發達的盛世圖景。在《新石頭記》中,吳趼人讓賈寶玉再度入世,尋求救國救民創建民族國家的救世良方。賈寶玉終于看到中國立憲已成,“不到幾時,中國就全國改觀了。此刻的上海,你道還是從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權也收回來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開了商場,一直通到制造局旁邊。吳淞的商場也熱鬧起來了,浦東開了會場,此刻正在那里開萬國博覽大會。”上海世博會也盛況空前,“各國分了地址,蓋了房屋,陳列各國貨物。中國自己各省也分別蓋了會場,十分熱鬧,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說不盡多少。”在《獅子吼》中,陳天華設想了一個作為“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雛本”的“民權村”,村里“有議事廳,有醫院,有警察局,有郵政局。公園,圖書館,體育會,無不俱備。蒙養學堂,中學堂,女學堂,工藝學堂,共十余所。此外有兩三個工廠,一個輪船公司。”[5]這是一個袖珍版的現代民族國家。“民權村”中的“豪杰”不滿足“新村”實驗,“后日競把中國光復轉來,變為第一等強國。”[5](P36)晚清小說想象中的“新中國”,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國體、政體和國計民生等方面都呈現出現代民族國家特征。
其三,“新生之國”,指民國初年時的中國形象。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新的共和制國家——中華民國正式成立,想象中的“新中國”已然變成了現實。但“辛亥革命所帶來的清王朝的覆滅,并不意味著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壓迫、由此提前發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滿的民族主義三種力量重合的結果。在中國的土地上,遠未來得及產生足以支撐民主共和國制度的經濟結構、社會階層和思想文化。”[6]這使民國初期文學對“新生之國”的想象,遠不如晚清小說對“未來之國”的“新中國”的想象那么清晰而熱烈,充滿了失望、憤懣和哀婉。李涵秋的《廣陵潮》、朱瘦菊的《歇浦潮》、平襟亞的《人海潮》、包天笑的《甲子絮譚》、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等作品,都對民國初期軍閥混戰、社會混亂、災難頻仍、民不聊生等殘酷的社會現實有逼真的敘述,對國民麻木愚昧、人性扭曲、道德墮落等也有揭示。民國初期文學對“新生之國”的現實描述與敘事想象,重現了“過去之國”的舊影,展現了“未來之國”的理想被無情擊碎的冰冷現實,起到了促發國人覺醒,開啟思想文化啟蒙的歷史作用。因而,也可以說是“五四”新文藝在“民主”與“科學”的現代性維度上重塑“中國形象”的歷史預演。
二、現代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形象
“五四”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形態在啟蒙、革命與救亡的時代變奏中,不斷重組、變換和轉型。在歷史中抉擇而又在抉擇中變幻不定的中國,呈現出自身形象的多個側面與不確定性。在血與火的年代里,想象中國的方式,不僅有小說、報紙等比較傳統的“技術上的手段”[7],而且出現了電影、廣播、話劇等新的技術手段和傳播媒介。以小說、戲劇、電影等敘事性文類為主的中國文藝及傳媒所塑造的中國形象豐富多彩,類型多樣。而其最重要者,至少可以概括為如下六個類型:
其一,“病態中國”,這是啟蒙話語形塑的中國形象,是與啟蒙話語理想中的現代民族國家相悖的國家形象。在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比照下,那個時代的中國,其病態是多方面的,而最突出者就是國民劣根性。國民的精神疾患之一就是在長期的封建王朝統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識,缺乏“公民”意識與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梁啟超講要“新國”必先“新民”,魯迅講要“立國”必先“立人”,而“新民”和“立人”的重要內容就是要通過啟蒙,讓國民形成公民意識與現代民族國家觀念。老舍曾經說:“‘五四’送給了我一雙新眼睛”,“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做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做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后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8]如其所言,民族國家意識貫穿在老舍的《二馬》、《趙子曰》等作品中。如《趙子曰》中的理想國民李景純走的就是思想啟蒙與救亡圖存道路,他教導趙子曰們要為國為民學好真知識,要有真本事,要有民族自尊心,要有國家觀念,要愛國:“我們的人民沒有國家觀念,所以英法聯軍燒了我們的圓明園,德國人搬走我們的天文臺的儀器,我們毫不注意!這是何等的恥辱!試問這些事擱在外國,他們的人民能不能大睜白眼的看著?試問假如中國人把英國的古跡燒毀了,英國人民是不是要拼命?不必英國,大概世界上除了中國人沒有第二個能忍受這種恥辱的!所以,現在我們為這件事,哪怕是流血,也得干!引起中國人愛國心,提起中國人的自尊心,是今日最要緊的事!”[9]
其二,“青春中國”,這是李大釗呼喚的理想中國,是受“五四”啟蒙精神洗禮的中國,是郭沫若詩歌、巴金小說等文藝作品中想象的新中國,是“病態中國”浴火重生的有朝氣有活力有希望的民族國家。在郭沫若的詩歌《女神》中,祖國是令人無比眷戀的“年青的女郎”,是令人常常思念的“故鄉”,是“集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的鳳凰。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從封建之《家》中突圍而出,投身到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時代激流中,雖然免不了傾軋、斗爭和悲劇,但洋溢著濃郁的“五四”青春氣息。
其三,“革命中國”,是現代中國文藝塑造的國家形象最突出的一面。革命是近現代中國不得已的歷史選擇,“近現代中國革命者所謀求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中國的富強,即現代化。在他們走上革命道路之前,或最終決定以暴力手段推翻現政權時,都曾對改良或漸進的道路寄以希望,如甲午戰爭之前的孫中山,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共產黨。但是,嚴酷的現實使他們認識到這條道路是不可能通達中國富強的目標的。舊政權的腐敗、面對現代化挑戰的無能為力、帝國主義影響的根深蒂固等等,促使他們最終認識到,唯有通過革命的手段,推翻舊體制,擺脫列強的控制,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才有可能最終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建立獨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是現代化的必要前提。”[10]中國近現代文藝的“革命敘事”也是感應歷史的敘事選擇。不同歷史時期的“革命敘事”所塑造的“革命中國”是不一樣的,如在中國早期新聞紀錄電影《武漢戰爭》和《上海戰爭》這兩部“多少紀錄了一些有關中國人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英勇斗爭的史實”的影片中[11],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歷史舊影;在蔣光慈的小說《短褲黨》中,可以看到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歷史圖景;在歌劇《白毛女》中,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給中國鄉村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革命中國”是近現代中國追求民族獨立解放和富強的歷史寫照。
其四,“都市中國”,是現代中國形象中最為遲滯的一面。但都市現代化是中國這個傳統農耕文明悠久的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最大、最深刻的“中國經驗”,也是最早同時最具有未來意義的“新中國”想象。在晚清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梁啟超)、《新石頭記》(吳趼人)和《新中國》(陸士諤)等作品中,都以幻想中的未來上海“世博會”極顯未來新中國的富強,“都市中國”在這些作品中成為“新中國”的理想圖景。在中國現代文藝的都市想象中,“都市中國”有多副面相,如“現代都市”、“病態都市”、“傳統都市”等。在“新感覺派”小說中,晚清小說想象的“現代都市”已然更加現代,活動在那里的都是跟著感覺走的“時間不感癥患者”;在沈從文小說《八駿圖》中,都市具有戕害健康生命的“閹寺性”,同樣的“都市病”在張愛玲小說中有更冷冽的表現;在老舍的小說《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傳統都市”日趨崩塌的歷史暗影;在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中,可以看到都市不同階級之間的搏殺與中外資本之間的纏斗;在電影《都市風光》(袁牧之編導)里,則可以直觀地看到“舊中國半殖民地都市社會的畸形怪狀”[11](P392)。值得玩味的是,代表現代工商文明發展成就的都市,甚至被想象為現代民族國家發展方向的都市,在中國現代文藝作品中幾乎總是以負面形象出現。
其五,“鄉土中國”,是正在逝去的農耕文明的留駐地,是追求現代化的中國最大的疼痛。在中國現代文藝作品中,“鄉土中國”也有多副面相,如“病態鄉土”、“革命鄉土”、“純樸鄉土”、“翻身鄉土”等。在以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等為代表的“五四”鄉土小說中,可以看到啟蒙話語燭照下的“病態鄉土”,國民的精神痼疾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阻力,沒有現代國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現代民族國家。在茅盾的“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葉紫的《豐收》、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孫犁的《荷花淀》等小說中,可以看到農民在貪婪的經濟掠奪與兇殘的外敵入侵的絕境中覺醒并奮起反抗,這就有了農村革命。“革命鄉土”是“革命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廢名的《竹林的故事》、沈從文的《邊城》等小說中,可以看到“純樸鄉土”,那里的人們仿佛生活在化外之地,而這又可以看成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另一種理想圖景。在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小說中,可以看到土地革命洗禮過的“翻身鄉土”,現代民族國家在中共建立政權的解放區這片“翻身鄉土”里,形成了自己的雛形。
其六,“戰時中國”,不僅僅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自晚清至20世紀50年代,中國幾乎都處在戰爭狀態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華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北伐戰爭,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似乎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這片歷史悠久而又多災多難的國土。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戰爭造就國家和民族”,“國民身份、國家特性都是在戰爭坩堝之中凝結而成的”,他引證歷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的話說:“沒有哪個國家不是誕生于戰火之中的……沒有哪一個有自我意識的群體能夠不經歷武裝沖突或戰爭威脅,就把自己確立為世界舞臺上的一個新的和獨立的角色。”[12]確如此論,戰爭給現代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卻也喚醒了國民的民族意識,培育了現代民族主義思想。如《風云兒女》(田漢、夏衍編劇,許幸之導演)中的東北知識青年在“九一八”后,不戀兒女私情,以民族國家為念,投身到民族解放戰爭之中。自晚清以來的中國文藝從來就沒有停止對戰爭的敘述,戰爭影響了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文藝,中國文藝的戰爭敘事也影響了民族國家的想象與建構。
三、當代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形象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最迫切需要的前提條件即現代民族國家,最終確立起來了”[13],中國由此告別過去的全部屈辱,進入新的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階段,由此帶來中國文藝根本性的變化。在和平建設民族國家的年代里,想象中國的方式,在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電影、廣播、報紙等藝術手段和傳播媒介之外,還出現了電視劇、電視、網絡等新型的藝術樣式與快捷的傳播媒介。有更多新藝術手段和新傳播媒介的中國當代文藝,其中國形象塑造,雖然延續了中國近現代文藝的諸多新傳統,但也有了時代的新內容新特征。中國當代文藝塑造的中國形象,在不同時期有應答時代召喚的不同形象類型:
其一,“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是中國“十七年文藝”塑造的中國形象。這里的“新中國”不是君主立憲、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是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其形象塑造從四個方面展開:第一,敘述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革命歷史,為新生的民族國家確立歷史的合法性,如小說《紅巖》(羅廣斌,楊益言)、電視劇《小八路》(姜坦、李曉蘭導演)等都是“革命歷史敘事”類的作品。第二,反映建設新中國的現實生活,有敘述現代工業建設的,如電視劇《生活的贊歌》(王扶林導演)講述工業戰線技術革新的故事;有敘述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如電視劇《養豬姑娘》(姜坦導演)講述農村姑娘養豬的故事;有敘述保家衛國的,如電影《上甘嶺》敘述上甘嶺戰役的英勇與慘烈。第三,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新中國”需要“新國民”,“社會主義新人”就是“新國民”的代表,當然也是新中國國家形象的代表,如小說《創業史》中帶頭走社會主義集體道路的梁生寶,電視劇《焦裕祿》中的優秀干部焦裕祿,電視劇《麥賢德》中的海軍英雄麥賢德等。第四,倡揚新的民族國家精神,培養“新的國民性”。對此,周揚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最偉大的啟蒙主義者魯迅曾經痛切地鞭撻了我們民族的所謂‘國民性’,這種‘國民性’正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長期統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種落后精神狀態。他批判地描寫了中國人民性格的這個消極的、陰暗的、悲慘的方面,期望一種新的國民性的誕生。現在中國人民經過了三十年的斗爭,已經開始掙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所加在我們身上的精神枷鎖,發展了中國民族固有的勤勞勇敢及其他一切的優良品性,新的國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們的作品就反映著與推進著新的國民性的成長的過程。”[14]中國“十七年文藝”所要倡揚新的民族國家精神及“新的國民性”,要言之,就是對新中國政體的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就是要有過去不曾有的社會主義精神、集體主義精神、階級斗爭觀念和愛國精神。中國文藝作品中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是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國形象。
其二,“文革中國”,是“文革”及其后兩個歷史時期中國文藝所塑造的中國形象。在“文革”時期的文藝作品中,中國被敘述為“繼續革命的中國”,“階級斗爭的中國”,“革命樣板戲”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已知的“文革”時期的電視劇《考場上的反修斗爭》(楊宗鏡等導演)、《公社黨委書記的女兒》和《神圣的職責》等所表達的也是“反修防修”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文革”意識形態。“文革”后“文革敘事”中的“文革中國”,則是一個動蕩、混亂、暴力、愚昧、貧困、落后的大搞階級斗爭、個人崇拜的中國,講述慘痛“文革記憶”的作品很多,如小說《傷痕》(盧新華)、話劇《于無聲處》(宗福先)、電影《芙蓉鎮》(謝晉)、電視劇《有一個青年》(蔡曉晴導演)、《蹉跎歲月》(蔡曉晴導演)、《福貴》(朱正導演)、《大公社》(楊真導演)、《血色浪漫》(滕文驥導演)、《孽債》(黃蜀芹導演)等。“文革”后“文革敘事”中的“文革中國”形象,因創作者對“文革”的認識不同而千差萬別,但投射的都是歷史浩劫導致的國家認同危機與民族心靈傷痛,總體上是一種負面的中國形象。
其三,“改革開放之中國”,是當今中國的國家客觀形象,也是中國的國家主觀形象和媒介形象,這是國內外公眾對“文革”后中國的基本認識和評價。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藝作品,對“改革開放之中國”的形塑是多方面的,最初是呼喚和想象中國改革開放,關注改革與保守之間的沖突,探索改革遇阻的思想、政治、文化和歷史傳統等多方面的原因。小說《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話劇《血總是熱的》(宗福先)、電影《野山》(顏學恕導演)、電視劇《新星》(李新導演)等都是塑造中國改革開放形象的最有影響的作品。改革開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持續不斷的深化改革,在推動中國社會不斷前行的同時,也為中國電視劇等文藝想象中國提供了新的現實與新的要求,這就有了不同時期不同的改革開放敘事,因而改革開放的中國形象總是在變的。但不論怎么變化,中國文藝塑造的改革開放的中國形象,總體上都是正面的積極的國家形象。
其四,“現代中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形成的國家客觀形象,也是中國文藝及各類傳播媒介著力形塑的國家主觀形象與國家媒介形象。當今中國之“現代”體現在“硬件”與“軟件”兩大方面。首先,在“硬件”方面,中國的國防、工業、能源、交通、通訊、科技、城市等方面,現代化的程度越來越高。譬如,在中國近年來的影視作品中,劇中人物使用手機,已由曾經主要是用于炫富的“大哥大”變成了今天必備的通訊工具,手機已儼然成為參與劇情發展、人物塑造的重要“功能”或“角色”;私家車已成為城市居民乃至部分鄉村居民必備的代步工具,都市現代病“交通擁堵”已成為劇中最常見的景觀。再如,在電視劇《鷹隼大隊》(彭昱凱導演)、《滄海》(趙浚凱導演)、《導彈旅長》(谷錦云導演)、《國家命運》(延藝導演)、《神舟》(寧海強導演)中,可以看到中國空軍、海軍、二炮、“兩彈一星”、航天等已躋身世界先進國家行列。其次,在“軟件”方面,中國科技教育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國民的現代民主精神等,也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即使是在敘述世俗日常生活的中國家庭倫理劇如《金婚》(鄭曉龍導演)、《大女當嫁》(孫皓導演)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中國人很現代的“新國民性”。從“硬件”到“軟件”都在快速現代化的“現代中國”是梁啟超等晚清作家當年超前想象未來40~60年的“新中國”也不能及的。
其五,“世俗中國”,這是“現代中國”的另一副面相。世俗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世俗中國”也因此可以說是“現代中國”。世俗化(Secularization),在西方是指去除宗教神圣性的過程,亦即馬克思·韋伯所說的“祛魅”,宗教由在現實生活中的無處不在逐漸退回到相對獨立的宗教領域里;本文則用以指當代中國的“去政治化”過程。當代中國曾經高度政治化,政治無處不在;“文革”后的中國已由“政治中國”向“經濟中國”轉型,政治意識形態話語及國家權力不再全面滲透到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國民活動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有了相對明晰的分界線,國民的個人需要、物質欲求等世俗欲望都得到肯定,世俗日常生活具有了現實的此岸意義。中國文藝特別是中國電視劇中的家庭倫理劇,如《渴望》(魯曉威導演)、《過把癮》(趙寶剛導演)、《我愛我家》(英達導演)、《裸婚時代》(滕華濤導演)等,都重在敘述國民的日常生活,展示國民的物質追求、情感欲望、婚喪嫁娶和生老病死等世俗生活和情感,從而呈現出積極的正面的世俗化的現代中國形象。
其六,“東方化中國”,是中國文藝特別是中國電影塑造的“東方化的中國”,亦即按照西方人想象中國的方式塑造的中國形象,這是一種“他者化”的中國形象。本文參照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15],將這種“他者化”的中國形象稱之為“東方化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不斷有國產影片沖出國門走向國際,相繼在各類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如《黃土地》(陳凱歌導演)于1985年獲瑞士第38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銀豹獎,《紅高粱》(張藝謀導演)于1988年獲德國第38屆西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霸王別姬》(陳凱歌導演)于1993年獲第46屆法國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小武》(賈樟柯導演)于1998年獲德國第4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青年論壇大獎,獲獎使這些影片產生了較大的國際影響,從而也影響了到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想象。問題是,這些國際獲獎電影塑造的中國形象多是“丑陋的中國”,而電影中呈現的“丑陋”有些是不真實的,如一些偽造的民俗、刻意凸顯的“陰暗面”等,都是按照西方想象中國的方式敘述,是一種認同西方“東方主義”的“自我東方化”。這類迎合西方口味的“家丑外揚”或“自我丑化”的電影敘事,在國內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評。近些年來,一些傳播到海外的中國電視劇,如《步步驚心》(吳錦源等導演)、《甄嬛傳》(鄭曉龍導演)等,也都存在值得討論的類似問題。“東方化中國”是一種負面的中國形象,影響到了國家形象的軟實力。中國的文藝創作如何擺脫西方視野,中國文藝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文藝創作的自由與責任,影視藝術如何塑造正面的中國形象等問題,已成為時下社會各界特別是文藝界的熱點議題。
中國當代文藝作品中的這六類中國形象,是較為重要的幾個國家形象類型,遠不是當代中國形象類型的全部。“中國夢”激勵下的中國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如埃德加·斯諾在其編輯的小說集《活的中國》序文中所說,中國“到處都沸騰著那種健康的騷動,孕育著強有力的、富有意義的萌芽。它將使亞洲東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面貌大為改觀。在中國這個廣大的競技場上,有的是沖突、對比和重新估價。今天,生活的浪濤正在洶涌澎湃。這里的變革所創造的氣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偉大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動。”[16]這雖然是20世紀30年代的友情祝語,也可以用來描述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把這樣的國家客觀形象,表現成可以傳播海內外的中國的國家主觀形象和媒介形象,是中國文藝和新聞傳播的歷史使命。
[1]王一川.中國人想象之中國——20世紀文學中的中國形象[J].東方叢刊.1997(1、2).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2.
[2]李鴻章.復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A].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又名《李鴻章》)[M].上海:東方出版社,2014:46.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M].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
[4]梁啟超.少年中國說[A].梁啟超.飲冰室合集(5)[M].北京:中華書局,1989:9.
[5]陳天華.獅子吼.中國近代珍本小說(8).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37.
[6]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648.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M].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
[8]老舍.五四給了我什么.老舍.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346.
[9]老舍.趙子曰.老舍.老舍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373.
[10]吳賢輝.革命、現代民族國家與中國現代化[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4).
[11]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第1卷)[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28.
[12][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M].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26.
[13]吳賢輝.革命、現代民族國家與中國現代化[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4).
[14]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154.
[15][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16][美]埃德加·斯諾.《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序言.文潔諾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
[責任編輯:王守雪]
2015-09-19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新世紀中國電視劇與民族國家想象”文章,項目編號10BC024。
李興陽(1961—),男,湖北省麻城市人,湖北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新文學;朱華(1972—),男,湖北省荊州市人,湖北師范學院美術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產品與視覺傳達設計及理論研究。
I206.6
A
1671-5330(2015)06-00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