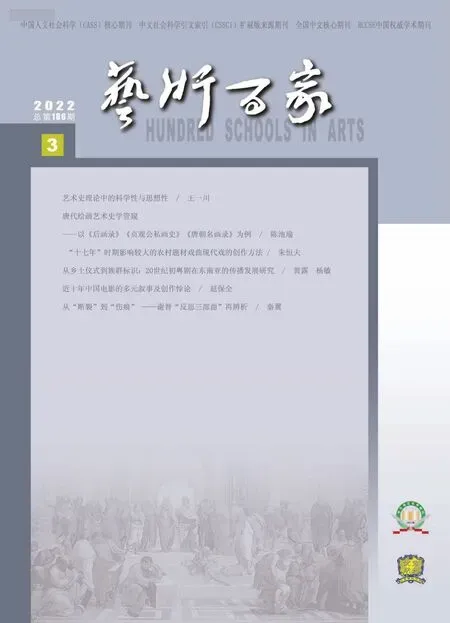南音《偷眼眺》的文學藍本
馬曉霓

摘 要: 在“荔鏡”系列南音散曲中,《寡北》門頭的《偷眼眺》無疑最受時人爭議。品其文辭情采,足以與昆曲《佳期》中的《十二紅》相媲美。南音散曲《偷眼眺》(清唱曲)和梨園戲口述本《陳三·私會》(劇唱曲)的相關曲文藍本均為明清文言小說《荔鏡奇逢集》,這符合中國戲曲大量地改編自傳奇小說的文藝傳統,為“正史小說,難被弦管”的說法也提供了一則相反的力證。
關鍵詞: 戲曲藝術;戲曲作品;《偷眼眺》;《荔鏡記》;《荔鏡奇逢集》;南音散曲
中圖分類號:J80 文獻標識碼:A
在“荔鏡”系列南音散曲中,《偷眼眺》無疑是頗受爭議的一首。在我國大陸學人編撰且流行的各類南音選集或教材中,這支曲子一般不被收錄(近年來略有改觀)。原因十分簡單,就是歷來被某些“冬烘先生”主觀地認為其中涉及“色情”、“鄙下”的成分,難登大雅之堂。事實上,像《偷眼眺》這樣的南音“名”曲之所以能流傳下來,這本身說明它曾經迎合了廣大觀眾的喜好,而這些觀眾同樣是“民間雅樂”的合法接受群體。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主流價值觀念和倫理取向在國人中間的滲透和風行,即使像《金瓶梅》中以招徠讀者而刻意為之的大量露骨而直白的性描寫,也早已不是專家學者討論的禁區,而李安導演的具有三大段展示床上功夫的電影《色戒》,更是堂而皇之地進入世界人民的眼球。與此類小說中露骨且夸張的色情描繪和影視劇中逼真加特寫的性交表演相比,中國傳統戲曲或散曲對相應事項的書寫,因主要采用比喻和象征等藝術手法,就更顯得含蓄蘊藉且詩意盎然了。從其描寫的藝術情境來看,南音散曲《偷眼眺》幾乎可以認為是《南西廂·佳期》的閩南方言版本,只不過“紅娘”、“鶯鶯”、“張生”等角色被替換成“益春”、“五娘”、“陳三”而已,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元曲壓卷之作《西廂記》對中國方言文藝的深刻影響。戲曲史論家劉念茲先生就認為:“《荔枝記》是南戲創作中的一部與《西廂記》媲美的作品。”[1](p.234)在目前流行的昆曲《佳期》中,紅娘所唱的《十二紅》也與益春所唱的《寡北》《偷眼眺》頗具異曲同工之妙。限于篇幅,本文重點討論《偷眼眺》的藍本問題,其他相關問題容另文探討。據筆者目力所及,學界尚無人專門討論過南音《偷眼眺》的藍本問題。筆者曾向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的前輩學者請教這個問題,他們認為:這首曲子估計是后來由民間的南管“秀才”根據“陳三五娘”故事創編而成,與現存明清戲曲諸刊本沒有直接關聯①。通過對現存文獻中蛛絲馬跡的梳理和分析,筆者認為該曲的文學藍本應該是在閩南一帶鮮為人知的文言小說《荔鏡奇逢集》②,以下試作具體討論。菲律賓弦友吳明輝等人抄編的《南音錦曲續集》中收錄了散曲《偷眼眺》,全文如下:[HK22*2]
[JZ]偷眼眺 寡北 五空四イㄨ[HT5”K]
偷眼眺於側耳聽,看三哥恰似君瑞張生,看阿娘又似崔鶯鶯。羅帳里鸞鳳和鳴,錦被中鴛鴦於交頸。笑阿娘露出一枝真於消息,半含半馥動於人心。笑三哥顛顛倒倒如於癡醉,汗濕肌胸透滿不女襟。可憐阮阿娘伊人柳眼戲於嬌鶯,一任枝頭輕偃仰。忽然露滴快把花於心迎,不堪妙處細細呻吟作嬌不女聲。真個滿面春風,一段於芳情誰識得。云雨兩於相稱,正是自家好事自家不女評。那虧得益春遙望於觀情,把卻金針引就紅於絲繩。黃金報我,黃金來報我不足不女稱。且趁此良宵美景,月明花香,只怕狂風弄蝶,亂采柳擺於花傾,亂采柳擺於花傾不女。③ 而在明清文言小說《荔鏡奇逢集》卷三之《秋八月望夜卿私琚》中,對此“佳期”情形就有頗為細致的文學描繪:卿挽琚就枕,琚曰:“丑陋之資,固不敢辭,但新花未慣風雨,吩咐東君細為護持。”卿曰:“嫩花含馥,偶先得之,豈可不知愛惜,而輕于物折耶?”生欲為琚解衣,琚羞愧不勝,且推且就曰:“向者見君,自以為兒戲耳,今宵接戰,退避不得,一身都是膽矣!”卿曰:“兵家勝負,一決便了,勿疑懼也。”再三迫琚,琚于是亦不能為情,乃露出一枝真消息,半含半馥動人心。卿也顛顛倒倒,癡如醉漢,濕脂香透滿襟。琚也柳眼戲鶯嬌,一任枝頭輕偃仰,花心迎露滴,不堪妙處細呻吟,滿面春風,一段芳情誰識得。片時云雨,自家好事自家知。④
琚于是亦不能為情,乃露出一枝真消息,半含半馥動人心。[]笑阿娘露出一枝真於消息,半含半馥動於人心。
卿也顛顛倒倒,癡如醉漢,濕脂香透滿襟。[]笑三哥顛顛倒倒如於癡醉,汗濕肌胸透滿不女襟。
琚也柳眼戲鶯嬌,一任枝頭輕偃仰。[]可憐阮阿娘伊人柳眼戲於嬌鶯,一任枝頭輕偃仰。
花心迎露滴,不堪妙處細呻吟。[]忽然露滴快把花於心迎,不堪妙處細細呻吟作嬌不女聲。
滿面春風,一段芳情誰識得。[]真個滿面春風,一段於芳情誰識得。
片時云雨,自家好事自家知。[]云雨兩於相稱,正是自家好事自家不女評。[BG)F]
從以上曲文對比中不難看出:二者除了個別方言襯詞和敘事方式(文言小說由“作者”用文字直接描繪,而南曲則借“益春”之口唱出。小說為敘事體,南曲為代言體)的不同之外,文字大體一樣,表達了同樣的藝術情境和審美趣味,因襲關系一目了然。我們再來討論文言(非閩南方言)小說《荔鏡奇逢集》(又稱《荔鏡傳》)的成書時間。關于文言小說《荔鏡奇逢集》的成書時間,早在20世紀30年代龔書輝就從該書深受明代瞿佑《剪燈新話》之影響、“數用元明以來戲曲故事”、“演唱西廂戲”、“內容與明人小說類似者甚多”、“體裁與明人小說同”、“作者熟識泉州地理”、“關于荔枝的品種”等七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論,斷定“荔鏡傳寫刊的時代是明永樂以后,比較籠統的說法是明中葉。”⑤20世紀70年代,蔡鐵民也考察了該書的形成年代,認為:“《荔鏡傳》出現大約于明永樂末年以后的年代里。”“《荔鏡傳》應該是明中葉之前一位不得志的文人”撰寫的。但應該注意到,蔡鐵民文中所采用的原始資料遠未超出龔書輝文的范圍,而且十分“簡要”且頗為武斷,如僅僅根據“《荔鏡傳》的結構、體例近乎明弘治前文言筆記小說”和“表現手法上受明前七子復古派文學風尚的影響”就貿然地肯定“《荔鏡傳》應該是明中葉以前出現的”、“是‘反復古派出現之前的作品”[2],這種僅根據文風等近乎縹緲的“證據”而得出的結論顯然讓人無法采信。至20世紀90年代,我國臺灣省知名學者陳益源對《荔鏡傳》曾做進一步的細密比證,認為“《荔鏡傳》成書上限”當以“成化丙午(二十二年,1486)和丁未(二十三年,1487)”為上限,以“萬歷十五年(1587)”為下限,“以弘治末至嘉靖初(中有正德一朝)的可能性居大”[3],與龔書輝所考結果基本吻合,堪稱定論。筆者又按,從現存明嘉靖丙寅(1566)刊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明萬歷辛巳(1581)刊本《新刻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清順治辛卯(1651)刊本《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記大全》、清道光辛卯(1831)刊本《陳伯卿新調繡像荔枝記大全》、清光緒甲申(1884)刊本《陳伯卿新調繡像荔枝記真本》,均無發現與南音《偷眼眺》相應的任何曲文。至少從現存明清文獻來看,南音《偷眼眺》應該是明清以來的南管“秀才”剝離文言小說《荔鏡奇逢集》之《秋八月望夜卿私琚》中的相關文字,并配以南音曲調和閩南方言襯詞創編而成。但是,在1952年根據蔡尤本等人口述整理的梨園戲《陳三》演出本中,卻出現與南音散曲《偷眼眺》相似的曲文⑥,因此,我們尚需討論的問題是:南音散曲《偷眼眺》與口述本《陳三》的關系如何?⑦我們不妨將口述本第十一出《私會》中益春(小旦扮)所唱的相關曲文也摘錄如下:[HK22*2][HT5”K]【雙鸂鶒】(小旦唱)偷眼看側耳聽,笑三哥恰是君瑞張生,笑阿娘恰是崔鶯鶯。羅帳里恰是鸞鳳和諧,錦被中鴛鴦交頸。看阿娘如癡醉,露出一枝真消息,半合斷約動人心。看三哥顛顛倒倒如癡醉,含觸異香側耳聽。可憐阮阿娘譬如雕鶯,含觸異香側耳聽。真個是滿面春風,自宿得云雨。令人傷情,正是又是自家英。那虧得益春蝶夢關情,把作金針引線鳳凰棲止,可消良辰美景。月明花香,只怕你狂蜂浪蝶,漫采而敗花香,匕匕。[4](p.455)
不難看出,《私會》中的這段曲文與南音散曲《偷眼眺》確屬“大同小異”⑧(應考慮到口述本會出現一定的加工、誤傳或誤記)。不過,二者之間仍有一些細節上的明顯差異:在口述本《陳三》中,相關曲文是益春在陳三和五娘首次偷情基本完成之后上場所唱,而南音散曲顯然是益春在陳三和五娘正在私合的過程中“偷眼看”和“側耳聽”的。后者與昆曲《西廂記·佳期》中“紅娘偷看”的時間十分吻合,而前者則存在明顯的“時差”。再從詞句來看,口述本比之散曲來已刪減不少(尤其是后半部分),連貫性和文學性已大大弱化。遣詞和韻腳也有些紊亂,進一步削減了“私會”攝人魂魄的藝術力量!當然,僅從這些比較結果我們顯然還無法斷言二者的前后關系(除非發現更可靠的史料證明)⑨。對于這首曲子而言,“劇曲散唱”和“散曲劇唱”的可能性都存在。不過,從上面的討論我們能夠肯定的是:不論是南音散曲《偷眼眺》,還是梨園戲口述本《陳三》中《私會》的相應曲詞,其文學藍本均為在閩南一帶鮮為人知的明清文言小說《荔鏡奇逢集》,這符合中國戲曲大量地改編自傳奇小說的文藝傳統,對有學者所提出的“正史小說,難被弦管”的觀點也提供了一則相反的力證⑩。需要強調的是,本文雖然初步證明了南音散曲《偷眼眺》的藍本問題,但是綜合考察現存的各類戲曲和小說文獻(尤其考察其刊刻或抄寫的具體時間),卻尚難證明戲曲《荔枝記》(或稱《荔鏡記》)就一定是根據文言小說《荔鏡奇逢集》改編而來的。倘若要坐實這個推斷,還有賴于更為可信的史料發現和更為細密的學術論證。 (責任編輯:陳娟娟)
[CD12]
[HT6F] ① [ZK(#]筆者于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記錄、整理,討論時間為2011年11月18日上午。
② 關于文言小說《荔鏡奇逢集》的流存刊本,現有英國牛津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九年(1814)尚友堂刻本《新刻荔鏡奇逢集》二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二刻泉潮荔鏡奇逢集》二卷(版心題:“荔鏡傳”),索書號:35328。而后來相對易見的刊本(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增注奇逢全集》、民國十三年(1924)上海燮文書莊翻印本《繪圖真正新西廂》等)則與道光刊本大同小異。從嘉慶本“新刻”二字來看,此前應有類似于《荔鏡奇逢集》的遠本,惜已不傳。有學者認為“《荔鏡傳》只限于知識分子或有文化的市民階層,作為好奇獵艷、茶余酒后消遣的東西”,也應合乎事實。蔡鐵民《明傳奇〈荔支記〉演變初探——兼談南戲在福建的遺響》,《廈門大學學報》,1977年第3期。
③ 關于《偷眼眺》完整的工乂譜(抄本),參見吳明輝主編《南音錦曲續集》,菲律賓國風郎君社,1986年印,第146-148頁。本文為論證需要和節省篇幅,僅據該抄印本對其唱詞加以校點,并標示其門頭【寡北】和管門“五空四イㄨ(管)”(相當于西樂之C調),具體曲譜請讀者自檢。鄭國權主編《泉州傳統戲曲叢書》(第一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年版)對此曲詞也作附錄,參閱該書第584-585頁。
④ 此處引文據泉州黃東翰藏本《增注奇逢全集》(光緒刊本)點校。鄭國權編撰《荔鏡奇緣古今談》(中國戲劇出版社,2011年版)時“輯錄明代小說《荔鏡傳》等及其部分研究論著”,對文言小說“《荔鏡傳》”據“原本”照實錄入,為“存其真”而未作新式標點。參閱該書第303頁。
⑤ 龔書輝《陳三五娘故事的演化》,載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泉州地方戲曲》,1986年第1期,第55-83、117頁。據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者的按語,此文“一九三六年六月發表于廈門大學,是最早較有系統地研究陳三五娘故事沿革的一篇專論”。戲曲史論家吳捷秋先生亦云:“對《荔鏡傳》與《荔枝記》及南曲、歌本作綜合的考證,并撰寫專題論文,首先是龔書煇先生發表于1936年為最早,在當時尚未發現明·嘉靖丙寅年重刊的《荔鏡記戲文》和潮州東月氏編集的《鄉談荔枝記》的情況,當時他所搜羅的資料,現在有的已看不到”。(吳捷秋《梨園戲藝術史論》,中國戲劇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頁。)
⑥ 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華東會演得獎本及其后《陳三五娘》各種演出本再無出現這段“南曲”。原因不言自明:新中國成立之后,紅色政治使戲曲追求“凈化”成為其必然選擇,類似《偷眼眺》之類的南音“艷曲”自然不能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了。
⑦ 關于口述本定型的具體年代,估計至遲在清代中后期。筆者主要依據老藝人蔡尤本等人的生平閱歷和現存《荔枝記》諸版本的刊印時間來推算。
⑧ 鄭國權先生對《偷眼眺》就有這樣的說明:“此曲源自《陳三五娘》,益春唱,與蔡尤本口述本的《私會》曲詞大同小異。蔡本由口述記錄,文字稍有出入。”(鄭國權編注《泉腔弦管曲詞選》,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頁。)
⑨ 梨園戲和相應的南音清唱版本的前后關系,學術界長期眾說紛紜,難有定見,乃至于王仁杰先生曾戲稱:“先有南音還是先有梨園戲”實在是一個“先有母雞還是先有雞蛋”的問題。應根據實際情況客觀分析和科學論證,而不應以偏概全,人云亦云。從大量南音散曲“剝離”自梨園戲古老劇目的事實來看,“南音來自梨園戲”的結論則更靠譜,我們不能為了某些既得利益而無視歷史事實地去“跟風”、去“睜著眼睛說瞎話”。(筆者于泉州王仁杰先生家里記錄、整理。時間:2010年5月12日上午)
⑩ 如鄭國權先生認為:“《荔鏡傳》是文言小說,不能‘被之弦管,只有《荔鏡記》系列戲文才進入弦管”,“《荔鏡傳》是文言小說,并無曲詞,應是《荔鏡記》戲文,才有十多個唱段成為弦管名曲。”(鄭國權《客觀評價〈泉南指譜重編〉》,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兩岸論弦管》,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273頁。)而從本文的考察結果來看,這一觀點顯然是需要商榷的。
參考文獻:
[1][ZK(#]劉念茲.南戲新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234.
[2]蔡鐵民.明傳奇《荔支記》演變初探——兼談南戲在福建的遺響[J].廈門大學學報,1977,(03).
[3]陳益源.《荔鏡傳》考[J].文學遺產,1993,(06).
[4]鄭國權.泉州傳統戲曲叢書(第一卷)[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