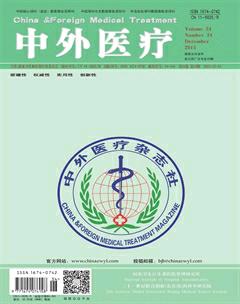從翻譯倫理解讀馬建忠的善譯觀
王志霞
【摘要】馬建忠在1894年《擬設翻譯書院議》一文中提出明確善譯觀點,但在當時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21世紀隨著翻譯理論的繁榮,一些學者和譯者開始重新認識善譯理論的意義,而不只是停止在語言學層面的語言轉換。善譯理論雖言簡意賅,對翻譯的闡釋卻十分全面,包括翻譯理論范疇和對翻譯實踐的指導。本文試從翻譯倫理角度剖析馬建忠的善譯,包括時代背景下馬建忠作為政治人,提出翻譯的必要性以及作為譯者,馬建忠提出對善譯的道德規約,通過這些解讀,嘗試挖掘善譯觀深層的理論價值。
【關鍵詞】翻譯倫理;馬建忠;善譯
一、引言
馬建忠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愛國之士,他認識到中國的內憂外患,強烈的民族意識使他深感興洋務,究西學,培養翻譯人才的重要性。由此他提出建翻譯書院,培養專門的翻譯人才,并詳細闡述了自己的翻譯思想: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考,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及其義理粗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是則為善譯也已。這一段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善譯理論的來源。很多學者在解讀善譯觀時大抵視之為翻譯過程抑或是翻譯產品,這都說得通。還有學者試從中西語言對比研究的視角分析善譯理論的價值所在。馬建忠在闡釋善譯觀點時涉及到了所有翻譯主體,有的學者則認為其初步構建了“原作(者)→譯者→讀者”這一完整的翻譯本體論體。不過,細細重讀馬建忠對翻譯的闡釋,使我們感觸更深的譯事之難不是如何翻譯,而是譯者的翻譯道德問題。從馬建忠文中所用字眼不難看出,“冥心鉤考”“深嗜篤好”“反復經營”“心悟神解”“曾無毫發出入”更多的是強調一種譯者的翻譯態度,體現的是翻譯使命,這恰是譯者的翻譯道德所在。
二、善譯的倫理體現
著有《馬氏文通》的馬建忠深諳文章之學,講究“修辭立誠”,主張翻譯要像做文章一樣盡心盡力,不允許有絲毫不講究文采。馬氏“善譯”標準,立足語言文辭差異,以求“善為旨歸的思維方式,具有明顯的中國哲學、倫理學特點。“善”,不同于“好”這個字本身就帶有倫理色彩,所以此處理解善的標準不應僅局限于譯作,還應指譯者的翻譯道德。馬建忠認為,譯者的使命在于通過翻譯西學來振興中國,此時的翻譯受時代的影響,帶有明確的目的性。在這一使命的驅使下,譯者在翻譯時則需要達旨,馬氏在闡述善譯的時候,并未像嚴復一樣提出信達雅可操作性的標準,使翻譯實踐有據可依。他只是強調了譯者在翻譯時應該怎么做,但并未闡明如何去做,所以說如果僅用翻譯過程來理解善譯就以偏概全,掩蓋了馬氏的良苦用心。國家需要翻譯人才,馬氏也提出要建翻譯書院培養翻譯人才,但翻譯人才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識與技能,而是良好的翻譯道德,這包括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翻譯使命和修辭立誠的翻譯態度。
作為一位愛國志士,馬氏有著強烈的愛國熱情。這在他的翻譯標準中體現出來的就是一種強烈的政治使命。可以說馬氏的善譯標準是帶有一定功利性和政治色彩的。他特別強調翻譯要達旨,這也體現了翻譯的目的所在。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馬氏以其舉足輕重的政治地位和學貫中西的學術背景為翻譯做了最初步的道德規約。嚴格地講,善譯并不能算作翻譯理論,只能是馬氏作為政治人在提議建翻譯書院時見諸于文的翻譯散論。馬氏本身是一位翻譯家,而非研究翻譯理論的學者,所以善譯的標準更是他的經驗總結,是他的翻譯態度的體現。
三、善譯的倫理意義
無論從微觀的語言層面還是從多角度剖析,馬建忠的善譯對于中國傳統譯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善譯理論是對傳統譯論的豐富和發展,精通西學的馬建忠把語言的對比研究融入到翻譯中,還涉及了西方語言學語義學,語音學,語體學,修辭學等各個領域的知識。此外,馬建忠從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文化戰略高度來看待翻譯,而不是僅僅把翻譯看成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簡單的文字轉換過程。可以說他的翻譯理論思想是對翻譯一種不夠系統但夠全面的凝練總結。
很多學者已經嘗試在新的歷史時期對善譯理論進行新的解讀,重新認識其價值所在。本文試圖挖掘善譯理論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倫理意義。馬建忠曾明確提出:“翻譯自在中國發軔之日起,就具有出自文化戰略的考量……”這里馬氏闡明了譯者的文化使命感,這對現在譯界的發展趨向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此外,馬建忠還指出了當時翻譯的癥結所在:今之譯者,大抵于外國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微辭奧旨……而漢文則粗陋鄙俚,未窺門徑。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華語者為之口述,則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在當時,譯者參差不齊,有的只通漢語,有的只懂外文,就造成錯譯,譯文不忍卒讀;還有通過口述翻譯,難免武斷胡譯亂譯。馬氏針對這種現象提出善譯,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善更多的是對譯者提出的要求,可以理解為譯者應具備善這一翻譯道德。這對于譯者和譯作都是一種重要的考量標準。
四、從翻譯倫理看善譯的邊緣化
善譯的提出在當時并未受到學者及當朝者的重視,究其原因,必然有其歷史局限性,善譯所倡導的翻譯倫理不適合當時的歷史狀況,當時雖興西學,但譯界為嘩眾取寵,淺嘗輒止,追求翻譯數量,如果按照馬氏提出的標準,那些譯者與善譯都相差甚遠。當時譯界剛剛興起,缺少道德規約,懂點洋文就敢譯,嚴重缺乏責任感和嚴謹的翻譯態度。因此,馬建忠提出善譯理論在當時有種世人皆醉唯我獨醒,世人皆濁唯我獨清的味道,難免遭人排斥。
五、總結
張谷若曾提出:要地道的做人,地道的翻譯,這也同樣說明了譯者的翻譯道德和翻譯倫理對于翻譯活動的影響。翻譯倫理,作為翻譯技能以外的內容,很容易被人忽略,然而,譯者在翻譯之初首先要對自己的翻譯道德給予規約,先做一個道德人,再做一個譯者。本文嘗試從馬建忠的善譯理論中窺見其對翻譯道德的重視和強調,不管譯者兼有何種身份,神圣的翻譯使命感和嚴謹的翻譯態度都應是譯者翻譯道德最好的體現。
參考文獻:
[1]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2]辛紅娟,馬孝幸.馬建忠翻譯思想之文化詮釋[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1:9.
[3]王洪濤.中國傳統譯論基本理念的嬗變與衍化一一馬建惠‘善譯”理論之現代闡釋[J].外語學刊,2005:1.
[4]王曉農.馬建忠翻譯觀的歷史命運:基于系統觀的解讀[J].東岳論叢,2007:11.
[5]張陽,龔昭.論馬建忠善譯之等值觀[J].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