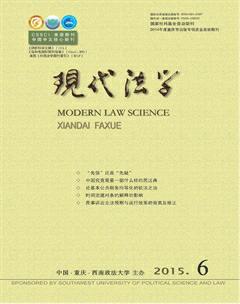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類型界分與功能定位
黃錫生 謝玲
摘要:環(huán)境公益訴訟并非一種獨立的訴訟類型。環(huán)境公益訴訟是原告以“凡市民”中一分子的身份訴諸司法之訴訟。環(huán)境公益訴訟并非通過與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者的結盟為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補強,而是通過“監(jiān)管監(jiān)管者”來實現(xiàn)環(huán)境公益目標之維護。環(huán)境公益與私人利益的內在關聯(lián)是環(huán)境公益轉化為私主體訴諸司法之權利的最終根據,而“利益歸屬主體”與“利益代表主體”的疏離為環(huán)境公益訴訟提供了訴訟法上的依據。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性質、功能定位及訴權基礎決定了環(huán)境公益訴訟仍具有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基本屬性。
關鍵詞:環(huán)境公益訴訟;訴訟類型;功能定位;訴權
中圖分類號:DF468
文獻標志碼:A
引言:環(huán)境公益訴訟傳統(tǒng)“二分法”否定觀點的提出
針對學界一般將環(huán)境公益訴訟劃分為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與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觀點,呂忠梅教授提出:環(huán)境公益訴訟既不是民事訴訟,也不是行政訴訟,而是一種代表國家政治意愿的“特別訴訟”,從而否定了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傳統(tǒng)二分法。其主要理由有:第一,依羅馬法關于公益訴訟與私益訴訟的劃分標準,認為現(xiàn)階段我國的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都屬于私益訴訟的范疇,與環(huán)境公益不協(xié)調;第二,民事訴訟中的原被告雙方地位平等,而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的原被告雙方地位卻是不平等的;第三,行政訴訟的基本理念是私權對公權的制衡,而在以國家行政機關為被告的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原告因代表了公共利益而成為公權力主體的代表,因此這時的訴訟是兩個公權力之間的博弈。勿庸置疑,否定環(huán)境公益訴訟有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與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之分的觀點敏銳地捕捉到了環(huán)境公益訴訟與傳統(tǒng)訴訟的差異,在環(huán)境法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并將學者們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性質及類型的思考引向深入。不少學者贊同環(huán)境公益訴訟類型不能二分的觀點,甚至有研究者主張,因環(huán)境公益訴訟具有獨特的訴訟目的、價值和機能,與傳統(tǒng)的訴訟制度有著本質的不同,可考慮將其歸屬為獨立的第四種訴訟制度。但也有不少研究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環(huán)境公益訴訟并非一種獨立的訴訟類型,它仍然應分為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與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
誠然,環(huán)境公益訴訟從訴訟理念、訴權基礎到具體制度設計均對傳統(tǒng)訴訟有顯著突破,但環(huán)境公益訴訟是否特殊到為傳統(tǒng)的訴訟類型所不容甚至應該成為獨立的“第四種訴訟制度”呢?針對呂忠梅教授否定環(huán)境公益訴訟“二分法”的第一個理由,即我國目前所進行的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均屬于私益訴訟的范圍而并非出于維護公益之目的的觀點,學界已有學者進行了有力反駁。有學者指出:傳統(tǒng)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確是私益訴訟,但隨著現(xiàn)代社會訴訟理念的不斷更新,公益也可以通過訴訟方式獲得救濟,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正逐漸接納并為公益服務,而不再固守私益訴訟的性質。“環(huán)境公益訴訟是環(huán)境公益嵌人訴訟的結果,是環(huán)境公益與訴訟這種權益救濟方式的融合,是訴訟法律理念適應現(xiàn)代社會需求的重要發(fā)展。”筆者亦認為,旨在對私益進行救濟的傳統(tǒng)訴訟向旨在預防和救濟“對環(huán)境本身之損害”、維護和增進環(huán)境公益的現(xiàn)代訴訟轉變,是訴訟理念適應社會生活之變化的結果,但這一訴訟目標的改變并不必然導致需要在傳統(tǒng)的訴訟框架之外構建一個全新的訴訟類型,而是需要拓展傳統(tǒng)司法救濟的范圍,即從僅僅對私益進行救濟轉變?yōu)樗揭婧凸婢葷⒅亍J聦嵣希S著公私法的交融,私法領域諸多傳統(tǒng)法律范疇和法律原則因公共利益的考慮而被不斷修正甚至逐漸失效,作為國家公權力象征的司法已不再局限于救濟私益。
然而,環(huán)境公益訴訟能否二分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以維護私益為主要目標的傳統(tǒng)訴訟能否容納公益保護的內容,而是在于以維護公益為目的的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確在制度設計上突破了傳統(tǒng)訴訟理論中的“當事人適格”理論和“訴之利益”理論,那么,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原被告之間的關系是否仍然符合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訴訟主體間關系的基本屬性呢?學界一般認為,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潛在原告包括公民個人、環(huán)保團體、檢察機關、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部門,其中公民個人與環(huán)保團體為一類起訴主體,檢察機關與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部門為另一類起訴主體;被告則包括企業(yè)等私主體和行政主體。因此,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訴訟形態(tài)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公民和環(huán)保團體對企業(yè)等私主體的訴訟、公民和環(huán)保團體對行政主體的訴訟、檢察機關或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部門對企業(yè)等私主體的訴訟、檢察機關或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部門對行政主體的訴訟。呂忠梅教授認為,依“私人檢察長”理論,作為原告的公民個人或法人團體因獲得了國家授權而成為公權力的代表,不再是私主體,因此由其提起的對企業(yè)等私主體的公益訴訟不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訴訟,因而違背了民事訴訟的本質屬性。同理,在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因獲得特別授權代表環(huán)境公益的原告,對行政主體提起的訴訟也不再是私權與公權之間的對抗,而是兩個公權之間的博弈,從而也違背了行政訴訟“民告官”的本質屬性。從表面上看,這一分析頗有見地,尤其是當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部門為了環(huán)境公益訴企業(yè)的排污行為時,其尋求救濟的訴訟還是民事訴訟嗎?或者當檢察機關為了環(huán)境公益而對行政機關的行政違法行為提起訴訟時,其訴訟還是行政訴訟嗎?似乎前者與民事訴訟的本質屬性即當事人地位平等相矛盾,后者則與行政訴訟原告恒定為行政管理相對人的要求不符。正是這一困惑導致不少學者贊成對傳統(tǒng)環(huán)境公益訴訟“二分法”的否定,仍然堅持環(huán)境公益訴訟類型二分的學者,雖然也看到了這一論述中的某些破綻,卻未能從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本源、功能及訴權基礎等視角深入地加以分析,因而未能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性質和功能作出準確的界定及令人信服的論證。
一、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制度定位:對“二分法”否定觀點之否定分析
否認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二分法”的觀點的確很有迷惑性,筆者也曾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到底是否為一種獨立的訴訟類型而苦苦思索。隨著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基本理論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入,筆者發(fā)現(xiàn),雖然環(huán)境公益訴訟無論在訴訟理念還是制度設計上與傳統(tǒng)訴訟均存在較大差異,但環(huán)境公益訴訟仍然可以劃分為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與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不管在制度設計上賦予誰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環(huán)境公益訴訟都不會與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本質屬性相沖突。endprint
否認環(huán)境公益訴訟傳統(tǒng)“二分法”的學者認為:“依據羅馬法上的公益訴訟理論來觀察所謂的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會出現(xiàn)一種完全違背訴訟法學原理的現(xiàn)象——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因私主體獲得了國家特別授權具有公權性質而成為‘不平等的訴訟;而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也因私主體獲得了國家特別授權而與國家行政機關具有相同性質而成為‘平等的訴訟。”這一論述集中反映出學界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性質、類型和功能等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仍存在諸多誤區(qū),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
第一,訴訟類型的劃分依不同的標準可以有不同的分類。依訴訟救濟目的和利益歸屬的不同,訴訟可以分為公益訴訟和私益訴訟;依訴訟主體間關系的性質和責任性質的不同,訴訟又分為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和刑事訴訟。環(huán)境公益訴訟依第一類分類標準屬于公益訴訟的范圍,但這并不影響其依第二類分類標準再繼續(xù)被劃分為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因環(huán)境公益訴訟以維護公益為目的而與私益訴訟相區(qū)別就認定其改變了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之本質的觀點,有混淆兩種不同訴訟類型劃分標準之嫌。
第二,將獲得特別授權能代表公共利益的私主體等同于公權力代表的觀點,事實上是將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都看成了國家公權力的一部分,即將公益訴訟納入與環(huán)境公益的行政救濟結盟的內部關系來界定,而沒有認識到環(huán)境公益訴訟是獨立于環(huán)境公益行政救濟之外的另一種救濟機制。另外,該觀點以公權力主體是環(huán)境公益的唯一代表為預設,因為只有在公權力主體是環(huán)境公益的唯一代表的前提下,其他主體要成為環(huán)境公益的代表才必須先成為公權力主體。環(huán)境公益訴訟“二分法”否定論者的一個認識誤區(qū)在于,一般主體只有通過代表公權力才能代表環(huán)境公益。
第三,環(huán)境公益訴訟“二分法”否定觀點很容易將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基本功能的定位引入歧途。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目標在于有效預防和救濟“對環(huán)境本身之損害”,構建該制度的基本前提是環(huán)境公益行政救濟在應對環(huán)境損害問題上的失效,這點在學界已經達成共識。然而,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具體是通過何種途徑來彌補環(huán)境公益行政救濟之不足從而達到救濟“對環(huán)境本身之損害”這一目標的呢?這一問題直接關系到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性質及功能的界定,學界卻未能對其進行更細致的思考。在主張應優(yōu)先賦予環(huán)保行政部門環(huán)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學者們看來,環(huán)境公益訴訟是通過對在行政系統(tǒng)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環(huán)境行政權的補強而起到維護環(huán)境公益之目標的,這與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基本功能是通過對公權力的監(jiān)督而實現(xiàn)環(huán)境公益之維護的認識相背離。將獲得特別授權以公共利益代表身份提起訴訟的普通主體都看成國家公權力一部分的觀點,可能導致我們將環(huán)境公益訴訟彌補環(huán)境行政救濟之不足從而達到救濟環(huán)境公益的具體途徑界定為對環(huán)境行政權的補強而非對國家公權力的監(jiān)督。
綜上,否定環(huán)境公益訴訟“二分法”的觀點模糊了我們關于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性質及基本功能的認識,如果我們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實現(xiàn)環(huán)境公益維護的具體路徑做更深入的分析,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本質與基本功能做更準確的把握,則關于環(huán)境公益訴訟能否分為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的迷霧將被澄清。
二、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基于“凡市民”概念的延伸分析
從公益訴訟的起源來看,與私益訴訟相對的公益訴訟最早起源于羅馬法。在羅馬法中,私益訴訟是指為了保護個人所有的權利的訴訟,僅特定人才可以提起;公益訴訟是指為了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guī)定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雖然時過境遷,今天我們所論及的公益訴訟與羅馬法時期的公訴在范圍和內涵方面均有很大差異,但公益訴訟是“凡市民”以“主持社會正義、實現(xiàn)社會公平、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而提起的訴訟之本質卻并未改變。在羅馬法中,起訴主體是以“凡市民”中一分子的身份來提起公益訴訟的,即提起公益訴訟的普通市民以自己的名義直接代表公共利益而訴諸司法,其前提是任何市民均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在否定環(huán)境公益訴訟“二分法”的學者們及當前的主流觀點看來,獲得特別授權并代表公共利益的原告,在提起環(huán)境公益訴訟時代表的是公權力。該觀點要在邏輯上自洽則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國家為環(huán)境公益的所有權主體;二是國家公權力機關是環(huán)境公益的唯一適格代表。事實上,我國現(xiàn)行有關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部分立法和司法實踐正是在肯定這兩個前提的基礎上進行的,例如,我國《海洋環(huán)境保護法》第90條規(guī)定:“對破壞海洋生態(tài)、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qū),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依照本法規(guī)定行使海洋環(huán)境監(jiān)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這一規(guī)定將“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作為“提出損害賠償要求”的條件,并將“行使海洋環(huán)境監(jiān)督管理權的部門”作為國家的代表規(guī)定為“提出損害賠償要求”的唯一適格主體,正是體現(xiàn)出將環(huán)境公共利益理解為國家財產,并認為公權力主體是環(huán)境公共利益唯一代表主體的基本思路。
然而,這兩個前提均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國家并非環(huán)境公共利益的所有權主體。在理論上,法律可以規(guī)定森林資源歸國家所有,但無法規(guī)定森林資源所具有的生態(tài)價值歸國家所有,因為事實上一定區(qū)域內甚至整個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共同享受著森林資源的生態(tài)功能。如2002年的《水法》規(guī)定水資源歸國家所有,這一法律規(guī)定僅僅是“從經濟功能的角度界定了水資源所有權,但我們并不能從這條法律規(guī)則中推出水的環(huán)境功能也專屬國家所有,因為河流流域的所有居民共同享受著河流容納污染物的環(huán)境功能”。環(huán)境公共利益不能成為國家財產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財產可以劃歸具體的個體排他性使用,而環(huán)境公共利益卻不能劃歸具體的個體排他性使用”。其次,國家公權力機關并非環(huán)境公益的唯一適格代表。環(huán)境公共利益并非歸國家所有的國家財產,環(huán)境公共利益的最終歸屬主體為社會公眾,社會公眾作為一個抽象概念的存在是由千萬個普通主體將其具體化的。因此,從應然意義上說,任何主體均可以作為環(huán)境公共利益的代表來提起訴訟,能夠代表環(huán)境公益提起訴訟的主體應該是多元的。也正因為如此,任何主體在提起環(huán)境公益訴訟時均不需要通過代表國家這一中間環(huán)節(jié)來代表環(huán)境公益,而是以自己的名義直接代表環(huán)境公益。endprint
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是因其為環(huán)境公益的利益歸屬主體中的一分子而提起訴訟的,這與羅馬法將公益訴訟界定為以“凡市民”中一分子的身份來訴諸司法的本質是一脈相承的。因此,一般主體并不需要升格為公權力的擁有者才能提起環(huán)境公益訴訟,相反,包括公權力機關在內的諸多主體在提起公益訴訟時均是以“凡市民”中一分子的身份即私主體的身份進行的。如此,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不管在制度設計上賦予誰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均不會與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本質屬性相沖突。由公民、社會團體提起的以私主體為被告的訴訟不違背民事訴訟的本質,由其提起的以公權力主體為被告的訴訟同樣不違背行政訴訟之本質。即便是檢察機關或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部門對私主體提起的公益訴訟,也并未違背當事人地位平等的民事訴訟之本質屬性。因為公權力主體作為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時,是以降格為“凡市民”中一分子的身份而提起訴訟的,其起訴地位與一般主體并無本質區(qū)別,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只能發(fā)揮其職業(yè)優(yōu)勢而不能行使其職權優(yōu)勢。從表面來看,在檢察機關或行政監(jiān)管部門為了環(huán)境公益狀告另一行政機關行政行為違法的訴訟中,原告與行政訴訟“民告官”的屬性不符。但是,所有的公權力主體都具有雙重身份:一般的私主體身份和公權力主體身份,原告在提起公益訴訟時正是以一般私主體的身份出現(xiàn)的,因而未曾突破行政訴訟“民告官”的本質。
有疑問的是,在美國環(huán)境法“私人檢察長”理論中,是否通過理論假設和特別授權而將普通個體上升為“檢察長”這樣的公權力主體呢?仔細考察美國的“私人檢察長”理論,可以發(fā)現(xiàn)“私人檢察長”是對“聯(lián)邦檢察總長”的類比化使用,“聯(lián)邦檢察總長”履行職責的核心功能是以“公力救濟”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政府利益。該理論有兩個前提:假定每個人都是執(zhí)法者;假定“私力救濟”能夠起到與“公力救濟”相同的法律效果。學界往往只注意到該理論的第一個假設即“每個人都是執(zhí)法者”,就匆忙得出美國公民訴訟中的原告是公權力的行使者之結論。事實上,該理論強調的重點是第二個假設,即通過被授權主體的訴訟救濟在保護環(huán)境公益的功能上能起到與“公力救濟”相同的效果。“私人檢察長”強調的“實際上并不是一種職位”,因為被授權的“私人檢察長”并沒有獲得像“檢察總長”那樣廣泛的法定權力。換言之,“私人檢察長”理論并非認為每個被授權的公民真的是檢察總長,而是強調被授權的公民通過提起保護環(huán)境公益之訴訟事實上能夠起到防范和阻卻違法行為之效果,而這一效果與檢察總長履行公職所發(fā)揮的功能相同。
從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起源來考察,訴訟主體間的關系逐漸清晰起來,環(huán)境公益訴訟是以“凡市民”中一分子的身份訴諸司法之訴訟,因而仍然遵循著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本質。
三、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制度功能:通過“監(jiān)管監(jiān)管者”實現(xiàn)環(huán)境公益救濟
從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制度生成背景來看,構建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直接動因源于我國現(xiàn)行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效果的差強人意,因而環(huán)境公益訴訟是對現(xiàn)行環(huán)境行政執(zhí)法不足的一種彌補。但是,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具體是通過何種途徑來彌補現(xiàn)行環(huán)境行政執(zhí)法機制的不足從而達致環(huán)境公益目標之維護的呢?
在否定環(huán)境公益訴訟傳統(tǒng)“二分法”的學者們看來,代表環(huán)境公益提起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是公權力主體的代表;主張應優(yōu)先賦予環(huán)保行政部門環(huán)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學者們亦認為,環(huán)境公益訴訟可以通過對在行政系統(tǒng)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環(huán)境行政權的補強而實現(xiàn)環(huán)境公益的維護。雖然這兩種觀點論及的是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不同方面,但二者的共同之處是事實上將公益訴訟納入了與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者結盟的內部關系來看待。如此,環(huán)境公益訴訟實現(xiàn)公益維護目標的具體路徑是通過對環(huán)境行政權的補強來彌補環(huán)境行政救濟之不足的。這一路徑判別的確契合了當前環(huán)境行政執(zhí)法的部分現(xiàn)實,觸及了環(huán)境行政執(zhí)法的某種無奈,因而得到了理論界和事務部門一定程度的認可。
然而,環(huán)境公益訴訟并非通過對環(huán)境行政權的補強、尋求與行政監(jiān)管者的結盟而實現(xiàn)環(huán)境公益的維護,而是在環(huán)境公益的行政救濟之外,通過對公權力運行的監(jiān)督促使行政職權的積極履行,從而維護環(huán)境公益。在傳統(tǒng)的法學理論中,的確對私益和公益的救濟安排了不同的路徑,私益的受害人可以通過訴訟方式得到救濟,而對公益的救濟,除刑事訴訟外,一般將國家和政府作為公益代表人,通過賦予其公權力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實現(xiàn)對公益的維護,此為“傳統(tǒng)的私益司法救濟與公益行政救濟之二元保護機制”。不可否認,長期以來的實踐證明,這種二元保護機制對私益的救濟和公益的維護均發(fā)揮了基礎性功能。然而,隨著現(xiàn)代社會的復雜化和單一行為社會效應的廣泛化,公益日趨脆弱且公益受損日趨普遍,公益行政救濟模式的有限性日益暴露出來。以維護公益為己任的政府理性有限、地位中立有限、執(zhí)法實力有限等因素制約著公益行政救濟在環(huán)境保護領域的功能發(fā)揮。具體到我國環(huán)境保護領域,不僅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主體受監(jiān)管體制、權力配置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執(zhí)法能力和執(zhí)法動力均顯不足,怠于履行行政職權的情形普遍存在;而且,地方政府等行政主體充當企業(yè)環(huán)境違法行為“保護傘”的情形也并不鮮見,甚至政府決策失誤等不當行政行為本身亦成為環(huán)境污染與破壞之源。
正是環(huán)境公益行政救濟的種種“失靈”催生了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構是以承認環(huán)境公益行政救濟存在固有缺陷為前提的。再來看美國的“私人檢察長”理論,由于美國政府也“永遠不可能擁有足夠的執(zhí)法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監(jiān)控每一個污染源”,因此該理論也以承認“公力救濟”環(huán)境公益的效果有限為理論假設之前提。在此前提下,借助一個類比化概念(私人檢察長)為普通個體提起公益訴訟提供理論依據的“私人檢察長”理論,其目的當然不是通過授權尋求更多的“公力救濟”,而是尋求在“公力救濟”之外通過私人啟動司法救濟程序來彌補“公力救濟”對環(huán)境公益維護之不足。
因此,環(huán)境公益訴訟欲求的目標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環(huán)境公益行政救濟的固有缺陷,而不是通過尋求與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者的結盟為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補強。環(huán)境公益訴訟是在現(xiàn)行環(huán)境公益行政救濟之外設置的另外一種補充救濟機制,即通過廣泛的一般主體啟動司法程序以實現(xiàn)對環(huán)境公益的維護。將環(huán)境公益訴訟界定為行政救濟之外的另一種救濟方式和將環(huán)境公益訴訟界定為與行政救濟結盟的內部機制,均能實現(xiàn)對現(xiàn)行環(huán)境行政執(zhí)法不足的彌補,并達致維護公益之目的,但是對實現(xiàn)目標具體路徑判別的不同會導致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基本屬性和功能界定的迥異。若將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定位為與行政主體的聯(lián)盟,則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規(guī)制對象主要限定為私主體(包括企業(yè)和個人)的環(huán)境違法行為,即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主要規(guī)制對象與環(huán)境行政監(jiān)管的對象是同一的,這時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實質是私權對私權的監(jiān)督或者公權對私權的監(jiān)管。套用呂忠梅教授的一種說法,這時環(huán)境公益訴訟儼然成為另一種“監(jiān)管者監(jiān)管”制度,如此,構建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目標——克服環(huán)境公益行政救濟的固有缺陷,則無法實現(xiàn)。endprint
若將環(huán)境公益訴訟定位為獨立于環(huán)境公益行政救濟之外的補充救濟機制,則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基本功能是實現(xiàn)對公權力運行的監(jiān)督,其性質為私權對公權的制衡。梁慧星教授指出,依傳統(tǒng)做法,對公權的制衡適用“公權制衡公權”的法理,即“某個政府機關被授權行使某項行政權(如行政審批、行政許可),就相應設置或授權另一個政府機關來予以制衡、控制。而對于被授權的另一個政府機關的行為,又需要再設置、再授權第三個政府機關予以制衡、控制。”但這種以公權制衡公權的實踐并未取得良好效果,因此必須走出以公權制衡公權的傳統(tǒng)做法,建立私權制衡公權的制度。公益訴訟的本質屬性即為私權對公權的制衡。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直接針對的是行政機關的違法行政行為,在性質上是私權對公權的監(jiān)督。即使在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窮盡行政手段的行政前置程序同樣意味著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也是私權對公權的一種監(jiān)督,原告起訴前須告知負有職責的行政主體,這一程序設置的目的之一是敦促有責的公權力機關全面履行職責,因此,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也是對行政執(zhí)法的一種監(jiān)督。
綜上,環(huán)境公益訴訟通過對公權力主體的監(jiān)督而不是通過與公權力主體結盟的方式來維護環(huán)境公益,其性質應為“監(jiān)管監(jiān)管者”制度。這一本質和基本功能決定了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主體間關系的性質仍然符合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基本屬性。
環(huán)境公益訴訟是以私主體的身份直接代表環(huán)境公益而訴諸司法之訴訟,該論斷回答了代表環(huán)境公益的原告以何種身份提起公益訴訟的問題,卻無法闡明與環(huán)境違法行為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主體緣何可以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訴訟的問題。因此,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并非利益歸屬主體的私主體代表環(huán)境公益提起訴訟的正當性何在?這種利益歸屬主體與利益代表主體相分離的情形在訴訟法中是否已有相應的制度安排?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考察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訴權基礎與訴訟法依據。
四、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訴權分析:“利益歸屬主體”與“利益代表主體”的疏離
在大陸法系的訴訟理論中,起訴主體提起訴訟的正當性被表述為訴權。根據《元照英美法辭典》的定義,訴權是“為實現(xiàn)自己的權利或尋求法律救濟而在法院就特定案件提起訴訟的權利”。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的原告只有獲得訴權,才具有提起訴訟的正當性,才能啟動與延續(xù)訴訟。傳統(tǒng)訴訟中“訴之利益”理論和“當事人適格”理論,將訴權的賦予限制在與系爭糾紛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主體范圍內,而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顯著不同就在于對“訴之利益”和“當事人適格”的范圍進行了擴展。那么,與環(huán)境違法行為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主體獲得公益訴訟訴權的理論根據到底是什么?
公共信托理論、私人檢察長理論和環(huán)境權理論普遍被認為是確立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理論基礎。不可否認,這些理論為各國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構發(fā)揮了理論支撐的作用。但也有研究者認為,無論是公共信托理論、私人檢察長理論還是環(huán)境權理論,或因其理論的適用范圍的限制或因其理論本身的缺陷而無法為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筆者認為,公共信托理論和私人檢察長理論以理論假設的方式為私主體提起環(huán)境公益訴訟提供了可被接受的依據,但理論假設適用于環(huán)境公共利益的維護的確存在適用條件上的一些障礙;從應然的層面來說,環(huán)境權理論比虛構的公共信托理論和私人檢察長理論在解釋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訴權基礎方面更有說服力,然而環(huán)境權在我國至今還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以一個尚未確立的權利去支撐一個正在構建中的制度,的確顯得有點力不從心。其實,無論以何種理論解釋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訴權基礎,都必須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環(huán)境公共利益為何可以轉化為私主體訴諸司法之權利?
筆者認為,從根本意義上而言,環(huán)境公益與私人利益的內在關聯(lián)是環(huán)境公共利益轉化為私主體訴諸司法之權利的最終根據。環(huán)境公益與私人利益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一方面,環(huán)境公益有著不同于私人利益的特征。作為一種共同的善,環(huán)境公益具有普惠性、均享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征。環(huán)境公益并不歸屬于任何一個特定的個體,也并非個人利益的總和,“它實質上是在共同體內不受任何人自發(fā)控制的利益”。另一方面,環(huán)境公益與私人利益又密不可分。公共利益概念的爭議性和其邊界劃定的艱難性恰恰佐證了公益與私益的內在關聯(lián)性。作為一般的、普遍的環(huán)境公益寓于作為個別的、特殊的私人利益之中,離開具有個性特征的具體的私人利益,環(huán)境公益就只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同時,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實現(xiàn)的條件,“眾多權利都是以捍衛(wèi)個人自由的名義而提出的,但其實現(xiàn)卻有賴于確保公共利益的社會背景。沒有公共利益作支撐,這些個人權利將無法實現(xiàn)其既定目標”。當環(huán)境公益表現(xiàn)為共同的善時,我們習以為常地共享著,但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仍然不夠。然而,一旦共同的善受到嚴重損害而轉化為共同的惡(如霧霾)時,共同善的重要性即凸顯出來。當環(huán)境公益損害日益普遍而行政救濟乏力并威脅到私益的享有時,私主體采用補充救濟方式就成為必然。“對個人而言,他所享有的權利所能達到的公共利益比他享有此權利更重要。”正是源于環(huán)境公益不能歸屬于任何一個特定的主體,傳統(tǒng)的私益訴訟難以有效維護環(huán)境公益,也正是環(huán)境公益不歸屬于任何主體卻與任何主體都有利益關聯(lián)的特性,賦予了私主體直接代表環(huán)境公益提起訴訟的動力和訴權依據。
環(huán)境公益與私人利益的內在關聯(lián)促使環(huán)境公益的歸屬主體與環(huán)境公益的代表主體出現(xiàn)了分離,也成為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能夠擴大傳統(tǒng)“訴之利益”的救濟范圍和突破“當事人適格”理論的正當性基礎。但這種突破是否意味著公益訴訟已超出現(xiàn)有訴訟理論的制度框架而成了一種獨立的訴訟類型呢?考察訴訟理論中已有的制度安排后發(fā)現(xiàn),雖然在一般情況下訴訟當事人與實體權利主體是一致的,但訴權與實體權利主體相分離的現(xiàn)象也并不鮮見。訴訟法學界一般認為,訴訟擔當、訴訟承擔、訴訟信托和代位訴訟是訴權與實體權利主體相分離的基本類型。
環(huán)境公益最終歸屬于社會公眾,卻并不屬于任何一個特定主體,因為任何一個特定主體是社會公眾中的一分子,卻不是社會公眾本身,因此,任何一個主體直接代表環(huán)境公益提起的訴訟均屬于利益歸屬主體與利益代表主體相分離的情形。利益歸屬主體與利益代表主體的分離有效融合了私益與公益之間的界限,這一現(xiàn)象在訴訟法中表現(xiàn)為訴權與實體權利主體相分離的制度安排。環(huán)境公益訴訟應當歸為訴訟信托的范圍,只是將訴訟信托的當事人范圍從傳統(tǒng)的社會團體擴展至更廣泛的主體而已。可見,與環(huán)境公益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私主體直接代表環(huán)境公益提起訴訟不會突破傳統(tǒng)的訴訟框架,而只是對已有的訴訟制度——訴權與實體權利主體相分離制度——的一種延伸。endprint
結語: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認知回歸與完善方向
否定環(huán)境公益訴訟能分為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觀點模糊了我們對環(huán)境公益訴訟性質和功能的準確定位,而理論認識上的迷霧對當前環(huán)境公益訴訟具體制度的構建亦產生了消極影響。作為這種消極影響的后果之一就是當前對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關注度明顯不夠,不僅新修訂的《環(huán)境保護法》和《行政訴訟法》沒有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蹤跡,已經走在立法前面的司法實踐中也以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居多;在理論界,構建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必要性也遠未被充分認識。
若將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主要規(guī)制對象界定為私主體的環(huán)境違法行為,那么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構建的重點是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也就無可厚非。然而,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性質、基本功能以及我國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的生成背景都決定了我國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主要規(guī)制對象是公權力主體的行政行為。因此,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制度構建重點是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而非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我國目前的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構建偏離了該制度的性質和功能預設,從而影響了該制度的良性發(fā)展和基本功能的發(fā)揮。學界應加大對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研究力度,并盡快推動環(huán)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立法進程。
參考文獻:
[1]呂忠梅,環(huán)境公益訴訟辨析[J],法商研究,2008(6):131-137.
[2]傅劍清,環(huán)境公益訴訟若干問題之探討[G]//王樹義,環(huán)境法系列專題研究:第2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45.
[3]李義松,蘇勝利,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環(huán)保邏輯與法律邏輯[J],青海社會科學,2011(1):61-66.
[4]周柑,羅馬法原論(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958.
[5]王小鋼,論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利益和權利基礎[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3):50-57.
[6]張輝,美國公民訴訟之“私人檢察總長理論”解析[J],環(huán)球法律評論,2014(1):164-175.
[7]李靜云,美國的環(huán)境公益訴訟——環(huán)境公民訴訟的基本內容介紹[G]//別濤,環(huán)境公益訴訟,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95.
[8]呂忠梅,監(jiān)管環(huán)境監(jiān)管者:立法缺失及制度構建[J],法商研究,2009(5):139-145.
[9]梁慧星,開放納稅人訴訟以私權制衡公權[N],人民法院報,2001-04-13(03).
[10]薛波,元照英美法詞典[K],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01.
[11]徐祥民,凌欣,陳陽,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理論基礎探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2010(1):149-155.
[12]Joseph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Essays in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Politics [M]. The Clarendon Press,1994.
[13]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M]. The Clarendon Press, 1986:251.
責任編輯:邵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