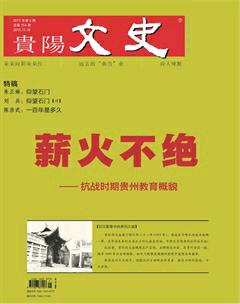老師是影響一生的人
楊甜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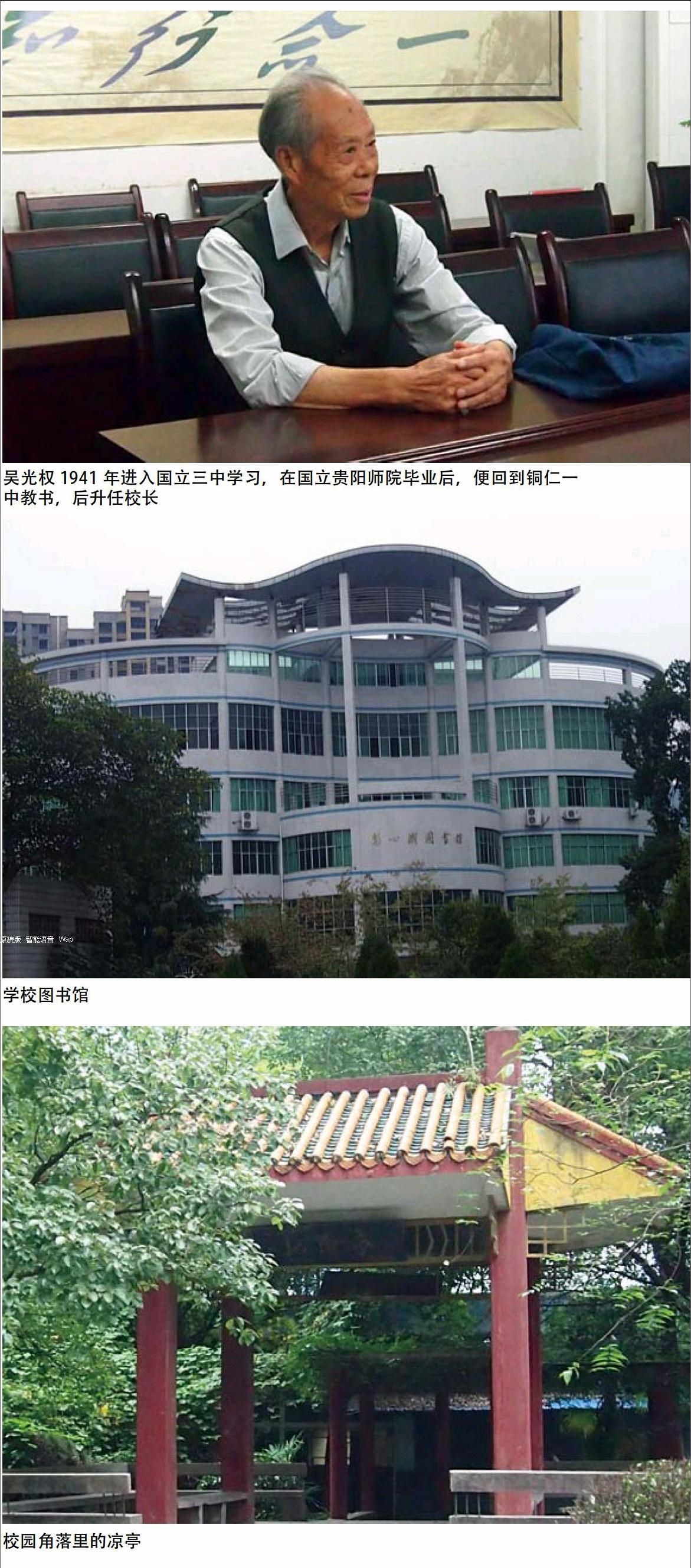
“老師是影響一生的人”。這樣類似的命題,我們都不陌生,在學生時代里恐怕每個人都寫過這樣的800字作文。然而,終究不是每個人對這句話都能真真切切地有所體會。或許是這一生確實沒遇上個如同明燈般的老師,也或許早已將那些金玉良言丟在叛逆的年少時代。
什么時候會再想起老師呢?大概,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校長坐在你面前,跟你細細講述他學生時代遇上的老師開始吧。
吳光權,銅仁第一中學的老校長。從曾經的國立第三中學到如今的銅仁市第一中學,吳光權的身份在這所學校不斷變化著——學生、老師、教導主任、校長。但不管多少次提及自己的人生歷經,他始終念念不忘的,是在國立三中讀書時對自己影響深刻的老師們。
1941年,年僅14歲的吳光權通過考試進入國立三中,就讀實驗初中部。他的語文老師是一位50多歲、留著胡子的光頭老先生,一件藍布長衫搭配一雙白布襪。就是這樣一位衣著古板的老師,自學了英語,將現代語法與英語語法相結合來教語文。老師常對他們說的是:“文言文是過去的東西,過去的人們講的話今天不用再多做學習,你們只要懂得就好,重要的是把現代的語言學好。”這位老師還向學生推薦巴金等現代作家的作品,讓學生們的視野從傳統文言文中延展到時下的文學文化。
后來,吳光權在國立貴陽師院(現貴州師大)讀書時,老師要求學生以《韓信匍匐胯下》為題作文,吳光權便用白話文寫了一篇。到了第二個星期發作文,老師就在課堂上問“誰是吳光權?”吳光權心想又要被批評了,默默站起來后,老師就語重心長地說:“哎呀,太可惜了,你這么年輕,思路認識這么清晰,寫的文章也好,但是為什么要用白話文、而不用文言文寫呢?”吳光權一時被問得不知如何回答。但此后的作文,他卻依舊堅持用白話文寫作。
教吳光權英語的是一位姓陳的老師。陳老師講課所用的教材都是他自編的講義,別具風格。吳光權畢業時,陳老師還將自己的講義送了一整套給他。受到鼓勵的吳光權后來就讀國立貴陽師院,毅然選擇了英語專業,繼承老師的衣缽。但令吳光權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陳老師曾經在課堂上所說的關于“賭博”一事。陳老師十分反感在抗戰國難時期還有心思去賭博的人,“一上場就想把別人的錢全部贏過來的人,沒有哪一個是好心腸的。”就這樣,吳光權又為自己樹立了一個今生絕不賭博的信念。
陳老師的愛人是一位教生物的老師。抗戰時期,又在地處偏遠的銅仁,根本是沒有條件做實驗的。但老師堅持實踐教學,帶著學生們去稻田里捉蝗蟲、青蛙,教學生用三角放大鏡觀察、解剖、畫圖。當時,銅仁有一處叫“死娃塘”的地方,是一個遺棄死嬰的地方。難以想象的是,這位生物老師竟然找到了一具死嬰帶回學校,自己解剖后制作成標本,供教學使用。這樣先鋒前衛的創造性教學給吳光權留下了深刻印象,后來他做了校長,看著如今老師們的教學方式都不禁唏噓。
王老師是一位地理老師。這位老師上第一節課的時候,除了一支筆什么都沒帶,還豪不謙虛地說:“以后我來考你們,今天請你們來考我,凡是有關地理的東西隨便你們提問。”起初,面對這種另類的教學吳光權和他的同學們還有些拘謹,到后來提的問題越來越多。同學們發現這位地理老師不但能把他們的問題一一解答,更能說得有聲有色。沒有去過巴黎,卻把巴黎的街頭景貌描繪得精彩細致;說起新疆的哈密瓜,也能把學生說得口水直流。
談及這些老師,吳老校長是不甚敬佩、懷念的。這些老師都是從抗戰淪陷區內遷至此,有的甚至因為戰爭家破人亡。到了這里,他們卻依舊一心一意地教書育人,將自己愛國敬業的心意,全部付諸于學生身上,熱愛教育、熱愛學生。有位老師為了養家,除了在學校任教以外,還得到外面兼課,唯一的一件衣服從星期一穿到星期六,周末才脫下來洗。要是遇上下雨天,還得用火烤千,下個星期才能繼續穿。但就是這樣一位老師,上課從不遲到,從不耽誤學生任何一門課程。
“老師對學生的影響,絕不是一時的,而是一生。”吳老校長每說一位老師都要發出這樣的感嘆。在吳老校長看來,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老師,有了這樣強健的師資力量,國立三中優良嚴謹的校風才得以彰顯發揚,學校的教學質量才有了名列前茅的輝煌成就。抗戰結束后,來自江浙一帶的這些老師們大多遷回原籍,只有少數幾位選擇留在了銅仁。要說對這些精英教師的離開不覺得惋惜,那是假的。但好在,銅仁一中并沒有因此而失去原有的光彩。老師們的精神已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演變成“仁、實、勇、毅”的校訓永遠在這所校園留存。銅仁一中也繼續在貴州的教育界大放異彩,在1984年至1991年吳光權任校長期間,銅仁一中已躋身貴州省級重點中學,無論是升學率還是影響力與貴陽一中皆可一比。
銅仁當地人都說,銅仁一中的校址是塊孕育英才的風水寶地。今天,銅仁一中已經搬遷至新校區,而位于市區的老校區則作為新成立的銅仁一中初級中學校址。學校2014年7月開始招生,至2015年已經招收了2屆學生940人。學校成立的初衷是傳承銅仁一中的教育文化,目標是在3至5年內,打造成銅仁市的一流初級中學。
70多年前,因為抗戰,國立三中將教育的種子播散在銅仁,這方土地培育了無數優秀學子。70余年時光,這所學校幾經更名,唯一不變的,是留存于這方土地之上不滅的教育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