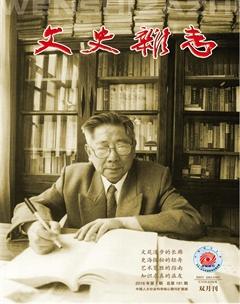略說(shuō)蔡文姬的書法承續(xù)
子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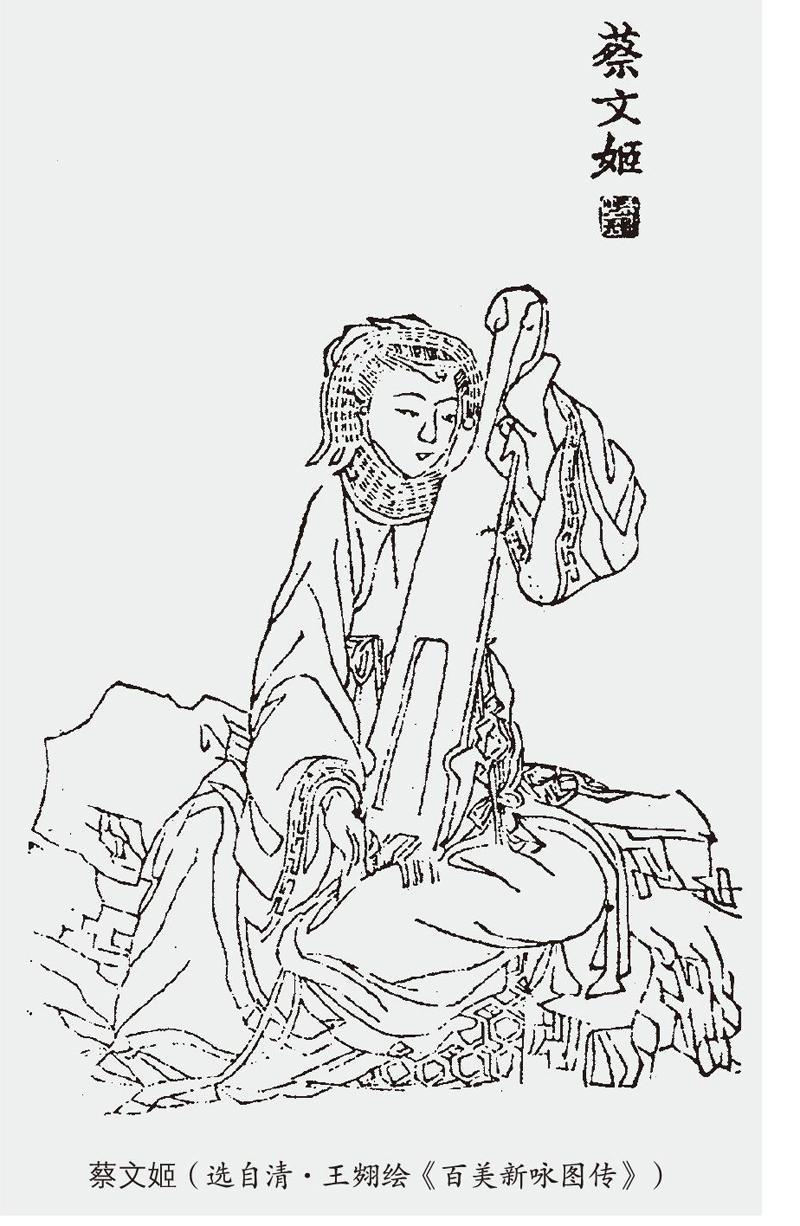
據(jù)《后漢書·蔡邕列傳》及其他史料等載,蔡文姬的父親蔡邕是東漢末的一代大書法家。據(jù)說(shuō)蔡邕能畫,更擅書,深諳篆書、隸書之妙,尤以隸書著稱,其結(jié)構(gòu)嚴(yán)整,點(diǎn)畫俯仰,體法多變,有“骨氣洞達(dá),爽爽有神”之譽(yù)。他曾于洛陽(yáng)鴻都門見(jiàn)粉壁工匠用帚蘸白粉寫字,得到啟發(fā),創(chuàng)“飛白”書。這種書法,筆畫中絲絲露白,像枯筆寫成的模樣,漢魏時(shí)曾廣泛流播,并用之裝飾、題署宮闕。
據(jù)《后漢書·蔡邕列傳》記,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議郎蔡邕和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等人,鑒于當(dāng)時(shí)儒家經(jīng)籍輾轉(zhuǎn)傳抄,多生謬弊,乃“奏求正定六經(jīng)文字,靈帝許之”,于是便開(kāi)始了中國(guó)歷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經(jīng)刻制工程;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告成,歷時(shí)凡九年。其因始刻于熹平年,故稱《熹平石經(jīng)》。《熹平石經(jīng)》的內(nèi)容包括《周易》《尚書》《魯詩(shī)》《儀禮》《春秋》《公羊傳》和《論語(yǔ)》,書丹者除蔡邕外,還有堂溪典等人。石經(jīng)刻成之后,立于都城洛陽(yáng)太學(xué)門外(今洛陽(yáng)城南30里洛水南岸的朱圪村)。其46方經(jīng)石,各高1丈許,廣4尺,兩面刻,駢羅相接,非常壯觀,《后漢書·蔡邕列傳》說(shuō):“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盛況。
張榮慶先生在《古代藝術(shù)三百題·熹平石經(jīng)》里指出,《熹平石經(jīng)》的書法為漢隸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因系官方巨制,書丹者自當(dāng)是如蔡邕一流的國(guó)手。例如其間的《周易》經(jīng)石,其結(jié)體方正,字字中規(guī)入矩,一絲不茍,點(diǎn)畫布置均稱工穩(wěn),可謂無(wú)懈可擊;用筆則方圓兼?zhèn)洌瑒側(cè)嵯酀?jì),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宮殿廟堂。梁武帝《書評(píng)》云:“蔡邕書,骨氣洞達(dá),爽爽如有神力。”后來(lái)也有人譏其過(guò)于工整,而冠之以“館閣派”。其實(shí)它整飭而不刻板,靜穆而有生氣,和明清以來(lái)風(fēng)行的拘謹(jǐn)呆滯的“館閣”字,不可同日而語(yǔ)。惟其如此,《熹平石經(jīng)》集漢隸之大成,不但在當(dāng)時(shí)被奉為書法的典范,而且流風(fēng)所及,至深且遠(yuǎn)。漢字字體由隸變楷的過(guò)渡,《熹平石經(jīng)》起了橋梁的作用。因此,范文瀾先生在《中國(guó)通史簡(jiǎn)編》第二編里如是寫道:
兩漢寫字藝術(shù),到蔡邕寫石經(jīng)達(dá)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畫工書,八分(指有波磔的隸書)尤為精工。一七五年(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以八分體寫《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禮記》《論語(yǔ)》五部經(jīng)書,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塊,立在大學(xué)講堂前。這是有名的熹平石經(jīng)。從經(jīng)學(xué)方面說(shuō),它校正了五經(jīng)文字;從藝術(shù)方面說(shuō),石經(jīng)文字是兩漢書法的總結(jié)。
張榮慶據(jù)《魏書》《隋書》等典籍記載說(shuō),自晉室南遷,洛都文物多被摧殘。北魏之初,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海州刺史,毀取太學(xué)經(jīng)石以建寺塔,遂致頹落。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公元518年),國(guó)子祭酒崔光曾議請(qǐng)修補(bǔ)未成。東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自洛陽(yáng)徙石于鄴都(今河北大名縣東北),行至河陽(yáng),值岸崩,遂沒(méi)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復(fù)由鄴城遷洛陽(yáng);隋開(kāi)皇六年(公元586年),又自洛陽(yáng)載至長(zhǎng)安,其后,營(yíng)造之司用做柱礎(chǔ)。唐貞觀初年,魏始收聚之,已十不存一。(《隋書·經(jīng)籍志》)后來(lái)連這些也不知去向。北宋時(shí),曾在洛陽(yáng)太學(xué)舊址出土過(guò)石經(jīng)殘片,但為數(shù)不多。直到近代,復(fù)絡(luò)繹出土(洛陽(yáng)最多,西安次之),見(jiàn)于馬衡《漢石經(jīng)集存》者已有大小殘石500余塊。其中最大的一塊是1925年洛陽(yáng)出土的《周易》上段殘石,兩面刻,合490余字,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1929年于同地又出《周易》下段,現(xiàn)藏陜西省博物館。此外,洛陽(yáng)博物館、國(guó)家圖書館也分別藏有《熹平石經(jīng)》殘石。
唐人張彥遠(yuǎn)《法書要錄》卷一中有“傳授筆法人名”一項(xiàng),其說(shuō)云:
蔡邕受于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鐘繇。鐘繇傳之衛(wèi)夫人(即衛(wèi)鑠)。衛(wèi)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xiàn)之。王獻(xiàn)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虞。王僧虞傳之肖子云。肖子云傳之僧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授于歐陽(yáng)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侄彥遠(yuǎn)。彥遠(yuǎn)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yáng)冰。陽(yáng)冰傳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傳終于此矣。
對(duì)于唐人張彥遠(yuǎn)之說(shuō),郭沫若先生在《五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載《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里批評(píng)道,張彥遠(yuǎn)的“傳授說(shuō)”,有一大部分不可信。因?yàn)樗^“蔡邕受于神人”已經(jīng)是神話;崔瑗早于蔡邕;鐘繇比蔡文姬的年齡大,地位也高得多,所謂“文姬傳之鐘繇”,也是靠不住的。不過(guò),郭沫若又從張彥遠(yuǎn)堅(jiān)信蔡文姬能書這一點(diǎn)著手發(fā)覆,指出:“蔡文姬的墨跡在唐代可能還有留傳,故構(gòu)成了這種有關(guān)書法傳授的說(shuō)法。”這里,郭沫若又顯然同意張彥遠(yuǎn)所堅(jiān)持的,即認(rèn)為蔡邕的確將書法藝術(shù)傳給了蔡文姬,蔡文姬也應(yīng)是一位書法家。
作為論據(jù),郭沫若舉出了北宋初期所出現(xiàn)的《胡笳十八拍》的墨卷。它最初是刻印在宋初的《淳化秘閣法帖》(《淳華閣帖》)中。它寫有《胡笳十八拍》最前面的兩句——“我生之初尚無(wú)為,我生之后漢祚衰”,是用章草體寫成的。收入《淳化閣帖》制成帖文以后,在帖文右面有“蔡琰書”三字。
宋初《淳化秘閣法帖》是在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就淳化閣所藏墨跡,命王著合南唐《建業(yè)帖》而摹刻的。不過(guò),郭沫若又認(rèn)為,蔡文姬所書14字是否由墨跡摹刻,或由《建業(yè)帖》復(fù)刻,不得而知。但其來(lái)歷,至遲當(dāng)追溯到唐代,是可以斷言的。
郭沫若還指出,黃庭堅(jiān)(即黃山谷)也曾看見(jiàn)蔡文姬那14個(gè)字。在《黃山谷全集》卷二十八《跋法帖》二十三條中有一條說(shuō):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余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黃山谷評(píng)蔡襄書有云:
蔡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氣頓挫,時(shí)有閨房態(tài)度。
郭沫若評(píng)議說(shuō),黃山谷所見(jiàn)到的雖然也只有“我生之初尚無(wú)為,我生之后漢祚衰”兩句,但既云“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可見(jiàn)在黃山谷之前有人見(jiàn)過(guò)十八章的全文,他是在轉(zhuǎn)錄前人傳說(shuō);再就黃山谷本人來(lái)說(shuō),則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不僅相信《胡笳引》十八章是蔡文姬著的,而且還相信是她自己寫的。
但是,蔡文姬書14個(gè)字,宋代也有人懷疑是假托的,如米芾,但他沒(méi)有講出理由來(lái)。對(duì)此,郭沫若在《六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載《光明日?qǐng)?bào)》1959年8月4日)里推想道:原文可能是寫在竹簡(jiǎn)上的東西,一簡(jiǎn)14字,全詩(shī)應(yīng)有90多簡(jiǎn)。估計(jì)詩(shī)后還當(dāng)有年月日和蔡琰的署名;但因簡(jiǎn)冊(cè)散亂或部分焚毀,好事者僅拾取其第一簡(jiǎn)而保之,俾得流傳于世。觀黃山谷所云“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可見(jiàn)在黃山谷之前乃至在北宋之前,是有人看見(jiàn)過(guò)蔡琰自書的全文的,黃即本之以立說(shuō)。不然,僅僅14個(gè)字,雖然知道是《胡笳十八拍》的開(kāi)頭兩句,何以便知道是蔡琰書?那豈不是不近情理?
簡(jiǎn)牘之制,漢末及魏、晉猶見(jiàn)使用。如蔡文姬之父蔡邕《答詔問(wèn)災(zāi)異八事》,敘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七月十日蔡邕與馬日、張華、單揚(yáng)等“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見(jiàn)《蔡中郎文集》卷六)。又如《通典》(卷五十五禮十五)載晉博士孫毓議,言封王告廟冊(cè)文當(dāng)以“竹冊(cè)篆書”,四時(shí)享祀祝文但用“尺一,白簡(jiǎn)隸書”。簡(jiǎn)牘之用自晉以后似即廢棄,而普遍以紙帛代之。偶爾有用玉簡(jiǎn)的,這是變例,如成都王建墓所出玉冊(cè)即其物證。寺廟中的竹簽之類當(dāng)然也是簡(jiǎn)牘的孑遺,但嚴(yán)格地說(shuō)其已不能算是簡(jiǎn)書了。
郭沫若在上述文章里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蔡文姬手書的《胡笳十八拍》的確是簡(jiǎn)書,否則很難解釋為什么現(xiàn)在僅余開(kāi)頭兩句14個(gè)字。因此郭沫若堅(jiān)持說(shuō)《淳化閣法帖》所收的蔡琰書14字,應(yīng)當(dāng)是真跡。
作為對(duì)郭沫若此論的支持,筆者認(rèn)為還有《后漢書·董祀妻列傳》的一條記載。這條記載,系在曹操赦免了董祀死罪以后,當(dāng)時(shí)——
操因問(wèn)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shí)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當(dāng)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于是繕書送之,文無(wú)遺誤。
真草當(dāng)指楷書和草書。正因?yàn)椴涛募Ю^承了父親的書法藝術(shù),并且十分相信自己的造詣,因而才以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的理由,婉拒了曹操派10人幫助書寫的提議。倘若文姬書法功底不濟(jì),她敢于如此拒絕嗎?并且還要以真草兩種字體聽(tīng)?wèi){選擇,后來(lái)果然書成。“文無(wú)遺誤”,不僅是對(duì)文姬保存父親資料之非凡的記憶力的贊嘆,而且也是對(duì)她的書法藝術(shù)的爐火純青功夫的首肯。也正是基于此,唐人張彥遠(yuǎn)才會(huì)在《法書要錄》里將文姬列為蔡邕書法的傳人,而且還將她捧為三國(guó)兩晉的一代書法宗師——鐘(繇)王(羲之)的師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