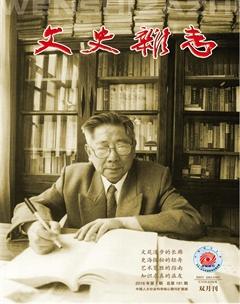一條石板路千年洛帶城
李天義 張學梅

從文明形態(tài)著眼,城市與農(nóng)村,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永遠都是難于相融的一對矛盾。改革初始,伴隨城市化的進程,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文化正從我們眼前淡出:三峽大壩建成,使纖夫詠唱了數(shù)百年的“船工號子”消失;通俗歌曲的彌漫,導致傳統(tǒng)的民歌失色……凡此種種,都引起社會學家的深度思考。1978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拯救面臨滅絕的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對我國上千種古文明和原生態(tài)文化列出條目,要求當?shù)卣袑嵞贸鰧Σ吆痛胧员Wo和挖掘伴隨人類文明走到今天的那些優(yōu)秀文化形態(tài)。洛帶古鎮(zhèn)就是這樣一種值得政府保護和世人珍視的文明模板。它古拙的木制建筑,豐富多樣的客家文明形態(tài),均應受到國家重點搶救和保護。
一、古鎮(zhèn)建筑風貌
文明“civilization” ,是人類審美觀念和文化現(xiàn)象的傳承、發(fā)展、糅合和分化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總稱。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研究員黃萬盛先生將其理解為:“那些化育心靈的人類智慧、歷史記憶、情操體驗。”[1]文明形態(tài)通俗講為,集結在城邦生活群落的生活習俗、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建筑特征、飲食習慣、語言表述、音樂舞蹈等——這是這一群體最具特點的外形和世俗風貌,有著普世不變的文明形態(tài)。洛帶古鎮(zhèn)坐落于成都市東郊,龍泉驛區(qū)北部,西距成都市區(qū)18公里。該城于三國時期建鎮(zhèn),傳說是因蜀漢后主劉禪的玉帶落入小鎮(zhèn)旁的一口八角井而得“落帶”之名,后演變?yōu)椤奥鍘А薄B鍘ф?zhèn)俗名甑子場,是成都東山五場之一。洛帶鎮(zhèn)內(nèi)古建筑列立街道兩邊。該城依山傍水,背靠龍泉山,面臨成都平原,蜿蜒曲折的街道恰似一條玉龍盤旋。全鎮(zhèn)長略一公里左右,采用一條暗紅色石板路鋪成;進城的各條路為長條青石鑲嵌,平整美觀,干凈舒展。城內(nèi)修建有一條清潔溝渠,玉龍泉水穿城而過,帶著山野的清新和古老鄉(xiāng)鎮(zhèn)文明的氣息。涓涓的泉水經(jīng)由洛帶古鎮(zhèn),從每家的店鋪和居所前面流淌穿梭,給人的感覺別致且寧靜,溫馨又愜意。洛帶古鎮(zhèn)山水相簇,背山面水,城中古屋鱗次櫛比,木質(zhì)雕窗,玉砌屋頂,石缸、石盆舉目可見,條形紅石鑲嵌整個古城……所有這一切,別致古雅,符合中國古人造物建城的審美標準。根據(jù)中國風水學說,古鎮(zhèn)洛帶選址考究,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的美學特點。“堪輿[2]重選址,也就是對客觀環(huán)境的取舍,這也正是建筑的前提條件。上至立國定都,次至州郡縣邑,下至村坊街宅,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必須考慮到具體環(huán)境對居住地的影響。”[3]最有意味的是,在這座古鎮(zhèn)的街沿上,每隔50米即有一雕琢的石缸。石缸古樸雅致,其側面雕有美麗的圖案,形態(tài)各異,紋飾鮮明。據(jù)當?shù)厝酥v,這個石缸絕不僅僅只為裝飾之品,還用于防火。古鎮(zhèn)歷史久遠,沿街居民的房屋均為木制。從全鎮(zhèn)安全出發(fā),避免一家起火殃及萬戶,因而在50米間距就放置一個石缸,防患于未然。時下,隨著時間的演進,古鎮(zhèn)部分居民門窗已安裝防火材料,但這種石缸盛水防火的生活習俗,卻延續(xù)至今,成為古鎮(zhèn)一道靚麗的風景。
洛帶古鎮(zhèn)的民居大都屬于傳統(tǒng)的瓦房,房頂上雕梁砌玉,飛檐畫壁。在屋的木制橫檔梁上面,均有瓦當作為裝飾。這種裝飾最早出現(xiàn)在秦朝。秦朝瓦當為圓形,雕飾圖紋,氣勢恢弘。洛帶古鎮(zhèn)的瓦當則相對簡潔,正面為蝴蝶雙翼展翅,下端為清朝古銅錢開口的菱形狀。從這一圖案可以判斷,這座古鎮(zhèn)可能在清朝重新翻建過。在一家旅社,我們看見了據(jù)稱是清朝皇帝雍正和嘉慶二帝的工筆彩畫。詢問該社的主人得知,正是借助清朝二帝的皇恩,古鎮(zhèn)才得以翻修,洛帶才得以變成今天這樣的娟秀美貌,成為風光宜人的AAAA級旅游勝地。
二、洛帶古鎮(zhèn)的飲食文化
傳統(tǒng)是根,民族是魂。傳統(tǒng)文化就是人類生活積淀下來的寶貴資料和經(jīng)驗,是思想的結晶,“它是留存在歷史文本中有生命的偉大智慧。”[4]洛帶客家人雖然來自廣東、福建、山西和江西不同地域,但他們大多保持良好的生活習俗。洛帶街入口處,擺放著許多農(nóng)家蔬菜。當?shù)乜图胰藢⒆约曳N植的各色蔬菜挑到市場上銷售。洛帶當?shù)剞r(nóng)戶到古鎮(zhèn)銷售農(nóng)產(chǎn)品受到政府的極力保護,后者為他們提供場所和市場優(yōu)惠政策,很少收取攤位費。我們在考察洛帶地區(qū)生態(tài)文化中還發(fā)現(xiàn),當?shù)鼐用袢栽谘赜梦嗤┕驮斫莵硐搭^洗衣,以此保持原有的生活情趣不被現(xiàn)代文明浸染。洛帶地區(qū)最著名的莫過于當?shù)氐臎龇郏@是客家人手工自制的一種小吃。這種小吃源于清朝。在一家標有“傷心涼粉”的店鋪中我們看到這樣的介紹:“客家人從廣東等地出發(fā),遷入四川后仍保持著當?shù)丶亦l(xiāng)的民俗風情,實屬不易。這種民俗采用豌豆、辣椒為其特產(chǎn),用純手工磨制的粉狀調(diào)成可口涼粉,并加以十二種輔助料調(diào)拌而成”。看到以上文字,我們立即轉過頭考察石案上放置的調(diào)料品種都有哪些,是否真地如文字所言那樣豐富。用心點數(shù)了一下,的確為十二調(diào)料:有花生、大頭菜、芝麻、小紅剁椒、味精、甜面醬、辣子油、香油、白糖、蒜茸、醋、生抽,有些另加蔥末和香菜為涼粉提色。涼粉的質(zhì)地也很值得大家注意:有綠豆涼粉、花生涼粉、紅苕涼粉、黃豆涼粉,黃白米色三色相間大大地提升了這種民間小吃的檔次。客家人生在異鄉(xiāng),從廣東、山西、福建等地遷徙至四川盆地。沿海城市不喜食辣,口味嗜甜偏清淡,尤其追求蔬菜的原色和鮮美。他們到四川盆地山區(qū)后,客家飲食文化也隨著巴蜀地方特點而發(fā)生變異,飲食中少許添加辣子,對于川人講究食物麻、辣、鮮、嫩、燙的特色也極為認可。因為,在多雨且陰冷潮濕的四川盆地,很少見到明媚的陽光。人們成天生活在陰霾密布的生活環(huán)境中,以爆辣和麻燙等食物來調(diào)節(jié)情緒,趕走身體內(nèi)積郁的陰冷寒氣十分必要。入川的異鄉(xiāng)人在四川稱之為客家人,洛帶是四川客家人最為集中的地方。他們在細雨連綿的巴蜀地域,永遠記得他們來自何方,對海洋文化與山地文化進行了融合與嫁接。如在“川北涼粉”的基礎上,添加白糖、蠔油、生抽、香油、香菜、花生、黃豆等物,變成了色澤鮮艷,味道濃郁爽口的,適合現(xiàn)代人吃的一種食品,并借以表達對家鄉(xiāng)的思念之情。在涼粉二字上附上“傷心”一詞,就是這種思鄉(xiāng)之情的表述。“傷心涼粉”是地地道道海洋文化與盆地文化的結合物,是客家人對生命意義的一種詮釋,也是他們托物言志的一種方法,體現(xiàn)出客家人適應環(huán)境、頑強生存、樂觀而開放的高貴品質(zhì)。
魯迅先生曾經(jīng)說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從生活特性和飲食習俗看民族,那是一種民俗文化的呈現(xiàn)。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朱漢民解釋民俗文化:“民間民眾的風俗生活文化的統(tǒng)稱,也泛指一個國家、地區(qū)集居的民眾所創(chuàng)造、共享、傳承的風俗生活習慣,是在普通人民群眾的生產(chǎn)生活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質(zhì)的、精神的文化現(xiàn)象。”[5]洛帶古鎮(zhèn)濃郁的客家鄉(xiāng)情,是客家文化與巴蜀文化相融匯、沿海風情與內(nèi)陸山地習俗相碰撞的產(chǎn)物,體現(xiàn)出多元文化的色彩。
三、洛帶其他的特色文化
在洛帶有一個具有傳統(tǒng)文化特色的郵局很是令人感到欣慰。這個郵局是清朝遺留下來的文化古跡。在郵局的門前塑有一個古銅像,頭頂草帽,肩挑兩個布袋似的東西。從這一造型可以看出,清代信件的傳遞只能靠人工完成。這一古色古香的郵局為洛帶增色不少。每逢慶典與文化活動,郵局成為接待外賓和他省文化要員的地方。改革伊始,文化成為國家經(jīng)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在“經(jīng)濟搭臺,文化唱戲”的當下,龍泉政府組織當?shù)剞r(nóng)民,在忙完收割季節(jié)后排練具有客家特色的文藝節(jié)目。目前,洛帶客家正規(guī)的演出隊達六個。這六個團隊大小不等,少則40人,多則100人。這是以宣傳客家舞蹈、音樂、說唱、曲藝為目的的演出團體,平時活躍在成都地區(qū),偶爾也參加全國客家音樂文化活動。由于受到當今城市文明的影響,居住在四川境內(nèi)的客家音樂文化已瀕臨消亡,甚至滅絕。洛帶政府遂組建客家農(nóng)民演出團隊,以保護和延續(xù)生態(tài)文明。洛帶古鎮(zhèn)是現(xiàn)代文明與傳統(tǒng)文明交織接踵的地方。這里距離成都市區(qū)近在咫尺,都市族群樂于來此消遣。他們最喜歡洛帶的客家人演唱客家山歌,這種山歌至今保持著廣東梅縣的文化痕跡,是客家人賴于生存的一種精神寄望,是客家文化的“活化石”。對于客家山歌的文化研究,星海音樂學院碩士生導師溫萍認為:“它源于中原古代民歌,是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延展,是客家先民大舉南遷時所遺留下的精神財富。”[6]
在洛帶古鎮(zhèn)除了音樂以外,書畫也極具特色。據(jù)說該鎮(zhèn)有許多知名書法家和畫者。我們在一家畫廊看見有這樣的書法名句:“名畫要如詩句讀,古琴化著水聲聽。”該名句以行書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筆觸蒼勁,行筆講究,內(nèi)容含蓄,韻味濃郁。該書法出自我國書畫家啟功之手。僅此一點,即可看出這座古鎮(zhèn)所蘊含的文化底蘊。在洛帶古鎮(zhèn)還有一特色最值得一看,那就是客家人建立的會館。在這條街道上,廣東會館、江西會館、湖廣會館吸引了眾多人的眼球。我們重點參觀了湖廣會館,草草瀏覽了江西會館。湖廣會館的門牌上寫著這樣的條幅:“錦江東流歸大海,黃鶴西上謁禹王。”[7]這句名詩成為湖廣會館的文化標簽。晉、唐以來中原大地戰(zhàn)亂頻繁,天災不斷。居住在黃河沿岸的百姓,不堪忍受戰(zhàn)亂的摧殘,舉家南下,再從今天的廣東、廣西、福建等地移至四川。歷史上從沿海城市向四川盆地內(nèi)陸遷徙,一共有五次大規(guī)模的運動。在歷史的長河里,史學家往往將從兩廣、福建遷往內(nèi)地的客商、居民稱之為客家,后來這個詞的外延擴展到從山西、江西、湖南等地離家求居的異鄉(xiāng)族群。客家人中不僅有語言學家王力,新四軍軍長葉挺,還有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和大文豪郭沫若。這些知名人士的到來,為客家文化注入了強大的生命源體。
歷史為世界增色,文化為時代添彩。客家人留駐四川帶來的不僅是他們原有的風俗習慣,還帶來了他們銳意進取、生氣勃勃的生命風采。
注釋:
[1][4]黃萬盛:《人類學與大學理念》,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第20頁。
[2]堪輿:即風水,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動,堪即天,輿即地,堪輿學即天地之學。
[3]李城志、賈慧如:《中國古代堪輿》,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頁。
[5]朱漢民:《中國傳統(tǒng)文化軟實力要素研究綜述》,載張國祚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頁。
[6] 溫萍編著《客家音樂文化概論》,上海音樂出版社 2007年版,第1-2頁。
[7] 該詩句出自客家山歌。
本文系2014年四川省社科規(guī)劃學科共建項目“中國傳統(tǒng)樂器陶塤創(chuàng)新研究與開發(fā)”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SC14XK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