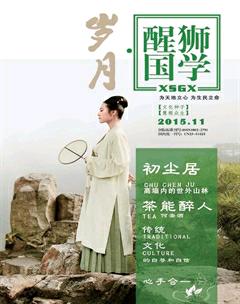鹖冠搖搖 圣心昭昭
南枝云山
《鹖冠子》作者相傳為戰(zhàn)國(guó)時(shí)楚國(guó)隱士鹖冠子。《漢書·藝文志》稱作者為“楚人”,“居深山,以鹖為冠”。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義》佚文也說:“鹖冠氏,楚賢人,以鹖為冠,因氏焉。鹖冠子著書。” 據(jù)此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大概形象:懷濟(jì)世之才而不被重用,故隱居深山,以鹖之羽為冠,發(fā)憤著書,瀟灑楚狂人也。
此書多闡述道家思想,也有天學(xué)、宇宙論等方面的內(nèi)容。原著不分篇目,后世按內(nèi)容分為十九篇。行文古奧典雅,字里行間皆表現(xiàn)出“道化腐朽為神奇,潤(rùn)萬物而無聲”的神奇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其對(duì)后世影響頗深,杜甫、陳子昂、劉勰等人不僅以鹖冠子自喻,且對(duì)《鹖冠子》一書博辯宏肆的文辭、天下大同的政治主張亦稱道不已。唐代大儒韓愈贊嘆道:“使其人遇其時(shí),援其道而施于國(guó)家,功德豈少哉!”其經(jīng)天緯地之功用可見一斑。
然今人緣何對(duì)此書不甚知之?皆因柳宗元在其《辯鹖冠子》一文中言此書“盡鄙淺言也,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自是以來,《鹖冠子》的偽書之名幾成定論。由于柳宗元的影響力,長(zhǎng)期以來敢為其翻案者幾乎沒有。近代學(xué)者呂思勉指出:“此書詞古意茂,決非后世所能偽為,全書多道、法二家論,與《管子》最相似。”幸而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了《黃帝四經(jīng)》等大量帛書,有學(xué)者研究發(fā)現(xiàn),《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書中有不見于別書而與《鹖冠子》相合的內(nèi)容,證明了其為戰(zhàn)國(guó)時(shí)所作,為證明其并非偽書提供了有力證據(jù)。自此《鹖冠子》方重新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關(guān)注。
《鹖冠子》繼承和發(fā)展了先秦道家一向關(guān)心人的生存境遇,具有濃郁人本主義色彩的特點(diǎn),十分重視人的生存與發(fā)展。該書將天道、地道與人道聯(lián)系起來,提倡尊重人的天賦稟性,肯定人的主觀能動(dòng)性,體現(xiàn)了對(duì)人自身原始生命力的尊重與關(guān)懷,蘊(yùn)涵著豐富的人文情懷。
自若則清,人之性也
《鹖冠子》對(duì)人的本性進(jìn)行了探討。《博選》在論及選賢問題時(shí)指出:“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雖然這里的“以人為本”概念與現(xiàn)在有很大差異,但它強(qiáng)調(diào)精神依附于人體,顯示了對(duì)人的重視。
《鹖冠子》對(duì)人性進(jìn)行了很好的總結(jié):“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這不僅道出了人類在生命歷程中對(duì)生死的本能態(tài)度,而且包涵著濃重的生命意識(shí)。
雖說貪生怕死是人之本性,“見遺不掇,非人情也”,但《鹖冠子》對(duì)人性并不抱失望態(tài)度。正如《泰鴻》所言:“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dòng)之則濁。”這就是說不要改變?nèi)舜緲慵儍舻淖匀惶煨裕渲小皹恪薄ⅰ扒濉北砻鳌尔i冠子》相信人性是善的,“毋”則表明對(duì)人性的肯定與尊重。
《著希》在闡述希人之道時(shí)說:“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即希望得人者不違人情,這也顯示出《鹖冠子》對(duì)人自然本性的尊重。在這點(diǎn)上,《鹖冠子》與《莊子》頗為相似,無論是物的自然,還是世事的自然,抑或本心的自然,都應(yīng)因順不悖。但其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與尊重是為了實(shí)現(xiàn)“因物之然,而窮達(dá)存”的目的,反映的是人類認(rèn)識(shí)與把握自身過程中的文化心態(tài),關(guān)注的終極目標(biāo)是人類的前途與命運(yùn),具有深厚的人文蘊(yùn)涵。
凡五不通,人之悲也
《鹖冠子》在關(guān)注人的生存與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表現(xiàn)出對(duì)人生存困境的悲憫。
它首先對(duì)人在社會(huì)生活中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博選》曰:“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在地位上,鹖冠子把人提到與天、地等同的位置,這是很了不起的人文主義思想。在《備知》中他又說:“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這是對(duì)人的能力的充分褒揚(yáng)。
對(duì)君子,他更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詞。《著希》曰:“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卻。嗜利而不為非,時(shí)動(dòng)而不茍作。”然而這樣的賢人在亂世的遭遇卻是“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無疑是對(duì)黑暗現(xiàn)實(shí)與小人得志的控訴。鹖冠子本人就是不得志的,但他并沒有牢騷滿腹地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批判個(gè)沒完,而提出人應(yīng)適時(shí)調(diào)整心態(tài),以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這是難能可貴的。《世兵》曰:“曹子去忿鹖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xì)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為知時(shí),魯君為知人。”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靈活應(yīng)對(duì),不拘泥于舊俗,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并成就大業(yè)。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知時(shí)務(wù)者吧。
鹖冠子沒有對(duì)人進(jìn)行一味的肯定,也深入總結(jié)了人的認(rèn)知局限,在《天權(quán)》中他說:“故人者,莫不蔽于其所不見,鬲于其所不聞,塞于其所不開,詘于其所不能,制于其所不勝。世俗之眾,籠乎此五也而不通。”這表達(dá)了對(duì)蕓蕓眾生的悲憫之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鹖冠子因人們生理或心理的缺陷導(dǎo)致不能正確、全面地認(rèn)識(shí)事物而哀其不幸,又因其不能沖破束縛克服自身局限而怒其不爭(zhēng),顯示出悲天憫人的情懷。
閱讀《鹖冠子》,如同沐浴在陣陣仙風(fēng)道雨中,在一片寂靜中可以聆聽往圣先賢娓娓道出的宇宙奧秘和人生真諦。我們仿佛看見那鹖冠之上搖擺的羽毛,而一顆關(guān)注生民的圣賢之心就在那搖擺間現(xiàn)于世人面前。
編輯/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