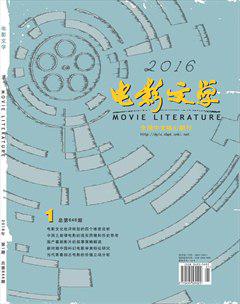虐心之旅:《贖罪》的創傷書寫
王艷文 楊思
[摘要]文章從創傷視角分析了由獲得普利策大獎的英國當代著名文學大師伊恩·麥克尤恩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贖罪》,從電影主人公布里奧妮的視角,闡釋了其少年時期的無知行為所造成的創傷,指出她的錯誤行為在給姐姐和其戀人造成創傷的同時,也對自己造成了創傷,要用一生來進行良知的拷問。而觀眾在目睹了一幕幕的悲劇情節后,也品嘗了創傷的刺痛,對戰爭的殘酷、贖罪的無計、生命的無奈和人性的糾葛進行反思。
[關鍵詞]創傷;救贖;良知
電影《贖罪》改編于英國當代文學大師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的同名小說,由英國著名導演喬·懷特(Joy Wright)執導。電影版的《贖罪》就像它的文字母本一樣,揭示了文學的一個基本命題,即人性的回歸,也因而獲得了諸如金球獎最佳影片獎等多項大獎。
故事講述了二戰前夕13歲的少女布里奧妮因為誤證姐姐的戀人羅比犯了強奸罪,而鑄成改變多人命運之大錯的故事。耽于幻想的少女、殘酷的戰爭、終生的悔悟、臆想中的和解,贖罪的結果是無處可贖,變成終生的良知拷問。弗洛伊德在闡釋創傷時指出,“受創的悲悼主體經過一段時間的悲傷,將愛從失去的客體轉移到新的客體,順利實現移情。受創的抑郁主體卻將對外在愛的客體的憎恨和懲罰以逆轉的方式發泄到自我心理空間中被對象化的自我上”[1]。成年后的布里奧妮意識到因為自己年少時期的想象而歪曲了事實,破壞了姐姐的美好愛情,她嘗試著贖罪,但卻失去了贖罪的客體,造成無處可贖。影片中無論是少年、青年還是老年時期的布里奧妮,留在觀眾心弦上的是虐他、虐己和他虐的輪回,一次次的創傷、黯然的結局,影片大幕落下后最沉重的是觀眾的被虐。本文從女主人公布里奧妮的視角,分析并探究電影《贖罪》的創傷書寫,以期對這部情感大片提供又一欣賞視角。
一、虐他
電影首先展現了在一戰和二戰之間英國社會的鄉村田園生活。布里奧妮是泰利斯莊園主人的小女兒,她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除了主人一家,還有女傭和她的兒子羅比,羅比在主人的贊助下與主人的大女兒一起上了劍橋大學,并雙雙陷入了懵懂的愛情。全家人暑假都回到鄉間大宅度假,同來度假的還有長子的朋友、布里奧妮的表姐和兩個雙胞胎表弟。影片一開始,充滿文學想象和創造才能的布里奧妮正在創作她的情景劇,唯美的畫面、奢華的豪宅、懵懂的愛情,在如此的敘事語境下故事的大幕徐徐展開。
表姐在泰利斯莊園被人強奸,年少自負的布里奧妮展開了想象的翅膀,言之鑿鑿地指證了羅比就是強奸犯,結果羅比被繩之以法,拆散了一對美好的鴛鴦,電影因而開啟了對這對年輕人的虐心之旅。
姐姐因為情人被投入監獄而到一個戰地醫院去工作,在一次轟炸中躲在防空洞里被海水淹沒;姐姐的戀人羅比加入了戰爭,在法國北部的敦刻爾克,在炮火紛飛中忍受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畫面中滿目瘡痍的小村莊、牛場里大大的炮彈坑、被炸飛的血肉之軀、羅比手中戀人送給他的海邊小屋的照片以及羅比在臨死前回到家鄉看到心愛的人和自己母親的幻覺,無不昭示著布里奧妮的虐他行為的殘酷后果,畫面中原本應該屬于這對戀人的美好生活卻是一場夢境。
一個死于敗血癥,一個死于空襲,一切只是源于一個無知少女的自以為是和滿腔嫉妒。原本應該綻放的美麗人生被活生生地改寫了,生命早早地凋零了,悲劇之美在于渴望的得不到,幻想變不成現實,贖罪本身是一種心靈的莫大痛苦煎熬。“緣分未盡,我們緣分未盡,我要堅持……我會回去,回去找你,愛你,娶你,然后挺起胸膛生活。”(The story will rsume, our story will resume, I will return, find you, love you, marry you. Then live without shame.)
影片中,羅比臨死前,還在憧憬著回到家鄉。“我要回去,我答應過 ,要幸福地過日子,她愛我,她在等我。”那張漆了藍色窗欞的海邊小屋的照片一直攥在羅比手里,在黑暗中,羅比點燃火柴還要看看那張小屋的照片,因為那是夢想,那是期望,那是他的心上人承諾的他們將要一起生活的理想之地。
二、虐己
故事的另一場景是布里奧妮長大了,她為自己的武斷帶給羅比和姐姐的巨大傷害而無法釋懷,她放棄了去劍橋的機會,成為一名護士,去幫助那些傷兵。深受良心譴責的她以苦行的方式在醫院里默默地做著護士工作,深深自責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她將那些從戰場上歸來的傷病員視作是姐姐的初戀,無微不至地進行悉心護理,借此來實現自己內心的救贖。影片多次給出了她在醫院工作時不停地刷洗雙手的特寫鏡頭,觀眾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樣的鏡頭有著雙重寓意,她刷去的不僅是病污,還有心里的極度懊悔。
然而當她發現表姐勞拉與當年的強奸犯結婚時,意識到自己無法還事實以真相,表姐不會幫助她佐證當年的錯誤指證,便轉而通過文學寫作來完成自我救贖。
在長達59年的創作歷程中她曾六易其稿,其中六個版本的事件經過、結局安排都不盡相同,布里奧妮這樣不停地修改原稿,尤其是修改有關結尾部分的事實說明,她想只有這樣,她才能給予她們早應屬于她們的幸福。她將《贖罪》比作莎翁的第18首愛情詩,只要她的手稿尚存,哪怕只是她終稿的一個打印孤本,她的姐姐和戀人就能生存下去,相愛永遠。“在面對過去,治愈創傷的過程中,布里奧妮通過書寫撫慰了受傷的心靈,同時對自我、人性和社會有了更深的認識,實現了與自己的和解。”[2]
凱西·卡魯斯給創傷定義為“一種突如其來的、災難性的、無法回避的經歷”[3]。布里奧妮最終選擇正視過去,通過創作釋放自己的創傷記憶。其實,布里奧妮一生都在書寫、改寫、重構這部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小說,她期許能夠給他們最好的結局,以實現自己內心的救贖。影片中布里奧妮選擇為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提供一個道歉的場面和團圓的結局,她找到了姐姐,此時二戰的硝煙已經散去,人們的生活也重回正軌,姐姐和羅比重拾了昔日的美好生活,有情人終成眷屬,無辜之人得到昭雪,負罪之心獲得解脫。
不可否認的是,布里奧妮在長達幾十年的寫作過程中,“罪孽在一次次回憶中被不斷放大、直至變成終生纏繞的夢魘”[4]。片中布里奧妮給姐姐寫信,告訴姐姐自己正在接受護士培訓,“我決定不去劍橋了,我想做個有用的人,做點實事,不管多賣力干活,不管每天忙多少個小時,我總是無法忘記我犯的錯誤,還有那錯誤的后果,那件事的前因后果我才剛剛開始明白”。有的人用金錢贖罪,有的人用愛情贖罪,而布里奧妮用漫長的生命書寫來贖罪,當她面對鏡頭,那張被歲月沖刷的面龐,充滿了悲傷、愧疚與無奈,她在年少無知時候做出的虐他行為,卻用一生時間在虐己。
三、虐觀眾
將文學與現實混為一體的布里奧妮,創造性地把無意間窺視到的姐姐與羅比的爭吵、誤傳的信件以及書房里戀人間的親熱,與表姐被強奸的場景聯系起來,并賦予其意義。
“是的,我看見是他,親眼所見。”(Yes, I saw him, I saw him in my own eyes.)
布里奧妮的證詞將羅比推向了戰場,戰爭的慘烈使得觀眾仿佛能聞見戰火的焦煳氣味,那些戰爭場面無數次地拷問著觀眾的心。戰爭是那些利益集團打著正義與邪惡的旗號,滿足一小部分人的私欲的工具,在它的陰影下,人們喪失了自由、平等的生活秩序和身份,在戰地醫院里沒有布里奧妮的名字,只有泰利斯護士,布里奧妮和其他護士一樣,只為戰爭服務。戰爭被美化,官方宣稱的前方的軍隊士氣鼓舞、節節勝利,觀眾所看到的卻是敦刻爾克大撤退:昏暗的黃昏沙灘,遠處的風車有氣無力地旋轉著,沙灘上的士兵橫七豎八地躺著、坐著,有的喝得爛醉,麻醉心靈和肉體,有的面無表情地唱著圣歌,有的甚至在銷毀他們戰斗的武器。在電影中,數以千計的女童尸首遍布于荒野和叢林之中,傷兵橫七豎八地躺在醫院里,身上流淌著膿血,好多人肢體不全、傷口潰爛,讓人目不忍睹。而與之相對應的是BBC的高調、虛假的影像報道資料,蒼白荒謬,觀眾的內心不斷地被虐。人類的貪婪和掠奪的欲望使得他們對自己的同類發動了戰爭,戰后的國土家園滿目瘡痍,人們的心靈受到重創,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作為觀眾,我們欣賞完影片后深深反思,如果一個人的罪責能用自己的生命來救贖,那么對于帶給人類災難的戰爭,又用什么來抵償它的罪惡呢?
影片中,布滿皺紋的布里奧妮對著攝像機說出了自己新書的秘密,羅比與姐姐的再次相逢是美麗的謊言和虛構,面對片中羅比死于敗血癥的蒼白眼神和姐姐尸體漂浮在水上的鏡頭,觀眾禁不住會肝腸寸斷、唏噓不已。布里奧妮的自責和贖罪并沒有改寫故事的悲慘結局,留給觀眾的是無限的遺憾和反思,反思人性的本質,反思自我。
“我姐姐和羅比再沒有機會團聚,也沒有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幸福。我覺得……是我分開了他們倆。但是我的讀者能從那樣的結局中,獲得什么樣的希望和滿足感呢?”
從故事的敘事視角來看,布里奧妮為整個故事提供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使蒙冤之人得以平反昭雪,負罪之心得以救贖,有緣之人得以幸福結合,然后再將這一美好撕裂。影片結尾,羅比與心愛之人終成眷屬,布里奧妮的嚴重過錯得到救贖,觀眾為此如釋重負,但尾聲部分布里奧妮的真相披露使觀眾的內心情感突然崩塌。著名文學評論家費倫指出,這樣的結尾是“一種充滿暴力的揭示”[5]。但是觀眾在接受布里奧妮布下的情感斷崖的同時,也會有期待之外的收獲,因為“布里奧妮的浪漫回歸不是原地轉圈,而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運動,因為她在呈現了一個美好愿景的同時提供了事實真相,讓讀者在經歷悲劇式的撕裂之痛后有前行的勇氣和希望”[6]。
四、結語
目睹了表姐勞拉在戰后與當年的強奸犯結婚,布里奧妮極度迷茫,她再也沒有機會修補過去由于年少無知而犯下的錯誤了,她只能寄希望于寫作,選擇正視過去,通過創作釋放自己的創傷記憶。利科指出:“記憶讓人保存了過去的蹤跡,使之不至于被淹沒摧毀;透過寬恕與許諾,人才能從過去的枷鎖中解放,找到繼續前行的勇氣和希望,成為‘過去的主人。”[7]布里奧妮無疑是“贖罪”的主體,可是除此之外,又是誰將家園國土毀滅,將愛情破滅?戰爭,才是人類命運中最大的罪犯,戰爭發起者才應該是“贖罪”的最大主體。不可否認,是布里奧妮的敏感和錯誤的想象將姐姐和心愛之人拆散,但隨后的戰爭將團圓的可能性徹底撕裂,美麗的家園、美好的愛情是被戰爭這把魔劍毀滅的。影片中,從表面上看,布里奧妮是在為自己的行為贖罪,其實,誰又能說她不是在為人類所發動的戰爭贖罪呢?伴隨電影落幕的是觀眾對本片的創傷書寫的反思,縈繞不去的是對戰爭的無情、贖罪的無計、生命的無奈、人性的糾葛的反詰。
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凈化功能應該主要側重于悲劇所激起的情感對觀眾的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的‘清理,即擺脫痛苦的情緒和脆弱的性格,建立強健的身心體魄。”[8]無論是少年、青年還是老年時期的布里奧妮,留在觀眾心弦上的是虐他、虐己和他虐的輪回,而最沉重的是觀眾自身的被虐。黯然的結局,贖罪的結果是無處可贖,《贖罪》的創傷書寫變成對觀眾終生的良知拷問,也許這就是這部悲劇電影的意義所在吧!
[參考文獻]
[1]陶家俊.創傷[J].外國文學, 2011(04).
[2]王俊生.無法撫平的創傷[J].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02).
[3]Caruth,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21.
[4]梁衛格,陳宓.英國影片《贖罪》賞析[J].電影文學, 2010(24).
[5]詹姆斯·費倫.敘事判斷與修辭性敘事理論:以伊恩·麥克尤恩的《贖罪》為例[J].申丹,譯.江西社會科學, 2007(01).
[6]鄒濤.敘事認知中的暴力與救贖——評麥克尤恩的《贖罪》[J].當代外國文學,2011(04).
[7]Ricoeur,Paul.“Memory and Forgetting”: Questioning Ethic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M].Eds.Richard Kearney and Mark Doooley.London:Routledge,1999:10-11.
[8]朱立元,袁曉琳.亞里士多德悲劇凈化說的現代解讀[J].天津社會科學, 2008(02).